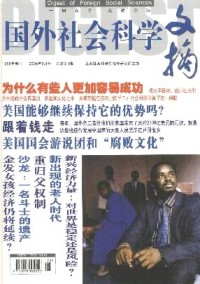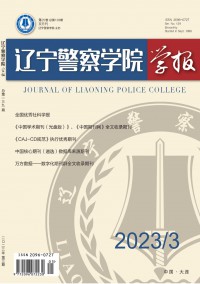恐怖愚人节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恐怖愚人节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恐怖愚人节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内部人控制 博弈分析 解决思路
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出现,缘起于现代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委托――关系。公司治理结构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人的激励和约束问题,激励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积极为投资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而约束的目的则是为了使人不至于因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激励的实施,就应使人有职、有权、有利,而约束的出现,就应使人的职位、权力、利益时刻受到监督,二者之间的制衡便成为公司治理结构有效与否的关键。但是由于董事会与公司经理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这就严重地限制了董事会监督、评价经理业绩的能力。同时,在多数情况下董事会中又普遍缺乏深谙公司财务等方面的专家,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对本已有限的信息资源的利用。信息不对称造成董事会与公司经理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使委托――循环恶性发展,从而造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应当承认,适度的内部人控制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尤其是当股东监督成本大于内部人的成本时更是如此。但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内部人控制。本文论及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指内部人控制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发展,严重背离了社会最优化目标。事实上尽管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逐渐完善,但内部人控制问题依然相当严重。
基于此,本文从所有者对经营者监督的角度,对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展开分析,进而在对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模型的建立
现代企业所有权扩散的结果是形成了两类典型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即集中所有权结构和分散所有权结构。在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董事会、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人的行为目标与委托人的行为目标常常是不一致的。委托人所要求的是股东权益的最大化,而人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很有可能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如果人认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股东的监督使其收益与损失之差要小于他以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得到的收益时,就会以股东权益最大化为他的行为目标。否则,他就会谋取私利。
可见,无论是在何种股权结构下,股东和经营者都具有不同的效用目标,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被认为是非合作的。现假定某公司有股东A和经营者B,A可以选择监督和不监督两种行为,B可以选择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两种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混合战略非合作博弈模型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假设c为A监督B所需的成本,F为B的努力成本,它等于B不努力时的收益与努力时的收益之差,A的收益是B努力程度的函数,当B的努力成本为F时,A的收益为a,当A对B进行监督时,B为维持不努力的运行成本为φ(假设B的运行成本全部为A对B的罚款,也即φ是A在此时的一部分收益)。则A、B的效用矩阵如下:
用ρ代表股东监督的概率,λ代表经营者努力的概率。给定λ,则股东A监督(ρ=1)和不监督(ρ=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A(1,λ)=(a-c)λ+(a-c+φ)(1-λ)=a-c+φ-φλ
UA(0,λ)=aλ+0(1-λ)=aλ
解UA(1,λ)=UA(0,λ),得λ=(a+φ-c)/(a+φ),即经营者不努力工作的概率大于(a+φ-c)/(a+φ)时,股东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反之,则选择不监督。如果经营者努力的概率等于(a+φ-c)/(a+φ)时,则股东随机的选择监督或不监督。
给定ρ,则经营者B努力(λ=1)和不努力(λ=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B(ρ,1)=-Fρ+(-F)(1-ρ)=-F
UB(ρ,0)=(-F-φ)ρ+0(1-ρ)
=-(F+φ)ρ
解UB(ρ,1)=UB(ρ,0),得ρ=F/(F+φ),即股东监督的概率大于F/(F+φ)时,经营者选择努力工作,反之,则选择不努力工作,当股东监督的概率等于F/(F+φ)时,则经营者可随机地选择努力工作或不努力工作。
因此,该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为ρ=F/(F+φ),λ=(a+φ-c)/(a+φ),即股东A以ρ=F/(F+b)的概率选择监督,经营者B以λ=(a+φ-c)/(a+φ)的概率选择努力工作。该纳什均衡是经营者B的努力成本F,不努力的运行成本φ,股东A收益a,及股东A的监督成本c的函数。通过均衡点的分析,可知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下:当经营者选择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所有者选择监督。当所有者监督时,经营者选择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当经营者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所有者选择不监督。当所有者不监督时,经营者选择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所以,所有者选择监督的概率一定要使经营者选择以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期望得益相等。可见,经营者不努力的成本φ越小,F/(F+φ)越大,(a+φ-c)/(a+φ)越小,即股东监督概率越大,所需要的监督也就越大。股东收益a越大,(a+φ-c)/(a+φ)越大,即经营者努力概率越大,股东所需要的监督也就越少。股东监督成本c越小,(a+φ-c)/(a+φ)越大,即经营者努力概率越大,股东所需要的监督也就越少。
控制“内部人控制”的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找出内部人控制的解决思路: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降低经营者努力工作成本
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中经营者的报酬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由于尚未形成职业经理阶层,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往往由行政领导指定总经理,其报酬很难与公司效益真正挂钩;而在民营公司里,往往由投资人自任经理,经理报酬与股东收益混为一谈。在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超越非人力资源的经济环境下,寻找有效的经理报酬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努力工作成本是不努力工作时的收益与努力工作时的收益之差,因此降低经营者努力工作成本可以通过减少经营者不努力工作的收益或增加经营者努力工作时的收益两种途径来实现。报酬机制就是董事会激励经理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经理的报酬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工资与奖金、股票购买权、其它长期奖励。其中股票期权制度可以有效提高经营者努力工作的收益来实现降低经营者努力成本,达到股东减少监督的目的。股票期权是对公司管理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它是通过赠与内部人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作为补贴,使公司内部人拥有在将来以规定的价格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这样,经营者努力进行经营管理,使公司价值得以提高,股价也会随之上涨。此时,经营者可以通过出售股票期权获得收益,而这部分收益正是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回报,反之,如果经营者不努力工作,他的股票期权价值也就不能实现,也就没有这部分额外回报。从而达到激励内部人努力工作的目标。
应该注意的是,尽管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经营者持股,经营者应该有更大的动力去实现公司价值或股东收益的最大化。但是研究证实(Yermack,1995):第一,只有当公司的会计收益数据存有很大模糊性时,股票购买权奖励才会对经理构成一种动力。第二,受流动性约束较大的公司倾向于使用股票购买权奖励手段,以减少公司的现金支付。这些研究说明,股票购买权奖励手段的应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另一项针对经理所有报酬机制所做的研究证实,公司绩效或经理的动力与经理报酬之间缺乏显著的联系:据统计,股东收益每1000美元的变化会使经理的工资与奖金变化30美分,股票购买权奖励变化15美分,与解雇相关的收入变化30美分;这样,股东收益每1000美元的变化对经理报酬的影响总计只有75美分。经理持股虽然是最有效的动力机制,但总体持股水平过低。由此可见,经理报酬机制并未发挥预计的激励作用。
建立科学有效的内外约束机制,提高经营者不努力工作的运行成本
公司制企业中,内部控制机制是指股东和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控制,它是约束经营者日常行为,实现事前帕累托最优的适当手段。内部控制机制作为一种预警系统,可以在公司陷入危机阶段之前促使公司摆脱困境。公司内部管理控制机制包括公司组织规划,与管理当局进行经济业务授权的决策过程有关的程序和记录,以及其他与财务控制关系不甚紧密的程序和记录。董事会是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系统的核心,它负责为公司经理制定博弈规则,其主要任务是雇佣、解雇、奖励公司经理。
为了更好地对经营者实施监督,可以通过推行会计人员委派制,使会计人员隶属于所有者(而非经营方),通过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进行实时控制,借以对经营者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以防止其道德风险行为。
会计人员委派制的出台和试行就是针对会计人员对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监督弱化的缺陷,按照“国家(国务院)会计局(财政部领导)会计人员(执行监控)内部人”逐层委托的设想,主要向各级国有企业中委派独立客观的会计人员来强化对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和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内部人)的监督。
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完善经营者的外部控制机制来降低经营者不努力的成本。经营者不努力的运行成本指不努力一旦被发现所丧失的收益,包括经营者人力资本的贬值以及所有者对他的惩罚等。这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经营者市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东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与制约,是通过有效的公司价值评定和公司控制权转移的资本市场以及其它一些制度安排来加以实现的,规范的股份制度与股票市场可以已通过一系列市场手段(如公司控制权之症、敌意收购、融资安排等)约束经理人行为,迫使经理人努力工作。我们应当在活化公司股权的基础上构筑破产机制、兼并机制,并发展完善经理人市场。通过外部股东以及人力资本市场的压力加强对内部人的控制。
提高股东收益,降低股东监督成本
公司治理结构的良好的权力制衡关系依赖于分散化的公司股权结构。只有公司股权具有相当的分散度,才不至于出现大股东大权独揽控制公司管理层,从而损害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股东过少,由于缺乏其他股东的力量平衡,股东之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权力斗争的概率迅速增加,从而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但过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也不利于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股东过多且股权比例高度分散(如欧美等国的上市公司),那么每一个股东都不会因自己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努力而获得太多的收益,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搭便车”,于是大家就都没有积极性去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从而形成经营者大权独揽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企业经营陷入无序状态。因此,理想的股权结构应当是股权既有一定的分散度,又不致过度分散的中间状态,这样相对的大股东就会有动力去监控企业经营者,使之不偏离正常的轨道。由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大,其股东收益与目标公司具有极大的相关关系,因此,大股东相对其监督成本而言的监督收益将大大高于小股东,他们有更强的动力去监督目标公司(尽管其监督的部分收益被“搭便车”的小股东获得)。我国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关键是如何提高国有股的管理监督能力,同时防止大股东与经营者层相互勾结,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其次,有意识地培育机构投资者。可以分离股东的公益权和私益权,将公益权分离出来交给专门的机构集中管理(如基金,投资公司等)。专门的机构由于有专门的管理人才,可大大降低其监督管理成本,同时,由于公益权的集中,其相对的持股比例也增加,从而很好地克服了专门机构的“搭便车”心理。
参考资料:
1.费方域,《控制内部人控制》,《经济研究》,1996
2.林毅夫等,《现代公司制度的内涵与国有公司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97
3.卫兴华、黄桂田,《从“穷庙富方丈现象”谈起》,《经济日报》,1997
4.杨宏星,《公司制公司的权利是怎样分离的》,《改革》,1997
5.朱建芳、张友福,《“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实质及解决思路》,《中国经济问题》,1999
6.杨小凯,《经济控制论初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恐怖愚人节范文第2篇
4月1日是愚人节,我准备和妈妈开一个玩笑,捉弄她一下。可是我没有道具,我想到家门口的玩具店,对,去那儿买道具!
到了玩具店,我发现了许多捉弄人的玩具。有“断掉的手指”、发电口香糖、毛毛虫、恐怖贺卡……我顺手翻开了一张恐怖贺卡,里面竟然一下子窜出一个大毛毛虫,还发出了虫子吐丝的声音。我马上付钱把这张贺卡买了下来,回到了家。
我先是在贺卡上写上:“祝亲爱的妈妈愚人节快乐!”可我怎么才能让妈妈翻开它呢?自己递给她,她肯定不会打开。想着想着,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我找来了妈妈最爱看的《读者》,把它打开,把那张贺卡粘了上去。我自己还实验了一下,效果很好。我想:“哈,老妈,就让这只毛毛虫陪您度过快乐的愚人节吧!”
恐怖愚人节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工效学;监控系统;人机界面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 6129-0243-02
组态软件是一种通过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模拟或者数字信号的方式输入PLC进行处理后生成监控人员所需要的信息及数据,安装于windows等操作系统的开发程序,常用于空间监控、设备监控、电力等大型工程环境。目前多数的组态软件因为监控点数多、需带有大量统计分析的数据库,所以使得了其每个界面中都需要容载大量的数据信息、图像信息、图表信息,人机界面上大量的信息堆叠会形成视觉上的杂乱感,无论是视觉搜索还是光标对按钮的选取都很大程度的给作业人员增加信息干扰。随着对视觉规律理论在IT行业中应用被证实其科学有效性,以及人们对用户体验的重视,眼动追踪技术也随之发展并广泛应用于互联网行业的商业行为。但是工效学中的信息搜索与信息选取理论在工业领域应用的较少,通过对人眼习惯性运功轨迹、视觉辨识的研究,对舱室温度差异化调节试验平台系统显控界面进行分析设计,重点在于用减少作业人员的时间压力和认知压力,提高作业人员与界面交互的友好性。
1舱室温度差异化调节系统平台研究
1.1l功能层级划分
舱室温度差异化调节系统是用于监测24个舱室室内温度、湿度、风机进出风量、以及其他空调机组数据信息的系统平台。结构系统(见图1)中的主要功能模块有变风量空调、定风量空调、新风机组、冷热源模块、风机盘管、定压装置、辅助监测、报警查看,在层级划分中,将以上8个模块作为第一层级。在第一层级的监控对象中,每个监控设备的对象分别有其相应的显控状态包括:结构视图(模拟显示)、布风器(数字显示)、系统趋势(图表显示)、末端趋势(图表显示)、报表查询(表格显示)等,将其列为第二层级。以变风量空调模块为例,所对应的结构视图子模块为模拟显示方式,对于相应的设备进行抽象形态提取,24个舱室用标有序列号线性框表示。布风器子模块中每个舱室所需要采集的包括:房间温度、房间设定温度、末端实际风量、末端需求风量4个参数。因为布风器模块为单纯数字显控模式,24个舱室参数以每个舱室为单位以带有序号线框划分列与同一张界面上,而不需要再以舱室为单位划分第三个层级。曲线趋势子模块中,要根据时间的变化来监控每个舱室末端的参数值的变化,因此以每个舱室为单位划分成为第三个层级,每个层级以折线统计图的形式显示。报表查询子模块为无限下拉的表格形式。
1.2菜单层级划分
第一层级8个主功能模块名称为第一层级菜单,第二层级的监控显示状态名称为第二层级菜单,曲线趋势中24个舱室的序号为第三层级菜单。在第一层级中添加EXIT按钮,无论位于哪一层级的界面中,点击EXIT按钮都可以返回上一层界面。
2舱室温度差异化调节系统平台界面布局
2.1主界面功能模块内容
根据上述的在系统中划分的三个菜单层级的布局设计中,将主界面的划分成以下模块:系统标题栏、一级菜单栏、二级菜单栏、主要功能模块区域、返回上一步按钮(如图2所示)。三级菜单作为按钮置于系统趋势、末端趋势等曲线统计图界面。
2.2菲茨定律数学模型的应用
菲茨定律(fitt‘s law,用于估算用户移动光标点击链接或控件按钮所需的时间的数学模型。)的数学模型:T=a+b log2(D/W+1)分析,T代表光标从起始位置到目的位置所用的时间,D代表起点到目标位置的距离,W代表目标的大小。a、b为经验参数根据具体环境改变而改变。
根据公式可以得出,光标从起始到目的所需用的时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光标到达目的所用的时间和目标大小成反比。选取较目标物比较小会限制光标的移动速度,因为当光标快要到达目标物的时候使用者便会提前减缓速度以防止移动过快超出目标范围,因此光标的移动速度和目标物的大小成反比。我们常见到将某个系统将多个子模块的简要信息平铺在一张总览图上面,点击便可进入查看子模块详情,次类的进人次层级的方式比点击以子模块名称命名的按钮效率更高,缺点是返回上一层级需要逐步操作,无法直接点击其他层级按钮。其次,在很少数的情况下有条件将按钮放到足够大。
根据菲茨定律理论中所提到的:目的地明确的移动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一个大幅度的移动将光标移向与目标大致相同的方向和区域;紧接着是一系列精细的小幅度微调来将光标精确定位在目标中心,后者的人机活动负担高于前者。因此,在屏幕的边和角的位置比较适合放置菜单栏和按钮,因为边角在鼠标的移动过程中所呈现的物理空间是无限高或无限宽,你不可能用鼠标超过它们。人手无论有多大幅度的滑动,鼠标最终会停在屏幕的边缘,并定位到按钮或菜单的上面。将菜单置于界面的边缘位置,可以使得作业人员在操作鼠标时尽可能地减少甚至省略对于光标的小幅度微调以减轻认知负荷,因此将一、二级菜单分别放置于界面的边缘。
2.3眼动追踪的应用
显示屏已经确定了为16:9的宽屏显示器,横向长度远大于纵向。根据计算机显示按钮的一半字符大小来计算,一级菜单数量为8,二级菜单中的数量最多为5、最少为3,横向尺寸无法容纳一级菜单的字符,因此将一级菜单置于纵列,二级菜单置于横列。在通常情况下作业人员对系统的浏览顺序应该为:系统标题栏
在工效学中有关于视觉运动规律的理论依据有提到:1、眼睛沿着水平方向比沿着垂直方向运动更快,且不容易疲劳,通常在视物的过程中先看到水平方向的物体,再看垂直方向。眼睛对水平方向的尺寸比垂直方向要估计得准。2、对于矩形物件视线的变化习惯于从左-右、上-下,对于圆形物件习惯用顺时针的方式进行浏览。
第二层级菜单位于第一层级菜单的右下方向最符合人的搜索习惯。如图2所示,a点到b点的轨迹为一般情况下的视觉搜索轨迹,浏览顺序为上一下,左上一右下,下一上,左上一右下,基本符合一般人眼运动规律的。而图3中从点b到点c的轨迹,图4中点d到点e的轨迹都适合人们习惯性的视觉运动规律相反的,所以图2中的界面布局方案在减轻操作人员的认知负担时更为合理。
恐怖愚人节范文第4篇
景航学校飞鹰文学社 七(2)班童 志 磊
4月1日,是外国的愚人节。
为了想方设法的骗同学们,我可是起了个一大早,绞尽脑汁的去想办法骗同学们。
到了学校,我刚进教室门,就有一个铁哥们提醒我:今天是愚人节,要注意防范!说实话,他要是不提醒我,我还真把提防同学的事给忘了!
我刚把书包放在桌子上,就有一个同学对我说:“昨天我遇见你爸爸了,你爸对我说:等到星期天,他要揍你一顿。”我有些相信他,但又想到了刚才我哥们给我的提醒:今天是愚人节。便问他:“你昨天什么时候遇见我爸的?”这一下,他呆了,但他马上又说:“昨天下午5点钟遇见的。”这时,我不禁笑了起来,因为昨天下午我爸爸还在外婆家呢!
之后,我马上找了几个好朋友,商量好整人的办法。不一会,我们便开始行动了。
我们先找来了我们班成绩GOOD的女生,由我对她说:“老师让你去他的办公室一趟,说什么你和别人互抄作业,反正你去一趟吧,让老师调查清楚,这样对你和别人都有好处,你快点去吧。”起先,她还不相信呢,便问别人,由于我们事先是串通好的,所以她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她便相信了,直到她走到老师的办公室门前,发现没有开门,才知道自己被我们给骗了。
就这样,我们利用这种办法又骗了好几个同学,可搞笑了。
愚 人 节, 越 愚 越 快 乐
景航学校飞鹰文学社七(2)班汪 宇 航
期盼已久的特殊日子——愚人节终于到来了,这下,我可以耍耍老师和同学,反正又不会被老师骂嘛。
同学们正在教室里议论纷纷,好象有什么事。看大部分的同学都往张美芹那边围过去。到底是什么事呢?出自好奇心,我也情不自禁的跑去凑热闹。原来,张美芹正在说一件恐怖的事,她家院子里有两条大蛇,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她爸已经逮了许多条小蛇了。哦!听起来蛮吓人的,不知是真是假呀。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笑眯眯的进来了。“今天难得大家这么高兴,这节课就拿给你们玩吧!”“噢耶……万岁……哦……”顿时,教室里一片欢腾。正当大家想一拥而出的时候,老师突然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就是这三个字让我们的“玩耍课”泡了汤,到底是哪三个字呢?大概你们也知道了,就是“愚人节”。哎!我们真是空欢喜一场。大家都在抱怨说:“要是愚人节是昨天该多好……”
愚人节,我们可都受骗啦!
愚 人 节 上 当 记
景航学校飞鹰文学社七(2)班程 纤 纤
今天是愚人节,上学之前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小心,千万不要被整到。
结果,唉,被整得好惨好惨……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
1
和同学走着走着,同学很随意的说:你的鞋带散了。
我低下头,很认真地看了半天,抬起头,很疑惑的说:没有啊?
2
有个同学说:今天下午要语文考试。
我吓了一跳,紧张地问:考多久啊,写作文不?
等我看到那个同学狂笑几秒后才醒悟过来
3
有个同学问:你看了数学考试的分数没?我刚才看了,顺便看了你的。
我忙问:多少多少,没有死得很惨吧?
那同学脸沉下去,停顿了一下,说:44分。
我很失落的答了声:哦。
心里想:完了完了,肯定倒数,怎么办怎么办...
那同学突然就笑出声来:这你也信啊!
……出了一身冷汗……
4
这件事最可恶啦!
今天,我居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封给我的信!
拆开,一股酸味扑来——原来是“情书”!!!我从出生到现在,收到这种东西可是头一回,内容肉麻的不行,十年前的饭都可以吐出来!
我昨天还在想:我写封“情书”整同学吧,今天居然有人来整我!最恶心的是,信封里居然还叠了十几个爱心!我都不会呢……
悲 喜 愚 人 节
景航学校飞鹰文学社七(2)班刘 一 璜
4月1日是愚人节,这回怎么捉弄别人呢?我心里策划着。
“我中了20元的小奖,今天下午我请客。”陶子同学宣布说。
“好。”同学们高兴得跳了起来。
“但是,还有一个坏消息。这不是真的。”
只听“啊”的一声,大伙才想起今天是愚人节。
哼,该我了,我让你们尝尝滋味,于是我对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说:“这位仁兄,你老爸老妈在校门口,你还不去迎接?”他果然上当了,回头一看,知道被愚弄,说一声:“好小子,敢骗我,看招。”眼珠一转,说:“哦,对了,老师说你昨天没有把教室打扫好,叫你重扫。”我一听,马上去拿扫帚。“哈哈哈哈,你中计了。”
上课了,老师说:“根据学校的安排,下午放假。”“耶……万岁……哦……”教室里沸腾起来,一些同学议论纷纷,大概是在想怎么玩。我刚想说太好了!老师突然在黑板上写了“愚人节”三个字,就是这三个字让我们“乐极生悲”,哎,空欢喜一场了。同学们都说:“老师,你怎么这么狠啊!”“老师你可真毒啊!”“老师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回到家,老爸说:“今天,你可以玩一小时的电脑。”
“我太高兴了,那就快让我玩吧。”
恐怖愚人节范文第5篇
利用电脑和网络整人,关键得靠你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手脚,具备了这两点,你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环扣一环,设下天罗地网,让被愚者无处可逃、哭笑不得。
最初级方法:简单易行,适合所有用电脑的人
趁别人上厕所时在其电脑上设置屏幕保护,并加上密码;伪造网站管理员讲话:“系统即将重启,请保存手中的工作后退出”;发电子邮件给朋友,先用Winzip打包、再次打包……最后做成自解压文件,如此循环几遍,最后对方打开信时,只有6个字:今天是愚人节!
易容术:适宜使用OICQ、ICQ等即时通讯软件的朋友
用紧急事件将正在使用即时通讯软件的被愚者支开,打开即时通讯软件的修改个人资料选项,动用键盘、鼠标,将被愚者的网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络容貌来个全方位修改。至于如何改,那就看你的兴趣和能力了。最后别忘了销毁一切可能暴露形迹的证据。这种方法不易被发现,不仅让被愚者的好友一时半会搞不清楚他是谁,就连被愚者自己也一时半会摸不着头脑。
另一种方法就是设法取得被愚者的OICQ号码,自己重新申请一个OICQ号码,按照被愚者的详细情况填写个人资料。将被愚者加入到你所申请的新号码的联络清单中,然后抓住对方弱点开始对其进行“大型轰炸”。本方法主要是不让对方知道你是谁,因此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隐藏,尽量不要让对方对你有疑心。
提醒被愚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千万要记住将系统锁定,再离开电脑。一旦怀疑中计,只能小心、细心地去观察破解了。
偷梁换柱:改变被愚者电脑中的一些设置
利用麦克风和Windows自带的“录音机”程序录下一些恐怖或离奇的声音,然后将其设置为Windows开(关)机声音。这样当被愚者开(关)机的时候,冷不丁地肯定被吓一跳。
将被愚者电脑中的“我的文档”所对应的目标文件夹改变,让其误以为辛辛苦苦撰写的文档全部消失。
将被愚者常用的一些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目标改变,让其点击快捷方式开启程序后,却发现启动的不是和快捷方式相对应的程序。注意一定要将快捷方式的图标保持和原来的程序一致。
这些方法愚人的效果是一流的,足以让被愚者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浑身冒冷汗。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铸成大错。
提醒:愚人节当天不给任何人可以接近你电脑的机会。
动动硬件:电脑出了故障,一般人都会看程序或网络是否出了问题,很少考虑到细微的小硬件方面
你可以在被愚者还没有上班前,将其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或者鼠标的插头弄松,这样当被愚者上班打开自己的电脑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显示器黑屏或者提示鼠标找不到,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再神勇现身,轻松将问题搞定,那么对方非但不会想到被愚弄,还会大大感激你呢。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