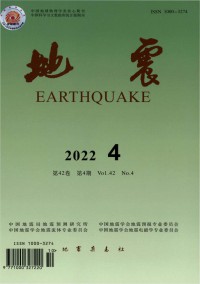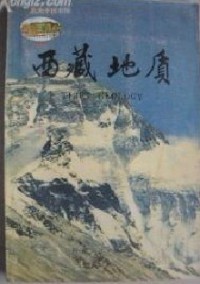地藏菩萨显灵
地藏菩萨显灵范文第1篇
地藏菩萨的前世今生
地藏梵名Ksitigarbha,音译作乞叉底檗婆,“地”是大地,“藏”是含藏、伏藏义。说的是此菩萨犹如大地,功德利益万千众生;又能含藏一切功德,自利利他。即《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说的“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
佛教有“地藏三经”,即隋代僧人菩提灯译《占察善恶业报经》、唐朝僧人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这也是地藏经典体系中最重要的三部,对地藏菩萨的本生、誓愿、功德等多有讲说、宣扬。
按照佛教的说法,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要经历五十六亿七千六百万年才有弥勒菩萨出世,示现成佛。因而佛祖圆寂之前,付嘱地藏,要他在这一漫长的无佛时代,担当救度众生的重任。根据《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的说法,地藏原来历经无量数劫修行悟法,其功德、智慧其实已经可证佛果,但他秉承佛祖法旨,自誓度尽六道众生,始愿成佛。所以地藏菩萨又称“大愿菩萨”,别称“持地菩萨”、“无边心菩萨”。
佛寺中的地藏菩萨的形像多为出家的比丘相,左手持宝珠,右手执锡杖,或坐或立于千叶青莲花之上。
地藏信仰的发展流传
地藏信仰在印度也有存在,但远不如在中土流传广泛和影响深远。而它在中土的流传、发展,也可以看成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一个缩影。
汉译佛经中最早言及地藏菩萨的是《罗摩伽经》,该经由西秦僧人圣坚译出,实为《华严经》的《入法界品》的早期译本。据此可以推断,地藏菩萨的名号大致在4世纪、5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传入中土。北凉(397年或401年~439年)时期译出的《大方广十轮经》,大力宣扬地藏菩萨的本愿与功德,可以视为地藏信仰在中土广为流布的开始。
在中土,地藏菩萨更多是与地狱相关联,作为幽冥教主,即地府的最高领袖,获得世俗的崇信。但地藏起初并未专门与地府关联起来。他最初和观音、弥勒一样,也是以其慈悲和功德为僧徒和俗众信奉。因为地藏菩萨誓愿拯救众生,众生如果能够虔诚念诵其名号或供养其法像,则可获得无上功德与福报,可远离各种忧愁苦恼,得二十八种利益,乃至得以生天、涅。
较早述及地藏菩萨救度地狱众生的汉译佛经是《须弥藏经》,此经由僧人那连提耶舍、法智于北齐天保九年(558年)译出,但此经似乎并没有广泛流传。隋唐以后,随着地藏三经的先后译出和流传,地藏菩萨获得了广泛的信仰。大致上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有关地藏菩萨的造像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翻译与流传,进一步将地藏与地狱关联起来。这部佛经中说到,地藏菩萨誓愿救拔,“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与之相呼应的是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643年~712年),他在其著作《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传记》中都指出,地藏菩萨常处恶道中救赎众生,地狱即是恶道之一。华严宗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颇受朝廷推重,拥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地藏救度地狱众生的观念大概就是在此时正式形成,并开始流行起来。
但地藏菩萨在这里也仅仅是地狱众生的救度者,其地府至尊地位的确立要到唐末五代的时候。这时出现了一部伪经《佛说十王经》,这部伪经存在于敦煌文献中,题为“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此经中历叙从秦广王至五道转轮王等十殿阎王的名目,它确立了后来中土民间颇为流行的地狱十王信仰。而地藏菩萨的形象在此经的图文本中也多有描绘,占据突出位置,如有一个版本中的插图就画有地藏与阎罗王并坐一厅的情景。此经的传本有55种之多,可见十王信仰流传的广泛。随着十王信仰的确立与流传,冥府最高统治者的席位出现了“空缺”。此时地藏菩萨无疑是最具有条件充当此职位的,并最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冥府至尊。北宋僧人常谨撰成于端拱二年(989年)的《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一书,专集中土信奉地藏菩萨灵验之事。其中记载有僧智佑于五代时期驻锡清泰寺,供奉有地藏菩萨变相图。此图中地藏菩萨头顶,位居中央,左右有十殿阎王像,每边各有5人。显然,地藏菩萨在这里处于被拱卫的中心地位,它的存在可以说明至迟在五代时期,地藏菩萨的冥府至尊地位已得到确立。
地藏于地府中的至尊存在,展示了佛教的慈悲与功德,引诱、启示着世人皈依佛道,改过向善,满足了世俗对于生命延续以及趋福避难的欲求。前面提到的《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其实就是以地藏之名号、法力来实现此功能的。宋代以后,此类故事多有出现。地藏信仰在与地狱十王信仰合流的同时,又被赋予了强烈的劝孝意味。这应该是源于被称为佛门《孝经》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在这部佛经中,地藏菩萨多处宣扬孝道思想,教导信众孝敬父母,止恶向善,可以获无边利益。并且地藏菩萨本身就是孝道的实践者。此经中言及他前世曾为一婆罗门圣女,其母轻慢三宝,信从邪行,因而死后堕落地狱。圣女虔诚礼佛,布施供养,使得其母最终脱离地狱。地藏前世又曾经为光目,为拔救亡母堕落恶道及短命之报,供养罗汉,并于佛像前发下救度众生皆得成佛、自己才成正觉的宏愿,其亡母也因此得到超脱。到了明清时期,地藏又与佛教中身入地狱救母的目连合二为一,通过《三世光目宝卷》、《幽冥宝传》这样的文学作品作了形象的展示,其孝道的典型性进一步突出。应该说,地藏菩萨孝道色彩的强化与中土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它迎合了世俗百姓通过信奉佛教来促进社会稳定、家庭安宁的期望,使得佛教与中土固有文化间的关系更为融洽,有利于地藏信仰在世俗社会的广泛传布与深入人心。
民间的地藏节
中土的四大菩萨各有道场,号称四大佛教名山。其中观音菩萨的道场是普陀山,普贤菩萨在峨眉山,文殊菩萨在五台山,而地藏菩萨的道场则在安徽青阳县西南的九华山。之所以是九华山,它与唐代驻锡在此处的一位僧人金乔觉相关。根据《宋高僧传》的记载,金乔觉是唐初新罗国王族,出家之后法号地藏,金地藏涉海来华,入九华山修道,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圆寂,寿九十九。金地藏身高7尺,顶耸奇骨,常年孤坐石室,以白土(也就是民间常说的观音土)和米为食。他圆寂以后,遗体置于木函中,经过30年肉身都没有变坏。徒众以其全身入塔,抬举之时,其全身关节如金锁铿锵作响。大概正是因为他多有高行异相,又恰好法号地藏,世人于是就认为他是地藏菩萨转世,九华山因此也成为了地藏道场,其所在寺庙为化城寺,后人并建肉身塔以供奉之。这两个地方至今仍然可以在九华山见到。
地藏菩萨显灵范文第2篇
说起贵阳有名的背街小巷,就不得不提毓秀路与北横巷。
毓秀路与北横巷是相互连通的街巷,都有一个出口在中华北路。毓秀路长500米、宽不过10米,东面路口正对成都路,由西往北通往永乐路。毓秀路1938年因为毓秀里而命名,历史上的地名名称有:文家坝、般若寺、五显庙。
在民国时期,毓秀路北是一个在老城墙上新开的出口,因为紧邻外黑神庙,庙里供奉南霁云而得名霁云门。霁云门是没有城门的出城通道。毓秀路上有几条小巷:毓秀巷可以通往合群路,马家巷与黔灵西路相通,白果巷是北横巷的一部分。现在,毓秀路沿路以居民住宅为主,也有不少机构单位,主要有:市各派市委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公楼、市城市管理局、贵阳市文物局、云岩区民政局、毓秀路小学等。
毓秀路35号大院,解放前是文家大院,文家坝因此得名。1958年4月,当时的云岩区与富水区合并,新的云岩区人委搬到这里办公,将文氏宗祠作为大礼堂,左右厢房及祠堂前楼房作为办公用房。1980年,云岩区委从中华北路迁入。上世纪90年代建设了7层高的办公楼。进入新世纪,根据“退二进三”战略,区委作出搬迁决定。2005年,区党政机关迁大营坡新址。
北横巷也叫北横街,因为横贯于城北得名。曾经的地名还有:金箔行、黉池街。北横巷长约150余米,向南一段通往毓秀路,因为有白果树作为地标,后来改叫白果巷。过去,北横街东口往北就是六广门,六广门外就是城郊了。现在,北横街东口往北是金辉大厦,往南一直到毓秀路口是搜秀新城大厦。已经和中华北路融为一体,成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北横巷内原来有一座般若庵,也叫般若寺,般若寺的读音是“勃勒寺”,般若寺因为《金刚经》中般若心经得名,系佛教寺院。般若寺后来改作学堂,称蒙养义学。1803年,蒙养义学迁大兴寺。如今,般若寺早已在岁月流逝中消失,般若寺址成为居民宿舍。
北横巷因为紧邻蒙养义学、北书院,曾经得名黉池街。北书院在云岩区公安局现址。1800年,即嘉庆五年,由时任巡抚常明在贵筑县治废址上所建的正本书院,因为位于城北,又称北书院。1819年贵阳遭遇地震后,由粮储道倭臣布修葺。1902年,贵阳府在这里创办贵阳府中学堂,为贵州最早学堂。1905年,府中学堂迁到次南门雪涯洞后改为北区警署。解放后至今为云岩区公安分局。
金箔行作为地名是因为这一带金银器加工出名。过去贵阳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穿金戴银的习俗,每逢农历四月八要到喷水池盛装出游、载歌载舞,所以金银饰业主要集中在城北。旧时贵阳贵金属加工业的特色是:店铺的垃圾每年要堆积到年关时才清扫,为的是沙里淘金;对现在称为24K金的金饰品要打刻“上上足赤”、“十成足金”等印记,表明货真价实;金店学徒最怕老板请自己“打牙祭”,这是让人赶路的“最后晚餐”。
白果巷现在仍然是居民住宅区。白果巷口的对面是市城市管理局办公楼,那里原来是建于清末的五显庙。清人刘蕴良题五显庙联:“才兼乎三,德备乎三,玄功贯乎三,三亦微亦显;气运其五,行超其五,化身纷其五,五乃圣乃神。”五显庙1934年改建成为大同电影院,后又改作炸药库,也曾经作为卫生管理机构用房。
五显庙里供奉的五显是民间信仰中无时不显的五位神仙,也叫五位菩萨。能赐药治病、显灵退贼、滴水救火。毓秀路五显庙供奉的五显财神也是民间的“偏财神”。五显财神信仰普遍流行于江西,五显财神指兄弟五人行侠仗义,封号首字皆为“显”,生前劫富济贫,死后仍惩恶扬善保佑穷苦百姓,民间合称为“五显财神”。贵阳曾经有过几座五显庙。解放初期,中山西路旁边通衢街的五显庙还在,说明当时城内江西籍人较多。《西湖游览》载:“五显者,五行之佐也,无姓氏可考。宋时赐号,一曰显聪昭圣李顺福善王,二曰显明阳圣事义福顺王,三曰显正昭圣伊智福应王,四曰显直昭圣军爱福惠王,五曰显德昭圣争信福庆王。五王封号皆有显字,故谓之五显庙云。”民间认为五显相助,求子如愿、经商赢利、读书成就功名、农事丰收,有求必应。
在民间,称为五显的还有五圣大帝、五通大帝、华光菩萨等。在民俗中,五显是由神到人,又由人到神和神灵。这些五显与毓秀路供奉的五显就没有太大关系了。相传玉皇大帝封之为“玉封佛中上善王显头官大帝”,永镇中界。五显作为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善神之一。民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初五接的财神是《封神榜》上原在峨眉山罗浮洞修道的赵公明,因助纣攻打武王,死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由于关公亦称武显,民间也普遍视为财神。现在,许多商铺、住宅都供奉赵玄坛面似锅底、手执钢鞭、坐骑黑虎的神像或关云长红脸美髯、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塑像,庄严威武。在江南一带,每月初一、十五,经商之人都要去五显庙焚香供财神,正月十五至十八迎五显大帝回庙,用鸡鸭鱼猪牛和香蜡纸烛炮祭礼。蠡海集载:“九月二十八日为五显生辰,盖金为气母,五显者,五行五气之化也。” 又云:“五行大帝,按俗以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五显大帝又称华光大帝,诞辰在农历九月二十八日。传说华光大帝是三只眼火神,称为三眼华光,因喜欢玩火烧了玉帝的九龙墩,玉帝令其每年八月初一由天上下凡。农历八九月间正是天干物燥,容易发生火灾。华光诞辰日,百姓把易燃的木炭、纸屑等捆成一把放置门口,由巫师、和尚逐户收取,集于纸船投入江海中焚烧,认为这样能“灭火消灾”。同时,家家户户到火神华光大帝庙参拜,祈求一年平安。农历九月二十八日这天,各地基本都有参拜与庆祝五显的习俗。
在毓秀路,解放前还有一所寺庙叫地藏寺。寺庙建于清末,供奉地藏王菩萨。地藏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是救度天上及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地藏由于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所以名地藏菩萨。抗战时期,因为人口激增,学校不够,1944年,市参议员余筱田出面将地藏菩萨移到弘福寺,地藏寺改为毓秀路小学。学校将地藏寺的正殿隔为4间教室,另将右厢房隔成两间教室,后殿设小礼堂。因为紧邻霁云门,命名为霁云中心国民学校,校门面对永乐路。1952年,校门改设在毓秀路后改名毓秀路小学。毓秀路小学1973年改为云岩三中,1984年停办并恢复毓秀路小学。
贵阳历史上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民间曾经对地藏菩萨顶礼膜拜,在众多的寺庙里都供奉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梵名 Ksitigarbha,是菩萨之一。《宋高僧传》卷二十载:“地藏菩萨的生日是7月30日,降诞为新罗国(朝鲜)王族,叫金乔觉,在唐玄宗时期出家来到九华山,居数十年后圆寂,九华山供奉他的肉身殿传为地藏成道处。地藏菩萨的道场也因此在安徽九华山。九华山与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地藏十轮经》谓其:“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所以称为地藏。《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述:过去无量劫前有一婆罗门女,“其母信邪,常轻三宝”,命终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婆罗门女知母生前不积善因,死后必堕恶趣,遂变卖家宅供养佛寺。后受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指点,以念佛力来到地狱,见到鬼王无毒,得知因自己供养佛、寺之功德,使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地狱的罪人,得以脱离地狱之苦,超拔升天,婆罗门便在自在王如来像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菩萨,当时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释迦牟尼在经中讲述了地藏菩萨种种不可思议行愿。地藏菩萨发出“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使众生只要念诵其名号、礼拜供奉其像,就能得到无量功德、获得救度。
地藏菩萨显灵范文第3篇
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东方最有影响的两种文化体系,两千多年以来两种文化始终存在着密切的对话与交流。正像这两种文化体系是由许多不同的领域构成的一样,它们之间的对话也表现在宗教、哲学、艺术、文学、民俗、伦理等许多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宗教文化方面,中印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对话,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还从许多方面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本文则以中国民间观音信仰这种重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为例,说明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及其深远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研究始终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更没有人从中印两种文化的对话角度进行过思考。本文只是一个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我认为,中国的观音信仰可以划分为三大体系。其一是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它归属于正统的中国佛教范畴,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显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产物,保持了更多印度大乘佛教显教的成分;其二是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主要流传于藏蒙及山西、四川、北京等广大汉族地区,它归属于正统的藏传佛教范畴,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密教同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化对话的产物,以印度大乘密教的成分为主体;其三就是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体系,主要流传于汉族的广大民间地区,它归属于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不为正统佛教所认可,是印度大乘佛教文化(以显教为主体)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对话的结果。在这种观音信仰体系中,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成为一种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观音信仰体系。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领域里,儒道文化同印度佛教文化在观音信仰方面的对话是通过不同于正统佛教领域的许多不同方式来进行的。中国儒教文化侧重于伦理思想方面,基本方式是补充印度佛教文化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孝道、子嗣、长寿和仁善观念等方面;而中国道教文化则侧重于神灵体系方面,基本方式是修改印度佛教文化在这一方面的固有说法,主要表现在观音身世、所处境界、在神团中的地位以及观音的心境和神通等方面;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中国儒道文化的不同特征而决定的。儒教文化是以伦理教化为其主要特色的一种文化体系;而道教文化则长于融摄和创造丰富多彩的神灵信仰体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汉代以来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道教善于改造吸收各种神灵信仰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将其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之内,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神灵崇拜现象,这也成为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受道教这一特征的影响,当印度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走向中国民间以后,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之间的对话便首先在神灵领域内展开了。由于民间既没有各种经典与教义的规范,又没有各种既定成规与权威的束缚,所以,在中国民间,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的道教文化的对话是在更为广阔、更为开放、更为灵活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中国民间,无论对于基层老百姓来说,还是对于无信仰的各类知识分子来说,不管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道教,其原有的纷繁复杂的神灵已失去了严格的宗教义理与宗教规范的制约,为我所用的原则同大胆无束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在民间的对话导致了原本威严有序的神灵体系的持续变革与混乱,处于神灵体系之中的单个神灵也被迫脱离正宗的位置,甚至再作重新的组合。在这一对话过程中,观音在神格上主要发生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改变:
首先,从观音早期的身世来看,印度佛教认为,观音是远古时代的一佛,名叫正法明如来,因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娑婆世界苦难深重,所以投身人世救苦救难(见《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110页)。根据印度佛教经典的说法,观音投身人世后,为了方便说法和教化,所以随顺世间凡情俗习,历经多次转生,相继作过大居士,大仙人等(见《十一面神咒心经》,《大正藏》第20册,第152页)。印度佛教观音身世说教中最著名的是“不旬太子” (见《大正藏》第3册,第167-233页)和“莲花童子”(见《大正藏》第12册第353-357页)。
受道教的影响与启发,中国民间无视印度正统佛教经典的权威说法,另外为观音立了一个身世,最著名的是妙善公主的传说。这个故事据说最早源于唐代高僧道宣听天神所讲,道宣的弟子义常从道宣处得知,将其记录下来,后又传至河南汝州香山的僧人怀昼。蒋颖叔在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应怀昼之情,将义常的记述“润色为传”(见 [宋]朱弁,《曲Y旧闻》卷6,清乾隆甲午年刊本,第5页)。南宋初张守的撰文对这一事迹大加赞颂,从而使其进一步传扬(见[宋]张守,《毗陵集》卷11,光绪二十一年盛氏刊本,第10-11页)。接着,祖绣又在《隆兴编年通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于是这一说法便逐渐传播开来(见[宋]祖绣,《隆兴编年通论》卷13)。到了元代,管道升在此基础上写成《观世音菩萨传略》,从此妙善修道成观音的故事为民间普遍接受,并不断渲染,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戏剧、散文作品和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
但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经典根据的,所以严谨的佛教徒历来采取否定的态度,就是在这个故事刚刚编写出来的时候,也有人提出反对。如南宋朱弁就认为:“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信后世,岂未之思矣!”([宋]朱弁,《曲Y旧闻》卷6,清乾隆甲午年刊本,页6)后来又有人称妙善的故事“要是俗说,非其实也。”( [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17,光绪九年吴下春在堂刊本,页3)
妙善公主为观音的说法是否来自于道宣,这是大可怀疑的。笔者认为,这是受道教影响而产生的,假托道宣仅仅是为了找一个如法的借口而已。南宋朱弁曾有记载:“《文选·啸赋》注引《灵宝经》曰:禅黎世界坠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岁,王怪之,乃弃女于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无粮,常日咽气引月服精,自然充饱。忽与神人会于丹陵之舍,柏林之下。……于山出,还在国中。国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过半。穿地取水,百丈无泉。王希惧,女显其真,为王仰啸,天降洪水至十丈,于是,化形隐景而去。按此疑即妙庄王女之说所自来。姓音或即观世音也。”([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17,光绪九年吴下春在堂刊本,第23页)可见,妙善的故事的确是受了道教的影响。
民间关于观音的身世还有一种说法,即把观音说成是尹喜所变,而尹喜是老子的弟子,这样一来,观音也便成了老子的再传弟子(参见顾希佳,《菩萨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页30)。受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影响,中国民间还有将观音视为元始天尊和无生老母之化身的。早在北周时期,甄鸾作《笑道论》,对道教大肆抨击,其中说:“臣笑曰:按〈诸天内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灵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于隆汉之号也,至赤明年号观音矣。’”(《广弘明集》卷9,《大正藏》第52册,页146)这一传说到后世已很少流传。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中常将观音视为最高神无生老母的化身,特别是在反映民间宗教各种创世神话的宝卷文学中表现的非常清楚(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600-616)。
其次,从观音所处的境界来看。印度佛教认为,观音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胁侍,协肋阿弥陀佛演说妙法,接引众生。《佛说无量寿经》中说:“彼佛国(指西方极乐世界――笔者注)中……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世界。……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是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终转生彼佛国。”(《大正藏》第12册第273页) 正规佛教还认为,观音虽为极乐世界的一位大菩萨,但出于慈悲救世之心,经常来往人间(《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受记经》,《大正藏》第12册,页353-257)。
可是,在民间,受中国传统神话和道教的影响,印度正统佛教的说法发生了变化。在这里,观音被视为天界中的神,也就是把观音所处的境界定位于天界。而天界之主为玉皇大帝,于是,观音便成为玉皇大帝手下的一员。《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说:“善(指妙善――笔者注)坐普陀岩,九载功成,割手目以救父病,持壶甘露以生万民。左善才为之普照,右龙女为之广德,感一家骨肉而为之修行,普升天界。玉帝见其福力遍大千,神应通三界,遂从老君妙乐之奏,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赵望秦、贾二强校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4,三秦出版社,1989年11月,页94)但以印度佛教的十界理论来看,天界还只是“四圣”之下尚未解脱的六种凡夫境界(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之一,观音作为古佛,应属于四圣中的第一位,作菩萨之后则应属于四圣的第二位。民间信仰将观音置于天界不符合印度正统佛教的理论,但与中国民间的神灵信仰体系得以适应和吻合。 第三,从观音在神团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印度正统佛教虽然认为菩萨均处在十界中四圣界(即佛、菩萨、缘觉、声闻)的第二位,但他们并不受佛的控制与摆布,而只是把佛当作导师一样去尊敬,去效法。在开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菩萨时常会请示佛,佛也常根据需要指示菩萨如何去做。但这并不是等级制下管制与命令的关系。何况在智慧上,得道菩萨与佛并无本质区别,差距只是佛已完成了他的救度任务,即“觉”与“行”都已圆满,而菩萨只是“觉”圆满,普度众生的“行”尚未完成。特别是观音菩萨更是古佛再世,以菩萨身份救度众生,而且最后还要继承阿弥陀佛,成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作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关于各菩萨之间的关系,正规佛教认为他们之间也无相互制约的关系,菩萨对位处其下的声闻、缘觉二圣也无管制权,诸圣之间只有证果高低的差异,而无神权大小的区别。菩萨对各类凡夫众生只有慈悲胸怀下的教化,虽然这种教化有时也会通过比较强硬的手段进行,但这也只是一种方便之策,与神权绝无任何关系。
民间信仰受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及道教神团体系的影响,把观音置于等级森严的神阶制下,于是,向上观音要受玉皇大帝、如来佛甚至太上老君的管束,向下观音又可支配各类鬼怪神卒。如上引文中,观音的名号是玉皇大帝封的,甚至连观音身下的坐莲也是玉皇给的。有关此类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极多。《鬼神传》中讲述了一则故事,说是有一对夫妇,心地非常善良,平日修桥补路,布施贫人,但直到四十岁尚无子嗣。观音有心帮助,却要将此情况“一一上奏天曹……玉皇观诺准奏,即遣天吏往太上老君求取广嗣灵丹两颗”([清]不题撰人,《鬼神传》第9回,《雷峰塔传奇·狐狸缘·何典》,华夏出版社,1995年12月,页287)。可见,观音有事还要上奏玉皇,而玉皇却把赐子这种观音最拿手的事情交给了别人,最终竟是太上老君的“广嗣灵丹”起了作用。又传说,阴间有一恶鬼名叫黑无常,专门以勾魂为职业。“黑无常横行霸道,蛮不讲理;靠的就是玉皇大帝那道旨令和阎王爷手里的生死大权”。观音对此竟然无能为力,“恨无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只好坐在九品莲台上生闷气”(周濯街,《玉皇大帝与观世音》,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页129)。
至于观音管束其它神卒妖怪的传说,在民间传说和各类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明代杨志和著的《西游记传》的标题中就有“观音路降众妖”,“观音收伏黑妖”,“观音老君收伏妖魔”等(参见:[明]杨志和,《西游记传》,收于《四游记》,华夏出版社,1995年5月页109-182)。吴承恩的《西游记》标题中有“观音显像化金蝉”,“观世音收伏熊罴怪”,“观世音甘泉活树”,“观音慈善缚红孩”,“观音显像伏妖王”等。在《南游记》、《北游记》、《东游记》及其他许多小说和民间故事中也有大量类似的内容。
第四,从观音所具备的心境、品格方面来看。印度正统佛教认为,观音菩萨的所有救世行为均建立在般若智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观音已经证得至高无上的圣智,洞见宇宙实相,他对一切均无有执著,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处在一个极其高妙的精神境界中,在这一境界下出现的各种身心行为,尽管也表现为人间的色彩,但这只是一种救世的方便,是其“方便之力”、“无作妙力”的体现。另一方面,观音之所以常留五浊恶世,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宏大誓愿,完成普度众生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观音呈现出无尽的慈悲情怀。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没有慈悲就没有普度,就没有大乘。观音作为主悲的菩萨,正代表了大乘佛教这一最根本的特征。观音的慈悲不同于世俗的爱,她是无缘之慈,同体大悲,即无任何分别,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平等的慈悲。所以,观音在世俗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救世行为,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不论其显示凶相还是慈相,都是观音悲慈与智慧的体现,即所谓“悲智双运”。
而在中国民间,观音的品格已完全世俗化了。除了神通广大之外,观音在心境上已与一般世俗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民间有关“歪脖老母”的传说中讲:“他(指观音――笔者注)在西方极乐世界里是享有盛名的。但到了后来,他就骄傲了,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目空一切。当童子向他报告有人对他的教法提出批评时,观世音一听,吃了一惊,心想:这个人能比我还高明吗?”在这种心态下,观音对向他提出批评的人自然不会客气。“观世音提起宝剑就追。追了没有多远,果然见前面有一个瘦道人在大摇大摆地走着,还不时地朝观世音冷笑。观世音一见,气上加气,追上前去,也不搭话,举剑就砍。”(顾希佳,《菩萨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页30-31)在这里,观音完全是以世俗人的心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有些方面甚至呈现出恶人的暴虐之气,而这与正规佛教关于观音菩萨悲智双运的理论是截然相反的。
第五,从观音的神通来看。根据印度正统佛教经典记述,观音菩萨修成正果之后,呈现出慈悲与智慧的统一、观性与观音(亦即观相)的统一、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神圣与世俗的统一、威严与慈祥的统一等等(参见:拙作《试论观音所证的法门》,〈普门〉1997年7月号,页32-34)。 其中最关键的是三条:智慧、慈悲、神通,三者互为依傍,缺一不可。其中神通又可分为三种,分别可称为神通之力、显化之力、感应之力。神通之力指观音菩萨具有凡人和小乘四圣所达不到的一种奇妙之力,依据此力,观音的眼、耳、鼻、舌、身、意均已超出凡俗能力范围,成为无所不能的圣者。显化之力指观音为救度不同的众生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随时变化其身,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身相来,佛经中称此为“自在神力”、“方便之力”、“无作妙力”。感应之力指众生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无论遇到什么苦难和麻烦,只要他能以虔诚之心,按照观音法门的修持仪轨而进行一定的称名、诵咒、念经、礼拜、供养等宗教活动,观音菩萨就可立即察觉到什么地方、什么众生遇到了什么苦难,从而通过显露真身妙相、化作凡间俗相或在冥冥之中施展法力等方式,使受苦众生获得解救(参见:拙作《略释观音法门》,《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页3-6)。
民间受道教求签问卦传统的影响,在把观音拉入道教神灵体系的同时,还将预测吉凶的职能赋予观音。当然,观音具备非凡神通,对于预测吉凶之类的事情自然不在话下。但印度正统佛教认为,众生命运的好坏全由自己的善恶之业决定,也就是说,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些经典对此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以说明今日的某种命运乃昨日之某种心行导致,今日之某种心行又将会导致明日的某种境遇。所以,欲知未来命运如何,看看今日所作所为就行了。因此,佛教反对在命运问题上的各种无知和侥幸心理,不提倡预测未来吉凶祸福,反对道教的求签问卦等占卜活动。可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佛教的这些原则已失去了约束之力,受道教卜卦习惯的影响,中国民间逐渐把观音塑造成一位预卜未来、指点迷津的大神仙,形成了解疑释惑型观音信仰形态(参见:拙作《试论古代观音信仰的四种形态》,《南海菩萨杂志》,1998年第1期,页28-33)。宋代洪迈的《夷坚三志》辛卷五《观音救目疾》条记载,某王氏母家中敬奉观音,“有疑则卜,厥应如响”。至于如何来卜,则不大清楚。
在观音神仙化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了“观音签”、“观音课”、“观音阄”等预测方法。观音签即置于观音像前的竹签,求签者在观音像前焚香、供养、礼拜、默祷,然后摇动签桶,求出其签,以示吉凶,或解疑惑。观音签有两种,一是“一百签”,一是“一百三十签”,前者出自浙江杭州天竹寺的观音院,后者出自越之圆通寺(〈释门正统〉卷3)。其中一百签近年还在社会上流行。据说“观音灵签向来以灵验著称,只要诚心祈求,自有灵验”(有闲居士,《观世音100灵签精解》,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1994年1月,《前言》第1页)。观音课分三十二种,每一课代表一种预测或答复。其卜法是取五枚钱币,一面代表金木水火土,另一面代表空白,使用时把钱币在手中摇几下,心中默念观音圣号,观想所问之事,再将钱币掷于桌上,依顺序按金木水火土和空白的组合,索取三十二课中的一课(参见《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第1-2页,佛陀教育基金会2001年8月版)。观音阄即在竹、木、纸片上提前写下某种文字或标下某种记号,然后将其遮隐起来,或捻纸成丸状,在观音像前礼拜供养默祷,然后拈取其一,以所取者为凭,卜测吉凶祸福或裁决某事。
地藏菩萨显灵范文第4篇
炳灵圣境
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佛事活动,不仅将许多窟龛内的早期壁画进行了密宗内容的刷新重绘,还把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上寺和洞沟地区。凿塔建寺,发展僧众,并先后创立了嘉杨隆珠、嘉杨沃色等六大活佛转世系统,遍及周边大小60余座属寺,成为名噪一时、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文物陈列馆陈列出的清代道人画家临摹的一幅《炳灵寺弥勒圣地图》布画以较为写意的笔法,详尽地描绘了当时亭台楼榭、殿宇绵延、灵山秀水、舟船不绝的炳灵寺寺院繁盛景象,几乎一一对应了炳灵寺今天所有的寺院遗迹,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金铜造像
藏传佛教分为显宗和密宗,而习惯上视密宗为圣教精髓,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为便于随时随地观像修持,工匠们制作了大量精巧轻便的小型造像。这些造像依据经典中规定的仪轨比例,在尺寸、造型、身姿、手印等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各类佛、菩萨或金刚明王等的密宗造型变化万千、神秘诡异。创作材质也更加丰富,炳灵寺的金铜造像堪称这一题材的代表作。
金铜造像是以黄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镏金的佛教造像。炳灵寺陈列的镏金铜质或铜造像题材有诸佛、菩萨、明王、护法、高僧大德、佛塔等,工艺精湛,造型奇特。佛像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如来、弥勒等,平均高度为二三十厘米,均螺髻高耸,坐势挺立,神情庄重;手结契印或托钵,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宗教色彩浓郁,具有典型的藏传佛教仪轨像特征。
菩萨多为丰乳细腰的女性形象,其中以观世音菩萨的各种造型尤为突出,有八臂观音、四臂观音、水月观音,以及观音为救度众生幻化成的绿度母、白度母等。绿度母全身绿色,手持莲花,坐势优雅舒展。佛经中称她能解脱人间的狮难、火难、蛇难、水难、牢狱难等八种苦难,所以,又称其为救八难度母。藏族历来将文成公主看作是绿度母的化身。另展出的一身泥制白度母坐像,头戴花蔓冠,左手持一曲颈莲花,右手掌心向外作与愿印,双手、双脚各长一眼,面部又长三眼,俗称七眼女,是藏族人心目中尼泊尔尺尊公主的化身。
金刚一般是男、女二人合抱双修的形式,俗称喜金刚,且多面多臂,手持各类法器,形象狰狞怪异。牛头人身的大威德金刚,头戴骷髅冠,怀抱明妃金刚起尸母,全身,造型奇特夸张,据称是文殊菩萨为降伏阎魔王幻化而成的愤怒像。胜乐金刚四面十二臂,手持手鼓、金刚钺刀、三叉戟、颅碗、骷髅杖等法器,右脚踩印度死神迦梨的胸部,左脚踏印度阎魔死主之头,象征着他的修持可以消除普通的生或死,是无上瑜伽母续中的经典造型。
护法像面目狰狞凶煞,神情威严恐怖。其中的一身吉祥天母像,俗称骡子天王,头戴五骷髅冠,手持饮血颅器,身着人皮,侧坐于行走在尸林血海中的骡子身上。那人皮据说是其亲生儿子之皮,象征着大义灭亲。其所骑骡子可于天界、世间、地下遍走无碍,骡子前后各有一狮头人身和象头人身的随从。相传吉祥天母原是一位异常凶残的女神,专以啖人饮血为业,后被释迦牟尼降伏,以其显赫的威力成为密宗中最重要的护法之一。这尊观之令人悚然的造像充分彰显了藏传佛教神秘的宗教色彩。
北方毗沙门天俗称财神,又称黄布禄金刚,是藏教各教派普遍尊崇的财神。炳灵寺的财神像,除见于洞窟壁画外,展出更多的是镏金铜像,神情微怒,全身金黄色,腹部凸起,躯体肥满。左手抱口含宝珠的吐宝灰鼬,代表财宝;左脚踏白色海螺,象征着他能入海取宝。整体造型准确,个性突出,既展示出财神雍容富贵的外形,又显露着其作为佛教护法威慑逼人的气势。
镏金高僧大德铜像,也是炳灵寺文物陈列馆中不可或缺的题材。出现较多的有宁玛派祖师莲花生、袒身披发苦修状的米拉日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等,造像身姿各异,特征鲜明。他们既是对藏传佛教的发展革新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一代宗师,又以精深的佛法和出神入化的神通力被众多的信徒视为在世活佛,具有极高的威望。
镏金铜塔,在方形或圆形的基座之上,起一个覆钵,正面开龛,用于盛装舍利或高僧骨灰,顶部有13层相轮及刹顶,与印度堵坡墓塔有近似之处。展出的另一座宋、元时期的石雕仿佗伽耶塔,四面雕有佛、狮子、花卉等,两侧各开一小龛,龛内又雕一佛。造型独特新颖,雕饰逼真细腻,风格别具。
木雕造像
炳灵寺文物陈列馆的木雕造像有佛、弟子、菩萨和护法,大多为明、清时期的作品。这种木质造像在佛教寺院并不多见,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般经制坯、雕凿、刮灰、铺苎、髹漆、贴金、绘彩等阶段。因其均为手工制作,故刀笔细腻,造型灵动,形态万千,少有雷同,又经烟火熏燎,极富沧桑感。展出的一身高约89厘米的弥勒菩萨立像,全身涂以金粉,头戴五智冠,身体两侧雕满缠枝花叶,腰部饰宝珠璎珞,显得华美优雅,气度不凡。双臂一上一下似舞蹈状弯曲,手做契印,胸口开一小洞,内置宗喀巴大师像,谓之“佛在心中”,这是炳灵寺文物陈列馆的镇馆之宝。
地藏菩萨显灵范文第5篇
佛教肇始于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佛教的传播,除通过佛经文字外,还以佛教艺术的形式传播。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造像艺术从西域传至中原的中枢,自西晋开始就成为北方佛教传布的中心之一。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佛教艺术随之兴起。南北朝时期,长安不仅是佛教传播的中心,更成为佛教艺术的重镇。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隆盛,作为都城的长安,佛教艺术达到鼎盛。因此,西安及其周围地区留下了大量历朝历代的佛教艺术品。
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佛教造像以单体尊像为主,时代跨越北魏至明清各代,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展示了不同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风貌。造像种类主要有造像碑、造像塔、背屏式造像、龛式造像、单尊造像等。其中造像碑是佛教造像的一种独特形制,它将中国传统的石碑造型与外来的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即借鉴石碑外形,再于其上开龛雕凿佛像,同时刊刻发愿文、供养者姓名等铭文,形成了造型艺术与文字题记相结合的独特样式。造像碑在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为民间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陕西地区最早的造像碑是耀县药王山北魏始光元年(424年)魏文朗造像碑,这亦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佛道合刻造像碑。
碑林收藏的造像碑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方柱形(或扁方形),一种是碑形。方柱形造像多为平顶,于两面或四面开龛造像,有单龛和多龛之分,在佛龛四周通常雕刻有建筑、供养人、伎乐飞天、狮、龙、虎等图案,佛龛及各种图案的空处再刊刻发愿文及供养人姓名。造像主尊以释迦牟尼为主,另外还有释迦和多宝并坐像及弥勒像等。碑林所藏北魏熙平二年(517年)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就是方柱形造像碑的典型,它也是一尊佛道合刻造像碑,正面开圆拱形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像,龛楣饰火焰纹;背面雕刻头戴道冠、手执羽扇的天尊像,造像形式模仿佛像,面相清秀,衣纹细密流畅。同属这一类型的还有北魏田良宽造像碑,亦是四面开龛。这种佛道合刻的造像碑是陕西关中地区造像碑的特色,体现了佛道交融共存的状态。碑形造像碑则更多地模仿了汉代以来石碑的形制,多作圆首,并于碑首雕刻螭龙。如1959年陕西华县出土的北魏朱辅伯造像碑,碑首雕刻螭龙,碑身开三层佛龛,布局丰满,藻饰华美,雕刻精湛。
这些北朝造像碑上的题记内容广泛,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如其中由关中地区鲜卑、羌、氐(di)等少数民族供奉的造像碑,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很多发愿文中都有涉及当时社邑、家族、佛教组织等情况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这些铭文的书法古拙质朴,别有意趣,亦为人们所珍视。
造像塔可分为单体和多层两种。如1949年西安北郊查家寨出土的北魏景明二年(501年)四面造像,外形大致呈正方体,顶部和底部平整,四面开龛,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四周配有千佛、力士等形象。根据其形状推测,该造像原本应是多级造像塔中的一层。
此外,碑林还藏有不少背屏式造像,这种样式亦是北魏时期的主要造像形式。如北魏皇兴造像(471年),正面圆雕交脚弥勒像,作波纹高肉髻,面相丰满,隆鼻厚唇,身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厚重交叠,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其身后为舟形背光,雕刻有莲瓣纹、火焰纹及化佛等图案。背光后面以减地平雕的手法刻七层佛传故事,每个故事以方格分割,颇类连环画,画面丰富,造型生动。又如北魏和平二年(461年)释迦坐像,佛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施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并敷搭偏衫,双目下垂,神情宁静、端庄。两侧有胁侍菩萨,身后为刻饰精美的舟形背光,背光后而亦刻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与皇兴造像不同的是,和平二年造像采用了浅浮雕的技法雕刻,画面没有分格,但布局丰盈有序、构思巧妙,线条飘逸富有动感。特别是其中“婆罗门八人乞象”佛本牛故事,在单体造像中非常罕见。这两尊背屏式造像可谓北魏早中期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见,关中地区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多以乡土气息浓厚的造像碑以及民间雕造的小型造像为主体,并灵活运用了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多种雕刻技法,造像题材多样,藻饰华丽,反映了关中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风貌。而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及其演进过程又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即北魏早期的作品均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特点,至北魏中晚期逐渐汉化,出现了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秀骨清相的佛像样式。
北周至隋是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除了造像碑和单体小型龛式造像继续在长安地区流行外,大型圆雕单体造像骤然增多,这与北周时期高官显贵崇信佛教、大造佛寺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了十余件北周至隋的大型佛、菩萨圆雕立像,其中2004年5月在西安东郊灞桥区湾子村出土的5尊大立佛堪称这一时期的精品之作。因其中一尊佛像座上刻有“张子闻睹佛法,敬造释迦玉像”等发愿文,并有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的纪年,由此可以确定这5尊造型相似、风格相近的立佛当为北周所雕造的释迦佛像。这5尊大佛连座高度均在2.5米左右,应为当时寺院所供奉的造像。这些造像一改北魏的清秀面貌,变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螺髻低平、腹部鼓挺的造型。从袈裟样式上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为北魏中期秀骨清相式佛像的延续,只是体态变得壮硕;另一类着通肩大衣,袈裟轻薄贴体,衣纹简练,具有秣|罗样式风格(以古代印度阎牟那河流域的秣菟罗国为代表的佛教雕塑艺术)。这几尊北周大佛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这种在犍陀罗(古代犍陀罗即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佛像中常见的姿态在北周长安地区普遍流行,而在其他地区却很罕见,成为北周长安地区的典型样式。同时这批佛像雕刻技法纯熟,精湛,为研究北周佛像的特点提供了新的依据。再结合西安北郊等地新出土的北周佛像综合观察,修正了过去对北周佛像笨拙、粗疏的印象,从而也提醒我们应该对原本定为隋唐时期的某些大型无纪年佛像加以重新审视和认定。
与北周的大型立佛像相对应,碑林还收藏了多尊北周至隋代的大型菩萨立像。这些菩萨像高度均达两米以上,形体壮硕,装饰华丽。如2004年西安北郊岗家村出土的观音菩萨立像,面相圆润,形态丰盈,腹部微挺,头戴华冠,颈饰项圈,胸前佩穗状璎珞,肩臂之间披帛缠绕,装饰繁复华丽,雕刻精 致,体现了北周菩萨像的典型特征。隋代菩萨像沿袭北周风格,在平顶华冠的造型基础上,使发髻渐出,腹部平缓,体态多显轻盈、秀美。这些北周至隋代的佛像及菩萨像对外来因素进行汲取和创新,形成了佛教造像的“长安样式”,对周边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唐代佛教艺术之先风。
唐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佛教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普及。长安作为都城,寺院林立、宗派纷呈,造像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峰。佛教造像艺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从外来形式向中国本土化演变的过程,至唐代终完成了这一历程,形成了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新的艺术风格。综观唐代造像,已凸显出庄重典雅,雍容华美的气度,造型上更加注重写实,形象生动自然,更具人情味。这一时期,造像题材也更为广泛,不仅有佛像、菩萨像,还出现了单尊天王、力士等圆雕造像。这些造像身躯健美,体态匀称,神情庄和,佛陀的庄严、观音菩萨的优雅、天王力士的威武,充分展示了长安佛教造像艺术的样式与风格。如碑林所藏唐代佛坐像,结跏趺坐,高髻螺发,面部方圆丰满,眉目端庄,表情自然、恬静。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僧人贴身穿的上衣),衣纹线条疏缓流畅,造像工艺精湛,堪称盛唐时期的典型之作。又如1952年西安东关景龙池出土的唐观音菩萨坐像,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型莲座上,面部雍容,头挽高髻,戴宝冠,冠前有化佛,手执莲蕾,胸前佩璎珞珠玑,披帛自两臂间缠绕自然搭于台座,莲座下雕刻6组伎乐图像。菩萨像整体造型丰满华丽,雕刻精致,堪称完美。西安火车站出土的唐菩萨立像,整体用汉白玉雕成,石质光洁细润。菩萨身姿婀娜,略呈扭动之势,腹部袒露,项饰华美,披帛自然交错系于腹前,腰腹间肌肉微微隆起,形体更趋于女性化,颇具韵味。菩萨像的头、臂、足均已残断,却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再如1974年西安西关王家巷出土的白石力士像,力士右臂高举,怒目圆睁,赤脚踏于岩石之上。上身袒露,下着短裙,显露出全身结实饱满的肌肉和硬朗的线条,彰显着力度之美。该造像雕刻逼真、细微,富有动感。
1 959年在西安东北隅唐安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唐代密宗石刻造像,可谓唐代造像中的精品。这一组造像共11尊,有宝生佛、文殊菩萨、不动明f、马头明王、金刚造像等。这批造像严格按照密宗造像仪轨而雕刻,形象各异,造型生动。如不动明王像,明王呈忿怒相坐于岩座之上,发髻高耸,独辫垂向左肩,右手持慧刀,左手持I(juan)索,形象成猛。马头明王像则为三头八臂,三头均显忿怒相,头光正中有一马头,已残缺;八臂或作手印,或执法器。工匠根据造像规制的需要,将多头、多臂巧妙安排,使之井然有序又富于变化。文殊菩萨像,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姿态优美,饰物华贵,又不失清秀典雅。菩萨头像,双目微合,眉目细长,面容丰腴、饱满,神情静谧、安详。这批密宗造像雕刻水平极高,有的造像上还残存有彩绘、描金的痕迹。根据造像的组合来看,应是当时在寺院按曼荼罗设坛供奉之像。印度密宗自唐初传人中国,至开元年间经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设坛传法,形成密宗一派,并逐渐隆盛。但长安地区遗存下来的密宗造像数量并不多,仅有个别单体造像出土。如西安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的唐十一面观音菩萨头像,白玉石雕成,观音面相丰润,闭目合唇,口含笑意。束波纹高发髻,在高髻的四周残存有6尊小观音头和一尊化佛,均面容丰盈,神情恬静。每一尊小观音的宝冠正中又刻一尊小化佛,雕刻细致入微,韵味悠长。十一面观音的样式在目前发现的唐代石刻造像中较为罕见。这批藏晶是研究唐代密宗造像弥足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