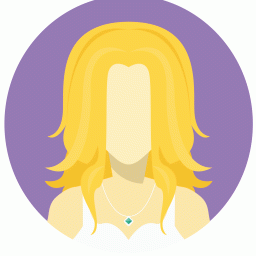童话和哲学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童话和哲学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咋一看,童话作家安徒生(HansChristianAndersen)与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irenKierkegaard)除了两人都生活在19世纪的哥本哈根,都是享誉世界的丹麦作家外,不可能有太多的联系。童话故事与哲学能有什么瓜葛呢?创作出《皇帝的新装》、《丑小鸭》、《海的女儿》(TheLittleMermaid)、《冰雪王后》的人和撰写《非此则彼》(Either/Or)、《恐惧与颤栗》(FearandTrembling)、《焦虑的概念》(TheConceptofAnxiety)、《致死的疾病》(SicknessuntoDeath)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全世界都庆祝其200周年纪念日的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故事大王和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我最喜爱的哲学家评选(可笑的1.65%的投票率)中排名第14位的苛刻的路德派教徒联系在了一起呢?
迪纳·伯奇(DinahBirch)在记载中(2005年5月20日)声称安徒生对那些能够超越“理性价值”的读者特别有吸引力,相反那些“充分相信逻辑规则的人可能对他充满敌意。”她说对安徒生作品特别不以为然的克尔凯郭尔拥有一颗被逻辑冷酷的心,甚至不能对《海的女儿》或者《丑小鸭》中表现出的痛苦做出反应。她说,他觉得“安徒生没有任何歉意地直接从儿童的自我中心转移到虚构的故事中去侮辱了他成人的判断力。”所谓的“童话故事”在他看来是“粗俗的,或许是对艺术尊严的背叛。”那种认为该哲学家不能欣赏孩子想象力的精细复杂,是个孤僻的老笨蛋的想法或许能赢得很多人的喝彩,但并不符合克尔凯郭尔及其著作的客观事实。
他当然是哲学家,不过是没有哲学味道的哲学家。他讨厌抽象观念,总是更喜欢曲折多变的、主观性的喜剧,而不是系统的、缺乏个人色彩的理论。他在其中一次俏皮话中写到如果我能见到理论体系,“我会像别人一样愿意屈膝跪拜,”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成功。有一两次我几乎就跪下来了,就在我以免弄脏裤子把手帕放在地上的时候,向理论家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我问“请坦率告诉我,理论彻底完成了吗?因为如果是,即使弄脏裤子我也要跪拜这个理论。”但是他们总是回答说“不,恐怕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体系再次迟到,我的跪拜不得不再次推后。
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完成的体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体系,克尔凯郭尔怀疑难怪古代哲学家总是找出各种慌乱的借口让我们再过一天回来找他们。他说,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是从来不可能在思想进步过程中被清扫出去的,“不管我们能从前辈中学到多么多的东西。”
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从前人那里学来的,那就是真正的人性。在这方面,每代人都是崭新的,其任务和前一代人的任务一样,不会走很远,除非前辈人碰巧逃避了自己的职责,欺骗了自己。没有一代人是从前辈人那里学习如何爱,没有一代人不是从头开始的,每代人的任务从来不会比前代人更小,如果任何人想和前人不一样,不愿意与爱同行,希望走得更远,那纯粹是空洞和愚蠢的胡说八道。但是许多人很难把自己对普遍进步的信仰抛到一边,他们总是说“我们要继续前进,要走得更远。”如果对前进的狂热是当今时代典型特征的话,那也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了。
取得进步的愿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默默无闻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过“你从来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他的一个学生没有坚持这个观点,而是更进一步,补充说“你甚至不能走进河流一次。”
为了超越老师,这个学生用乏味的、绝对静止的确定性替换了精炼的对变化普遍性的认识。克尔凯郭尔感叹到“可怜的赫拉克利特,可怜的赫拉克利特,怎么拥有这样的学生。”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现代崇尚进步的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就像赫拉克利特的学生一样。他们对脆弱性、不可预测性、和哲学眼光的怪异性缺乏感觉。对无休止进步的渴望让他们想象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个人生命的极限,曾经被勤劳的祖先学习的人生教训现在可以拿来阅读,但不必要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克尔凯郭尔在早年就认定战胜他那个时代无休止的哲学乐观主义的最好武器是幽默和讽刺,而不是理论上的辩论。当然有很多嘲笑哲学辩论仲裁者的前例。比如,蒙田(Montaigne)的随笔,或者从霍布斯到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和边沁(Bentham)嘲笑真理刻薄检验的英国传统。但是说到克尔凯郭尔,他是在哥本哈根大学著名的学位论文“论反讽的概念——对苏格拉底的反省”(TheConceptofIrony,withcontinualreferencetoSocrates)中详细阐述这个观点的,说利用笑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源头。
哲学家总是把苏格拉底作为他们传统的创始人,但是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说到他特别的幽默感,哲学家们一直有个盲点。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个讽刺家,他的教学是在讽刺所打开的内外或者真正的意义和虚假的意义之间的鸿沟中进行的。讽刺如果不是故意地掩盖或者欺骗的话,至少也涉及对自己观点一定程度上的缄默和节制。那些陶醉于进步和明晰的哲学家肯定把讽刺看作“等同于虚伪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能容忍讽刺,除非能把讽刺局限在弄清一些初步的误解或者让读者做些准备活动然后再谈论坦率和字面的系统观点的特殊场合。但是在试图把讽刺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忽略了某些种类的知识包括其中最重要的知识并不符合确定的或者积极的模式的可能性。
他们忘了苏格拉底本人从来没有展现自己的观点,更喜欢以辩论普遍智慧的伙伴或者讽刺一切的形象出现在雅典公民的面前。就好像他没有任何独特的观点,没有个人的信念或者信仰,只是狡辩的伎俩和伪装的保留剧目,运用这些他可以逼得挑战者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观点,不得不承认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为止。克尔凯郭尔提醒我们,苏格拉底式讽刺家否认真实的自我就是要“用诗一样的方式创造自己”,保持怀疑的火焰,并让它燃烧地更加明亮。苏格拉底的真正哲学,像耶稣的真正宗教一样关键在于丢掉自给自足的幻觉。“如果我们需要警惕讽刺是个诱惑,那么我们也必须称赞讽刺是个向导。”
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最早的哲学教师的原因是他一直是个讽刺家。他像只轻盈模糊的蝴蝶,在学生眼前飞来飞去却总是躲避他们,让人着迷、却并不盛气凌人,直到彻底地让他们感到困惑后离他而去为止。他认识到没有人愿意理解只是从老师那里捡来的哲学真理,他也知道老师最不应该渴望的事情就是来自学生的喜爱和感激。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苏格拉底的实质是学生能够摆脱老师,苏格拉底的艺术和英雄主义就是他把学生放在可以一脚把他踢开的位置。”成为哲学家就像成为基督徒一样微妙,同样伴随着自豪,满足和自我欺骗的危险。关键是如何开始。克尔凯郭尔在另外一个讽刺性的话语中说“我要是能找到一个老师就好了。”但是他说的不是一个可以给他讲授古代语言或者文学或者哲学史的老师。“我要寻找的老师是能够用不一样的、模糊的、让人怀疑的方式给我讲授关于存在和人生的模糊的思考艺术的人。”
年轻的克尔凯郭尔希望成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模糊老师,当然,区别在于他要通过文学作品而不是口头语言来达到这个目标。他要创造出作家的技巧颠覆人们的偏见,留下陷阱门自己逃脱,让读者们留下挣扎思考他们到底是谁,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他写到“拥有自己观点对我来说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它的前提那就是良好自我感觉的意识和存在的安全感。就像在这个地球世界拥有妻子和孩子,对那些不得不整天忙碌却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说是无法得到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的主要著作是整个哲学界最独特的发明,轻松、好玩、矛盾、挑逗性的笔名。历史学家们一直觉得要解释什么东西激发了这些非常困难。他可能是受到作家斯特恩(Sterne)或者狄德罗(Diderot)自传体小说的影响,可是好像没有证据显示他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对舞台的着迷好像也与此有关,不仅是他在《非此即彼》中写到的莫扎特歌剧,而且是他在《重复》(Repetition)中写到的访问柏林时喜欢的平民滑稽戏。但是我怀疑谜底离家乡更近,是在他与安徒生著作的尴尬关系上。
哥本哈根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仍然是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城。所以克尔凯郭尔与安徒生相互认识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街上见面了会点个头问声好。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相互认识,但是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他提到在1837年的一次相遇,但显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是反叛的年轻一代的成员,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几乎有天壤之别。安徒生1805年出生于外省欧登塞(Odense),母亲是文盲、洗衣女、嗜酒如命;父亲是手艺高超的鞋匠,可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留下11岁的安徒生自己谋生,来到哥本哈根闯天下。(据说他还有个姐姐在首都当妓女,虽然安徒生更愿意说他是独生子)
克尔凯郭尔则是哥本哈根一个虔诚的商人的第7个孩子,该父亲活到81岁,总是在经济上接济儿子,留下足以让克尔凯郭尔衣食无忧,恣意享受的大笔遗产。1837年见面的时候,克尔凯郭尔24岁是仍然在父亲影响下的学生,除了在学生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无关紧要的小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安徒生当时32岁,已经出版了14本书,创作淳朴的浪漫风格的诗歌,欧洲游记,而且还有长篇伤感小说,他已经出版了名字为《不过是个闲人》(OnlyaFiddler!)第三本小说,而且几乎成为国际著名的多产作家,他的小说很快要被翻译成英语,一个派生的诗歌“闲人之歌”(TheFiddler)很快要被德国作曲家舒曼(RobertSchumann)谱曲,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好作品。
但是安徒生对年轻的克尔凯郭尔感到疑惧。除了讨厌他无忧无虑的财富外,安徒生作为作家也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作品别人到底怎么评价。回头看看,他认为克尔凯郭尔已经瞧不起他,但是注意到“从那以后,我对这个作家有了更好的了解,他见我的时候总是很友好,很敏感、很精明。”1848年,安徒生赠给克尔凯郭尔两卷本作品选,上面写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拙著,我现在没有恐惧和颤抖地奉上,毕竟是点东西。”第二年,克尔凯郭尔回赠安徒生他的《非此即彼》第二版,安徒生回信说“非常高兴收到你的大作《非此即彼》,你或许明白,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根本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友好。我现在明白了,上帝保佑你,谢谢,谢谢。”
1837年,克尔凯郭尔可能就已经知道安徒生的巨大成功,他很可能也阅读过他的部分小说或者诗歌。也可能了解到给安徒生带来声望的清澈的童话故事。《公主与豌豆》(ThePrincessandthePea)《拇指姑娘》(Thumbelina)出版于1835年,《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出版于1837年,几个月后出版《不过是个闲人》。人们很想知道他在阅读童话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或许把安徒生描述的没穿衣服的皇帝等同于二世纪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nus),此人提出精神自我满足的异教徒哲学,这是克尔凯郭尔一直觉得愚蠢没有意义的。或许当他对丹麦教会发动猛烈抨击的时候,看到自己扮演着小男孩的角色。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克尔凯郭尔关注安徒生的童话,有可能他和同时代人普遍的看法一样,认为这些作品是艺术上的偏离,是安徒生才华的滥用。但是他确实尽很大努力研究了《不过是个闲人》,这是三卷本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名叫克里斯蒂(Christian)的小男孩的故事。他小提琴家的天赋注定因为贫穷给断送了。克里斯蒂的故事还夹杂着一个犹太人小女孩诺米(Naomi),她的天赋同样被浪费掉了,虽然毁灭其前途的不是贫困而是过多的财富。克里斯蒂和诺米的对比可以拿来作为安徒生和克尔凯郭尔情形的比喻,让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非常有趣,不过同样特别地不准确,经不起推敲。
安徒生可能声称他的小说“是在艺术上的才华和恶劣的环境艰苦搏斗中产生的精神成果。”但是这不能作为自我放任的冗长罗嗦的借口。尽管该书包含了同样卡夫卡式清晰的段落,就像他最好的童话故事中那样,克里斯蒂企图从哥本哈根步行到瑞典穿过已经开始融化的冰冻的大海。或者比如诺米化装成男的,精心贴上假胡子,从哥本哈根逃出来等段落里面充斥着太多世界对待天才少年残酷的作者的感慨,根本没有升华进入纯粹艺术创作的领域,或者达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讽刺的水准。
安徒生自己最终也对《不过是个闲人》不满意,但是正如他在自传中提到的,该书宝贵的地方在于让他和克尔凯郭尔建立了联系:
小说《不过是个闲人》很快就给我们国家年轻的天才克尔凯郭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在街上碰见他时,他告诉我要给该书写个书评,那我会比我对从前的书评更加满意,因为他说那些人都误解了我。
克尔凯郭尔花费一年中最好的时间写书评,可能像小说本身一样体现大量的创造性努力,不管怎么说是克尔凯郭尔第一次持久的实践他作为作家的才华。最初委托他写文章的刊物到了他写完的时候已经倒闭,所以他安排作为小四开本书出版,里面包含一些前页,接着是79页内容丰富的“小说家安徒生”正文。据说安徒生在该书出版前一直迫切期待它早日面世,按照传记的说法,实际出版后,他对该书不是特别高兴。
批评文章出来后,根本谈不上让人高兴。首先,它是作为一本书出来的。从语言上的黑格尔式笨重迟缓,难以卒读的特征来看,我肯定那是克尔凯郭尔写的,有人开玩笑说只有克尔凯郭尔和安徒生从头到尾看完过这本书。
评论确实沉闷迟缓,虽然克尔凯郭尔比黑格尔在处理长句子的本领上强多了。但是决不像安徒生暗示的那么糟糕。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安徒生完全缺乏人生观”是克尔凯郭尔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而不是对作家个人的评判。他的观点是安徒生小说没有表现出一种“人生经历的变体升华”,这是人们期待伟大艺术品应该提供的东西,安徒生的小说缺乏“让小说具备自身重心的深层的统一性。”
一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对勤奋多产成就卓著的作家做出这么傲慢的批评确实放肆。不过,尽管后来有各种谣言,克尔凯郭尔并不是以严格的逻辑家自居,谴责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书评家的作品总是应该像作家一样与别人分享对于创作困难的思考。他的批评不是说安徒生的小说缺乏理性,相反,是批评其“艺术性不足”,保留了过多的观点和主张,讽刺性不够。
克尔凯郭尔认为《不过是个闲人》里面安徒生的成分太多了这个主要观点相信所有读者都是同意的。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安徒生的小说“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小说的创作被认为是截肢,而不是为自身的作品。”它们给人Zwielicht(一种微光或者阴暗的双影光)的印象,其中根本分不清安徒生这个活生生的人和他“叙述的个人意识”的艺术形象,后来的批评家可能称为叙述声音或者叙述角度。克尔凯郭尔继续说“如果缺少人生观,小说要么寻求在牺牲艺术的情况下慢慢产生一些理论,要么与作者的血肉进行确定的或者偶然的接触。”安徒生作为小说家的麻烦在于他没有能“把艺术和自我分开”,把他的书当作香肠皮,往里面塞进去太多的愤怒和怨气,是“对人生让人消沉的思考的大杂烩”。小说包含了“作者确定人物的残渣”,好像无耻的第三者或者缺乏教养的孩子,不断在不适当的地方打断别人的谈话。按现在的形式,安徒生这一类作家除了给我们“自身性格的没有艺术性的堆砌”以外什么都没有。
克尔凯郭尔尤其对安徒生对待孩子的态度没有深刻印象。比如在描述克里斯蒂来到舞厅,试图赢得人们对他的音乐天赋承认的时候,安徒生写到“他手里拿着帽子礼貌地往各个方向鞠躬,但是接着加了一句“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这个意外添加的评论让读者纳闷是谁在说这些话,“谁发表了这个评论?”他问“肯定不是克里斯蒂说的,那是安徒生自己的观察,肯定是希望舞厅的人赶紧看到这个天才,安徒生又生气了。”即使当时他在文学实践上没有经验,克尔凯郭尔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重要议题,以及文学叙述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谁说的”。安徒生还没有弄清楚描述别人的意识和重复自己的说法是不同的。谈到孩子的时候,他常常采用大人的视角,克尔凯郭尔说“当他描述孩子的时候,”告诉我们小孩子的心灵充满了“小东西”,没有意识到从孩子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小。
我们看不到完全来自儿童意识的话语。相反,他是用生活给大人留下的印象说话,然后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人们不能忘记孩子,孩子的想象力的创造力量,简而言之,他只不过假装男高音,添了高音符号而已。
这是严厉的批评,不过不是不公平的。没有安徒生的辩护者喜欢添加在克尔凯郭尔身上的充满恶意的哲学傲慢的一丝痕迹。该书达到了评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作者提供了下一步应该做的建议。或许可以说是克尔凯郭尔劝说安徒生放弃了长篇小说,专心写短篇童话故事的。
不管安徒生是否从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评论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克尔凯郭尔从写书评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开始写关于苏格拉底讽刺的论文,五年后他才发表第一本真正的著作《非此即彼》,开始其42岁去世前出产30多本内容千差万别的书的生涯。(安徒生在他死后又活了20年,直到1875年70岁的时候去世)克尔凯郭尔正是通过研究安徒生作为小说家的缺点积累了所需要的文学工具,让幽默为哲学服务,谴责了黑格尔的理论著作和安徒生的小说中存在的自我中心态度,学会“诗化”自身成为纯粹的讽刺家。
在经过长达70多页区分真实作者和小说中的作者声音后,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他第一个严肃的文学笑话:他旋转脚跟感谢安徒生为丹麦文学做出的贡献,绝望地加上一句“我想亲口给他说这些话,而不是写下来,因为这样的话总体上很可能被误解。”在写完本来只能口头表达的话结束评论后,克尔凯郭尔继续创作了精巧的前言。前言的签名是“出版商”,声称作者克尔凯郭尔是出版商的“亲密朋友”和另外一个自我,虽然“我们的观点几乎总是不同的,总是在争吵不休,就好像同一个身体里的两个灵魂。”不管怎么说,克尔凯郭尔曾经问他发表这个书评,他即刻准备这么做,“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气急败坏的出版商说“结果他对这个书评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该书不能以“小说家安徒生”为名出版,而是以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的,彻底误导人的题目“违背作者克尔凯郭尔意愿的,仍然活着的作品”出版。
“仍然活着的作品”可以被看作影射出版已经去世的作者作品的做法,虽然也可以指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在他写这本书评的时候已经去世,让克尔凯郭尔成为困惑不已的幸存者。也许还包含一种讽刺,以损害“人生观”的观点为代价。因为只要仍然眷恋这个世界的生活,好像没有人能够真正得到苏格拉底式讽刺家的超然,当然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文学花招。不过很清楚的是,克尔凯郭尔试图从安徒生的错误中学点什么。可以这么说,正是安徒生教给了克尔凯郭尔成为作家的模糊艺术,这个艺术也成就了一名哲学家,虽然可能不是安徒生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