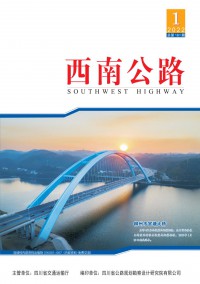西南政法研究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世纪;建国初期;《婚姻法》
一、史料与专著方面
一些重要文献汇编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的内容。主要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等。对建国初期婚姻法实施情况报刊资料的整理主要有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0年编印的《西南政报》、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编印的《西南工作》、以及《人民日报》、《新华日报》、《重庆日报》等报刊杂志。截止目前为止,涉及到该方面的论著有张培田主编的《新中国婚姻改革和司法改革史料:西南地区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培田和张华主编的China Southwest Archives: The Marriage Reform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Pty.Ltd,2007)、李胜渝的《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婚姻家庭制度变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二、学术文章方面
从全国层面来看,史学方面研究主要侧重于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历史过程、妇女解放及妇女离婚引起的自杀、被杀问题、婚姻制度改革等方面。其中,有的学者论述了在新旧婚姻制度的冲突中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并逐渐完成婚姻制度的变革与新式家庭关系的确立。有的学者论述了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第一部《婚姻法》的贯彻实施为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主题内容,对运动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有的学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受和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对固化的婚姻观念和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不可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社会变革。
法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史、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学界普遍认为1950年《婚姻法》是建国初期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但有学者指出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该法律实施的地域性差异。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多关注于社会动员、运动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等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为贯彻落实婚姻法展开的全方位的动员实践本质上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该运动通过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运用典型动员,推动了民众新婚姻观念的转变。这次社会动员的成功,紧抓民心是关键,加强组织调控是保证,结合群众切身利益是基础。另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的变迁是一种国家权力支持下的自上而下的变迁,虽然围绕婚姻自由、家庭财产保障等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多着眼于政治动员、政治认同、国家观念的形成以及国家政党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干预。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的宣传经历了中共从意图彻底破坏父权制到限制、改造父权制的不同策略,显示了建国后民族国家对待性别关系的多元化策略。也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成果较少,主要体现在群体心理的改变上。如庄秋菊的《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于北京工人婚姻观念的变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李巧宁和陈海儒的《中国西部农村婚姻家庭观念与实践变迁――以1950―1953年陕西农村女性离婚潮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从重庆地区来看,《婚姻法》各个角度的研究均很薄弱,主要是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如李胜渝的《新中国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惩处违反婚姻法犯罪的史实刍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6期)及《建国初期西南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考》(兰州学刊,2011年第7期)。另有岳艳斐的《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及刘全的《郑小平与西南婚姻制度变革》(世纪桥,2013年4月)。不少学者依据官方存档的宣传材料,认为婚姻法颁布后得到了切实贯彻,彻底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也有学者从“自下而上”贴近社会下层的视角对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露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底层民众在贯彻运动中有其选择性的主体表达,从而使研究更接近历史原貌。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20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方向
Abstract: In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can be p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beginning and initial stage (before 1937), mature stage (1938~1949), setback stage (1950~1979), and reconstruction and booming stage ( from 1980 up to now). Over the year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by translating western anthropological works into Chinese,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 doing large scale fieldwork,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Ethnology 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etc. While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are thriving, problems like improper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do exist. However, the ever increasing tendency of cross boundary studies and the painstaking efforts by Chinese scholars will certainly rejuvenate and broaden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Key words: 20th century;Chinese anthropology;development direction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20世纪初~ 1937年,1938~ 1949年,1950 ~ 1979年,1980年至今(注: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狭义人类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英美学术界大都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以法、德和俄罗斯为代表,研究人类文化与社会的那一部分学问归为民族学。本文是从狭义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历史进行综述。关于中国内地人类学发展的分期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有分为3个阶段,如周大鸣在“中国人类学的世纪回眸”(出自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中,持三段论观点;有分为4个阶段,如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一书和陈国强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主张分为4个阶段;有分为6个阶段,如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建民等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均持这个观点。 我的分期也是4个阶段,但与陈国强先生和顾定国先生的不同:陈国强先生分为20世纪20年代以前传入传播阶段、30~4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50~70年代分科发展阶段、80年代后宣传提倡这4个阶段;顾定国先生的4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全盘接受西方人类学理论、50年代初苏联模式取代西方理论、毛泽东化、80年代后强调中国模式。)。笔者如此划分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连,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国民政府的重视,出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人们去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复兴成为可能。1949年以前,中国人类学深受西方传统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术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至深,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和文化发展的繁荣,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恢复和重建的阶段。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一
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初至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表现在西方人类学学说的介绍、田野调查的开展、相关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4个方面。
抗日战争之前,西方人类学的许多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1903年)、陶孟和等翻译的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许德珩翻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年)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翻译出版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近20部。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根据西方著作加以编译,写出一些早期的人类学作品,如刘师培《中国民族志》(1903年)、陈映璜《人类学》(1918年)、顾寿白《人类学大意》(1924年)。林惠祥编译的大学教材《文化人类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人类学最初把“原始落后的民族”或“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类学家最初也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1928年夏,杨成志克服了诸多困难,首次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成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1],后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一系列论著。1929年4月底开始,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开展调查,编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是中国人类学家编著的第一部民族志,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1934年10月,凌纯声、陶云逵还对云南傣族、彝族、佤族等进行了调查。1935年,方国瑜调查滇西傣族、拉祜、佤族等,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此外,还有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金秀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等。
同时,有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对汉人社区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在吴文藻、许仕廉、步济时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他们的调查成果由黄迪综合整理为《清河村镇社区》。李景汉主持了长达7年的定县社会调查,他所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3]57-58。
1936年,费孝通对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1个多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后来题名为《江村经济》出版,被认为是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林耀华根据自己家乡的生活经历和对福建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仍然以福建调查为基础,以两个农人家庭的兴衰为线索,用小说形式写成了人类学作品《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再版),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江边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早期中国人类学另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杨懋春写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利用社区研究的方法对家乡山东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著名美国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认为它不仅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而且也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3]59。
1927年七八月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2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内分4组,第一组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成员有凌纯声、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另一个重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3组。人类学研究最初放在考古学组,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
1934年12月,由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凌纯声、商承祖、胡鉴民、徐益棠、何联奎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这是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学会创办了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司长陈念中主持了“全国风俗普查”,他邀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3人负责筹划此事[4]。他们拟定了3年计划,调查项目包括人生礼俗、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岁时风俗、职业制度、宗教迷信、神话故事、道德观念与制裁。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土化”的研究统一起来,既重视少数民族,也关注汉人社区,这与西方人类学最初纯以“原始族群”和“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
第二,中国人类学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传入的基础上创立的,受欧美人类学影响较大。最早传入的是进化人类学派,学者们主要应用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对汉族的古代历史进行解释,但没有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现状进行研究。德奥民族学派、美国历史人类学派、法国民族学社会学派传入较晚,中国学术界除了广泛介绍这些学派的理论之外,着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做了不少实地调查。英国功能学派的传入是更晚的事情,但由于学术界的广泛介绍,并曾深入到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其影响较大[5]。可以说当时西方出现的前沿学术理论均先后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人类学界紧跟国际学术潮流,与国际学术界亲密接触。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处于引用和模仿西方理论方法的阶段。
第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方法,由于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注重历史资料的运用,并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相互印证。如凌纯声在调查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之前,先对古代东北民族和赫哲族的资料进行详细考证,以弄清其发展脉络,“已发今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先声”[3]55。
二
1938~1949年,中国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先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国民政府先后迁都武汉、重庆,西部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政府需要开发西部各省,以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最多,政府亟须了解他们的状况。抗战中,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向西部转移,学者们就地取材,更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发展达到了高潮,其重要标志是开展大量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调查,也有学者个人的调查,其中政府的调查活动最多。
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开始于1929年,大规模调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调查区域主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如火如荼,盛况空前。可将政府进行的诸多调查分为3类:一是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组织自上而下的调查;二是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的调查;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的调查。
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进行调查从1929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这类调查规模最大,积累的资料最多,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文给西南几省地方政府,令各省民政厅负责,民政厅再令各县县长负责,认真调查情况,填表上报。方法是通过对调查表进行汇总,掌握西南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情况。其中,云南方面主要有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和云南傣族调查5类。贵州、四川和西康方面有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4类。
蒙藏委员会是民国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抗战时期蒙藏委员会对云南、四川、西康等西南地区开展调查,出版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中甸调查报告》(1945年)等[6]238-239。1941年,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对川西进行调查,出版了《川西调查记》(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4年编印)。同时,蒙藏委员会对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组织了调查,刊印了《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伊克昭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伊克昭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41年)、《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1941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942年)、《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等。
云南省的边政机构——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1943年成立),聘请民族学家江应梁为主任委员,该机构积极地开展边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制定了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先后写出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中维德区开发方案》、《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等。这些调查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并设计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方案,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贵州省的边政机构——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1945年成立),发行《边铎旬刊》、《边铎月刊》等刊物,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并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其调查成果发表在《边铎月刊》上。
国民政府还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对西部地区进行调查。1938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梁等学者,其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7]。同年冬,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成员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938年,教育部组织了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了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松(潘)理(番)茂(县)边区施教团。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开展调查。同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四川和西康进行调查,后来送交了视察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川康建设方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以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编成《雷马屏峨纪略》,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6]238。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遣康昌旅行团和青康考察团对西康进行调查,康昌旅行团成员朱契写成了《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 中央大学地理系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委托,考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移民垦殖等问题,重点调查甘肃和新疆等地,事后发表了许多著作,丁实存还整理出版了《新疆书目》[6]226。
在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同时,学术机构和团体也在西部地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38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这个机构后来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因此人们称这一机构为“魁阁”。先由吴文藻先生负责,1940年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等人在此工作。
抗战时期,魁阁学者选择云南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又称喜洲)、个旧等地开展调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合著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是代表作。其中《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点睛之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8]。费孝通抗战胜利后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许烺光的《祖荫下》,其影响力与《江村经济》、《金翼》和《山东台头》不相上下,在国外人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云南大学还建立了方国瑜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李田意的《缅甸史纲》、李拂一的《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丛书。
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贵州定番合办定番乡政学院,以定番为实验县,试图对当地少数民族做详细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1939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苗族考察团先后到贵州考察[3]86。1940~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派李桂芳、吴定良到贵州调查苗族和仲家的语言,测量体质[9]。对贵州调查研究规模较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夏大学许多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曾协助政府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1939年春,内政部委托大夏大学调查安顺、定番、炉山(今贵州凯里)等县,最后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每种约20万字。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贵州省民政厅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参加,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经过5个月调查,最终向民政厅上报了调查报告[6]234。
1938年夏季,第一次西康科学调查团对西康进行调查,社会学家柯象峰、民族学家徐益棠等人参加了西康科学调查团,参与西康民族调查。柯象峰后来写出《西康纪行》,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和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上。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馆合组西南文化考察团调查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川康边境地区[4]。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他们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搜集相关物品标本,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文[6]229-230。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10名学生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地区考察,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专家学者个人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中。江应梁于1937年9月到1938年5月间,到云南考察滇西傣族(旧时称摆夷),写成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10]。1937年至1946年,在多次调查傣族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摆夷的生活文化》(中华书局1950年版)、《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印)等著作。1941年,江应梁前往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珠海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他的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1948年由珠海大学印行。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学者在贵州开展民族调查,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收入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再版)。另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出版有《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入了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当时称夷族、罗罗或倮罗)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调查研究成果较多。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著成《凉山夷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有关凉山彝族的研究还有任映沧的《大小凉山倮族通考》(西南夷务丛书社1947年版)、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年版)等。
1938年,李安宅和夫人于式玉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研究。他们的调查长达3年之久,创下了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之最。通过这些考察,李安宅写成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又名《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
1938年冬,任乃强曾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聚居或杂居地区进行调查,撰有《泸定导游》(《康导月刊》第2卷第2~9期连载)。1944年,他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康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后来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和《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1944年夏,林耀华在暑假期间赴西康北部考察。1945年夏,他又带领自己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地区的嘉戎(今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写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和《四川嘉戎》等作品。陈永龄根据此次调查资料,完成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出版社1947年印)。
抗战期间,全国对边疆民族问题更加重视。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学会“以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以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华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1]。本着此宗旨,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出版刊物《边政公论》。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和中国边疆学会;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后,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华西协和大学建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中国边疆建设协会、中国边疆教育委员会、边事学会、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机构。总之,“民族研究之团体在此时期内极发达,重庆一地即有8个单位,其他大都市间,每处必有一、二团体之组织”[12]。
抗战时期,登载人类学文章的刊物增加,除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外,还有《人类学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5]。同时,在大后方兴起了“边疆学”和“边政学”,出版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刊物,较著名的有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疆学会出版有《中国边疆》、《边疆月刊》、《边疆周刊》。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还有《边疆人文》、《边事研究》、《边疆》、《边疆研究通讯》和《西南边疆》等。这些刊物也登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13]。
抗战及战后,西部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调查。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些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人类学调查中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系统搜集全面的民族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这种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的运作机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直接观察、典型调查等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同时,政府调查又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第二,调查种类齐全。其中,既有官方调查,又有学术团体调查和学者个人调查,形成政府调查为主,学术团体及个人调查为辅的局面,并明显带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第三,人类学调查研究与边疆问题结合,形成了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边政学。1942年,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成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他提出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边疆民族的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问题,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14]。吴文藻先生提倡边政学,实际上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尝试。
第四,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达到一个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度”,被国外同行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3]6。
三
1950~1979年,是中国人类学曲折发展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因为在欧美学术界普遍使用,基本理论框架受欧美学术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科体系受苏联影响较大,而苏联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结果,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不再出现,以民族学取而代之,全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或被停办或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并到其他科系。
这一阶段,开展了一些少数民族调查,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有所忽视,而且为了现实的需要,民族研究又长期定格在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划分等方面,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是曲折的。同时也应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研究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5],突出体现在新中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
民族识别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54年,将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和归并,确定了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彝族等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是1954~1964年,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新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仡佬、布朗、阿昌、普米、怒族等15个少数民族,并将一些不同的族群归并到全国53个少数民族中,识别工作基本解决;第三阶段是1964~1978年,于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第四阶段是1978~1990年,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同时对约500万人口的民族成分做了恢复和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作了归并,至此形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结一体的格局。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世界民族学史上仅有的先例,总体上是成功的。通过民族识别,历来不被承认的一批少数民族取得单一民族的资格,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识别的成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州、自治县(旗)提供了前提。
转贴于
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各民族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于是民族学界闻风而起。1956年春,为准备进行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一些专家起草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
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开始,先派出内蒙古、东北、新疆、两广(广东和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8个组,最初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蒙古、藏族、维吾尔、壮、苗、傣、景颇、佤族等20个少数民族。后来调查组增加到16个,调查对象扩大到全国少数民族。调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注:调查分期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42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956年8月到1958年6月,以调查社会形态为核心。调查工作仅两年时间,就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资料1 500万字,其中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成的调查报告有400万字,公开发表的有《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云南西盟卡瓦族(后改为佤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问题》等5篇调查报告。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由于种种原因,编写丛书的工作推延到“文革”以后继续进行。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历时8年,搜集到大量文献资料、访谈资料、实物(文物)资料,同时利用电影手段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从1958年开始,各个调查组开始编撰“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后增加为5种,编纂工作历经30年,到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齐。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1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本),总计400多本,约8 000万字(其中包括辑录的文献史料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一些补充调查报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在中央、各省地方政府领导下,由专家学者组成调查组,对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进行的调查。1958年以前,各调查组往往在调查地待很长的时间,与当地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参与他们的活动,直接观察他们的生活,所得资料又经过当地领导机关的审核,所以比较准确。但从1958 年起,“收集到的资料与前期相比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16]218,原因是“由于调查工作被规定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很多值得调查的问题被忽视或禁止调查;调查报告中充满了政治术语和套话,有用的资料很少;由于各种干扰,即便是可以调查的有限问题,亦常为了诠释经典著作、领袖言论或现行政策而不惜曲解实际问题”[17]。
笔者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国家投入充足的资金,各级政府部门密切配合,调查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的资料比较准确。只是因为1958年后的政治空气紧张,调查报告的编写有了许多顾虑和规定,出现了调查报告中充满政治术语和套话等现象,但有用的资料还是不少的。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调查范围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调查者,对所有少数民族开展广泛调查,调查材料的字数逾千万,这样大规模的田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提供了特殊的经验。
第二,调查研究种类单一。政府组织的调查成为唯一调查类型,学术团体和个人的调查几乎绝迹。由于这时人类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说”,人类学是以民族学的名义存在,而当时中国民族学是在“少数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旗帜下进行的,民族学被片面认为就是少数民族调查,因此忽视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前苏联民族学的方法成为新中国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影响较大。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社会进化论,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18]。
第四,调查方法与过去不同。采用组队的方法,除民族学家外,调查组还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文艺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这是综合性的调查方法。萨尔茨曼认为:人类学调查在“西方学者是孤独的冒险者的方式,而中国学者是‘组队研究,集体写作和联名发表’的方式”,这是中国用自己的田野调查工作经验丰富全球人类学的知识库[16]334。
四
198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重建和兴盛阶段。80年代开始,先后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一些大学恢复和建立了人类学系,并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是这一阶段的特征。
沿袭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的学术传统,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专家对少数民族继续进行调查。其中主要有: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东南部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综合调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省民族学会对该省“六山六水” (注:贵州省的“六山六水”是指乌蒙山、云雾山、霄公山、武陵山、大小麻山、月亮山和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舞阳河流域地区,是苗、布依、侗、水、彝等族的聚居区。)地区的综合调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对怒江地区的调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雅砻江下游及川西北地区有关民族的调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牧区的综合调查和工商业专题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开展的对萨满教等原始宗教的专题调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90年展战略研究和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专题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等。
云南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表现突出。为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2000~2001年,云南大学组织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这次民族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指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19]。其成果是“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7本)。2003年,由云南大学牵头,联合全国14所大学百余名专家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这是为全面了解新中国50余年来各民族发展变化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一项创举。整个调查历时近两年,省内外专家学者组成32个调查组,对全国15个省区32个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且主体民族占80%以上的1个村寨,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调查,内容包括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文化艺术、宗教、遗传、生态环境等。调查成果是出版了“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34本),文字总量1 000余万字[2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调查以县、区、乡为主要调查单位,鲜有以单个村寨为对象。云南大学组织和牵头的这两次民族村寨调查,力图超越过去“广泛的面上调查”,而转入以“典型”、“代表”的村寨为对象进行的“综合调查”,是一种新的尝试,至于调查所得资料的价值,将留待学术史的评断。
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调查,也包括后继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形成热点。
1939年《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以来,江村逐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知晓。费孝通本人自1957年重访江村后,对这个农村社区先后进行了20余次访问,持续研究长达60年之久,先后发表了《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探讨了江村几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正是这些后续性的研究,使江村一直被看作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江村的回访也成了学术史上追踪研究的经典范例。1986~1989年,庄孔韶5次访问林耀华先生《金翼》中的原型福建黄村,并出版了《金翼》的续篇《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
对华北村落的再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戴瑙玛重访40年代杨懋春所著《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的台头村,写出了《重访台头:社区再研究的前景》和《模范村与乡村真实》两篇文章。20年后,潘守永再次走入台头村,发表了《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一个中国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在20世纪40年代对河北、山东的6个村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汇编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依此资料,黄宗智完成了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Duara)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2001年七八月,兰林友在考察了华北6个村之后,入住后夏寨村进行调查, 在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概念,从而对黄宗智(他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他认为村落政治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所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发表了《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对华南名村的再研究主要有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注:1918年、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美籍教授葛学溥对广东潮州的凤凰村进行调查,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境内,葛学溥是最早的一位,而且他还进行了体质的测量。)进行的追踪调查。对凤凰村的追踪调查,使周大鸣对“乡村未来发展有进一步思考,对人民的关注使他很自然从村落聚焦到农民工、乡村都市化”[21]。他对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展现了华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孙庆忠对广州南景镇(注:1948~1951年,杨庆堃任教于岭南大学时,对广州近郊的南景村进行了调查,1959年出版了《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的追踪研究,描述了南景镇半个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村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周大鸣和孙庆忠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从2000年起,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对费孝通主持“魁阁”时期云南的3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进行重访和再研究[22],其成果有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禇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云南大理的西镇成为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张华志从西镇商帮、家族关系和家族企业等方面对西镇进行了延伸性的研究[23]。另外,段伟菊重访西镇,从族群认同角度研究了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24]。
对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福建和广东为代表。对福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惠东地区,1984年,蒋炳钊对福建惠东地区的惠东女风俗进行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开展人类学社区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岞村调查》、《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第一部有关汉人社区的民族志著作。1992年,两岸惠东人协作研讨会论文集《惠东人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闽台惠东人》。同时,开展对福建客家人的研究,成果有《长汀涂坊客家》、《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等代表性著作。
1992~1995年间,王铭铭对家乡福建泉州先后进行了1年多调查,之后出版了《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两部著作。前者以国家社会作为分析框架,以福建溪村陈氏家族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作为叙述架构,力图从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的变迁。后者是基于闽台3个村落的实地考察素材而展开的理论思考。同时,王铭铭先后写了《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文化格局和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人类学是什么》、《漂泊的洞察》、《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和《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等,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和普及有一定意义。
广东地区的调查研究主要有黄淑娉主持的课题“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对17个市县进行调查,1999年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报告集》。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朱晓阳的《罪过与惩罚——下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等,都是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与都市人类学不同的乡村(乡土)人类学。
近年来,中国乡村、农人、乡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学科专家的广泛关注,对汉族农村社会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家的专利,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史专家也开始重视对此的研究。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在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就比较关注具有典型性的乡村个案,其学生的博士论文有张学强的《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莫宏伟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钟霞的《集体化与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等,其中多数已经收入“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出版。他们注重档案资料的利用,同时又注意田野调查,重视口述史料,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族社会研究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汉族社会研究在承袭传统、拓展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一方面将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紧紧把握社会文化变迁这一主脉,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25]。但是也应看到,对汉族社区的调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华南、华北、华东地区,而东北、西北、西南的汉人社区则比较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
五
中国文化人类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目前正在走向兴盛,但是,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并未解决。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同一学科,还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科,近年来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从国际学术界来看,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有变化,早期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以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则正好相反,早期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将民族学包括在人类学中。近10多年来,一些国家的学者都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因此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26]。
中国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也是变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人类学被称为民族学,学科含义是广义的,既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也研究体质。当时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即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只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叫法,文化人类学等于民族学,两个学科没有严格的区分,当时的许多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等同时是民族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学科名称被取消,体质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保留了民族学的名称,这时的民族学含义则是狭义的,而且大多集中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忽视了汉族。从学科名称看,中国文化人类学前70年几乎都被民族学所替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名称才逐渐恢复。人类学与民族学尽管关系非常密切,但重建后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的建立就可见一斑。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但是中国学者认为,从历史和目前的具体情况看,中国民族学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又由于中国民族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把民族学置于人类学下面显然是不合适的”[26],所以,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目前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人类学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汉族的研究上,放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海外华侨的研究上,摈弃少数民族研究,不与民族学争地盘”[27],民族学则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不统一,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归属的混乱。目前,国内有3家权威单位对学科进行分类并定位。首先是教育部的分类和定位。在1990年正式公布,1997年调整后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广义的民族学)被归入法学类,是一级学科,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5个二级学科,把人类学归入社会学类。其次,是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和定位。1992年11月批准、1993年7月实施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民族学(广义)为一级学科,包括7个二级学科,即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学、蒙古学、藏学、文化人类学与名俗学、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学其他问题。这里的文化人类学是指狭义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作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体质人类学则分在生物学的二级学科。再其次,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分类。1994年3月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数据代码表》,规定民族问题研究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列在二级学科,社会人类学则分在社会学下面作为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作为一级学科的广义民族学,往往是“民族研究”的同义词,而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狭义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地位是漂浮不定的。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正确的学科定位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在人类学“销声匿迹”之时,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得到突出发展,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人类学则时而附于民族学之下,时而又被放在社会学之下,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能确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要求成为与民族学、社会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至今学科定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建议把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以“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作为学科名称,其下分若干二级学科[26]。这种建议笔者非常赞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统一、规范的学科分类标准,做出合理的学科定位。
对于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应分3个圈子:第一就是核心圈,即中国汉族的乡土人类学;第二圈是少数民族研究,即民族学;第三圈是海外研究(注:参考徐杰舜、王铭铭:《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前面两个研究圈,是对中国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继承,第三个研究圈体现了中国人类学家在21世纪走向世界的梦想,对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至关重要。
人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改革以来,人们试图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人类学研究出现了自觉的学科整合,形成了诸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如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体育人类学、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专业学会。20世纪90年代后,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这种“学科互涉”将给中国人类学研究带来持续的活力,开拓更宽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蔡家麒.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记杨成志先生滇川调查之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4):25-28.
[2]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导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3]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 1942,1(5、6期合刊):51-63.
[5]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J].民族学研究,1981(1):261-298.
[6]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7]江应梁.民族学在云南[J].民族学研究,1981(1):236-250.
[8]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5.
[9]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J].边政公论,1944,3(2):33-42.
[10]江应梁.江应梁自述[M]∥高增德,丁 东.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311-318.
[11]中国边政学会成立[J].边政公论,1941,1(3、4期合刊):205.
[12]徐益棠.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J].斯文,1941,2(3):5-9.
[13]江应梁.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1983(3):59-65.
[14]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1(5、6期合刊):1-11.
[15]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G]∥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32.
[16]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7]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8.
[18]周大鸣,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M]∥周大鸣.21世纪人类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3.
[19]高发元.总序[M]∥走进村寨——民族调查纪实.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4.
[20]马 京,李菊梅.总序[M]∥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纪实.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6.
[21]秦红增.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3):1.
[22]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2):132-245.
[23]张华志.家族企业和许烺光田野点的延伸性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1):46-55.
[24]段伟菊.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1):39-55.
[25]孙庆忠.近二十年来人类学汉族社会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05(2):83-110.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第3篇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和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玛拉毅教授分别致辞,并作为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西南民族大学共建“民族学与人类学西南研究基地”的合作协议书。张昌东书记在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主题将是对前四届论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对其田野、历史与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沙马拉毅副校长认为,此次论坛的召开和基地的落成,将极大地促进西南民族大学相关学科的建设,进一步加强西南民族大学与全国各地相关科研机构的学术联系与交流。开幕式由《民族研究》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方法的反思
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教授回顾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从近年来中西方之间展开的学术对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已经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正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一百多年来发展的基本特点。浙江大学庄孔韶教授从组织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可能性。作为对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回应,云南大学何明教授介绍了云南大学2003年组织的由10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村民自己书写日志的科研项目,讨论了在田野中人类学研究者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起沟通渠道的问题,揭示了由过去的民族调查转变为后来的民族学调查的重要意义。贵州民族大学吴秋林教授从文化基因论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学“中国化”的尝试与可能。北京师范大学刘夏蓓教授总结了当下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关于民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在题为《民族同化论的三个误区》的发言中指出,当下中国的民族同化论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要和国家的边界一致(熔炉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区别(文化中心论)、美苏国情误读(一厢情愿的断章取义)三方面的误区。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通过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现在云南边境的“普洱誓盟碑”的分析,认为“结盟”展示了新中国民族政策与多元民族文化传统的巧妙融合,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起点,对于今天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借鉴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探讨了安宁河上游多续藏族的族源问题,认为多续藏族是以安宁河流域的原住人群为核心,不断吸纳周边人群而形成的藏族支系。云南大学张跃教授以云南丙中洛地区怒族“仙女节”为例,指出了在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节庆在民族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群体整合和调适功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永祥研究员通过在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洼垤乡所做的有关干旱灾害的田野调查,归纳了抗旱政策在灾害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的不同回应与特点,指出干旱灾害的应对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需要政府、村民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才能够战胜干旱灾害。
(三)关于传统文化与族群认同的研究
针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张建世教授和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副教授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张建世教授主张从个体看整体,从一种或一类文化(或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出发,进而对它生存和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即“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和研究。吴兴帜副教授则从整体看个体,主张从整体性的“文化生态区”理念出发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广西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艾菊红副研究员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于旅游情景中的日渐“遗产化”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传承进行了讨论。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上海大学张江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正爱副研究员也通过具体案例对“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四)关于民族区域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研究
西南地区几所高校的学者们的发言,集中在藏东南、藏彝走廊、川区、川滇交界等处的区域研究上,突出体现了“西南论坛”的地域研究特色。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庄万禄教授和来仪教授分别以各自的在研项目为例,对地区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为促进区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通过分析1940年代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设立及其内部人事纷争,讨论了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地方之关系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从发展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通过对泸沽湖沿湖的旅游商品市场的调查和分析,指出了当地旅游商品地域特色缺乏、品牌意识差、无竞争优势等问题,提出要依托应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工商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锦研究员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为例,探讨了嘉绒藏族独特的社会性别观。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第4篇
南因果博士一直在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奥秘。在他看来,“理解当代中国之谜,肯定首先要破解中国共产党之谜。”他认为,与西方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有其特殊性:一是历史基础,能够成为执政党,是因为中国90%以上的老百姓当年支持中国革命。二是执政理论,西方国家政党的理论都是为了日常政治需要的简单理论,而中共却有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注具体情况,又能超越“日常政治”,从根上解决问题。三是人民拥护,尽管犯过错误,但依然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60多年的实践中,把一个一穷二白、出发点基本为零的中国,发展成为如今一个稳定的国家,各方面都比较成功的国家。
当然,南因果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也直言不讳。他说,中国每年10%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合理的、平等的政策目前非常重要,中共必须关注社会福利,避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关注工人劳动条件和安全条件,以及农民和偏远地区的生活水平。应该继续打击现象,树立执政党两袖清风、为人民谋福利的形象。
在党和国家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形象塑造方面,南因果认为,中国现有的宣传方式太古老,效果不好,有待改进。例如,在一些国际上特别关注和争议的话题上,中国往往采取回避或者淡化的方式,没有向西方做出充分的解释,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在阅读了《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英文版后表示,该书的出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描述方面已经取得进步,更启发我们,应该面向大众普及关于中国的学识,特别是在那些话语权已被似是而非的西方涉华报道所垄断的领域。他说,“随着中国影响力日增,西方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中共成功之‘谜’,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群人数也越来越多。”他相信,对西方学者来说,对中共的历史和政策形成客观平衡和理性深入的看法是完全可能的。
南因果博士另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中国的问题。在西方,出于不同原因,有很多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和偏见的声音。对此,南因果通过实地研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他从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说起,到元朝对行使有效管理,再到清朝皇帝设驻藏大臣,说明与中国联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也是顺应历史的自然结果。关于是否存在“种族灭绝”,他说,中央政府对藏人实行了比汉人优待得多的计划生育政策,藏族人口增长率也比汉人高出很多,所谓“种族灭绝”也不存在。关于是否存在“文化灭绝”,他说,这种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政府实际上是大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的语言、文学、口传文学的研究,日常生活和传统建筑。还有包括寺庙在内的很多文化场所也得到了修缮或重建。在解释目前发展还比较落后的原因时,南因果认为,这主要是历史和地理原因造就的。他说,1950年以前,除了寺院教育以外,根本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把占藏人绝大多数的人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本身就是一大进步。“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几乎只听那些上层贵族代表的说法,而不去问问那些平民百姓。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心声。”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第5篇
摘 要: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近代;湘西;开发史;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2608
一、何谓区域史视野
强调确立区域史的视野,以“开发史”为问题切入口深刻地阐述一个地方社会的近代变迁,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一种挑战性首先是必须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区域史的视野”?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运用“区域史的视野”来议论和阐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相关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方法论和意义上予以解释与阐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缘于社会史研究推进的带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转而开始越来越关注下层社会空间与生存场景的新变化,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域转向”新趋势。史学研究中的这种“区域转向”既不是以往史学界宏观叙事模式下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拓展的一种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不是传统地方史研究范式的翻版,而是一种包括思维方法、解释框架、叙事风格等系统要素在内的史学方法论转型。与以往史学仅仅专注于“宏观历史”的重在描述“国家、政治、时间”的“大历史”的“正史”叙事式研究不同,“区域史”关注“大历史”背景下具体“微观历史”的“民众、社会、空间”的“小历史”的解释与分析,强调社会公众、不同空间、地方经济,凸现史学研究应有的主体性、结构性和差异性;而同传统地方史的主要差别在于传统地方史往往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确立研究对象范围,而以行政区划来界定研究范围往往包括若干不同显性的区域在内,实际是多个区域历史的机械相加,这与以历史同质性为特征的区域史研究有本质区别。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不是通史的地方化,也不是专史的地方化,同样也不是宏观主题的地方化(如“在湖南”之类),而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
所谓区域史的视野就是研究区域史所要求的思维角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基于区域历史同质性上的问题意识,体现整体性特征的历史要素的结构分析路径和以文献与田野相结合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历史同质性是建构区域的基本廪性,也是判断确认“区域”的重要条件。区域史研究就是要在区域历史同质性中寻找课题,从其特征上发现要研究的问题,从而确立问题意识;同时,应当进一步发现影响区域整体社会变化的重要历史要素,并依循这种历史要素的自身结构来分析其在区域社会历史中的形成、特征和作用,从而反映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状况。而这样的研究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方能在解读“大历史”与体验“地方感”相互印证、补充,从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全貌。
二、对近代湘西历史研究的学术反思
湘西自古以来就与外部地区及中央王朝存在种种历史联系,而正是这种历史联系赋予它值得关注的历史价值。然而,无论在地域范围、民族地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湘西都不可能进入传统的正统学术探讨主流视野,因为它只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成份和特定历史影响的特定地域。所以,在传统学术的视野中湘西只能是关注这一区域以及这一区域内民族的学者的学术对象,具体地讲,对湘西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和土家族、苗族问题的学者(或者说本土学者)。经过这些学者多年的努力,有关近代湘西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著方面涉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主要有:廖极白的《湘西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论述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湘西的通史著作,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谈到历史上的湘西开发,其中关于近代湘西的开发用笔较多;游俊、李汉林的《湖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从民族史的角度叙述了近代湘西开发中的一些历史大事;游俊、龙先琼的《潜网中的企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了近代湘西的开发史实。此外,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陈国安的《土家族近百年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黄柏权的《湘鄂西土家族》(民族出版社,2003年)以及王跃飞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都对近代湘西的开发历史有不同程度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