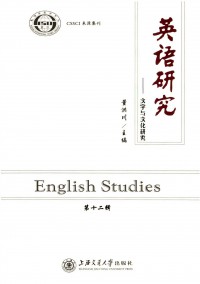泰戈尔代表作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理想主义 女性主义 神秘主义 真理
1、引言
泰戈尔是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尽管泰戈尔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事实上他也是一名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的作品正如德国著名学者温得泥兹所说由东西方的译文传遍世界。(倪,1),中国学人也对泰戈尔大力赞扬,、冰心均表示从中受益匪浅(2)。
泰戈尔的作品卷帙浩繁,不可能一一提及,所以本文对文本进行了限定。泰戈尔因为能整合东西方最精华的方面而为人称道,他写的很多作品包括五篇英文作品:,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1913), Personality (1917),Nationalism (1917),Creative Unity和The Religion of Man (1930),足以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世界级的思想家。
然而对泰戈尔的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泰戈尔曾经宣称他拥有永恒的简单(Tagore, 494), 萧伯纳曾经对此也有抱怨, 说他使用的语言含糊不清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事实是泰戈尔的玄学倾向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泰戈尔对待他讨论的问题是十分认真的。尽管泰戈尔有浪漫主义倾向但他的很多互相关联的作品透露出他思想的重要方面。
以下各章将从各个方面考察泰戈尔的思想,以展现出一幅较为完整的泰戈尔思想拼图。
2、与爱因斯坦关于真理的论战
作为文学大家的泰戈尔曾与物理大师爱因斯坦有一场关于什么是真理,真是世界地位的讨论,泰戈尔在他的著作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Tagore中记录了这些论战(Tagore, 11-16).摘录如下:
Einstein: Truth, then, or Beauty, is not independent of man?
Tagore: No.
Einstein: If there would be no human beings any more, the Apollo of
Belvedere would no longer be beautiful?
Tagore: No.
Einstein: I agree with regard to this conception of Beauty, but not with
regard to Truth.
T: Why not? Truth is realized through man
以上的简短对话揭示了两者的分歧,泰戈尔很明显认为像美一样真理是依存于人的,他在他的作品The English Writings 中有这样的表述对他来说真理就是完美理解自己精神的世界,每个人不同的精神特质构成了世界。他接着说任何事情都包含于人之中,也就是说宇宙的真理就是人的真理。(Tagore,912)爱因斯坦在这里却坚持认为美脱离不了人但真理却可以,真理是独立于人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比如说北京今天的温度为15摄氏度,尽管有些人会觉得热,有些人会觉得冷,但是温度依然是15度。著名的英国孟加拉语专家威廉姆斯・拉迪斯也对泰戈尔进行了解读,他把泰戈尔与英国著名神秘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主义相提并论,并认为两人都不否认事实,因而观点是相近的。然而通过与贝克莱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的出发点或者说角度是不一样的。拉迪斯主要是从经验阐释出发为形而上正名,他的这一观点在下面的打油诗里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Russell ,623)
There was a young man who said, ‘God
Must think it exceedingly odd
If he finds that this tree
Continues to be
When there’s no one about in the Quad.’
REPLY
Dear Sir:
Your astonishment’s odd:
I am always about in the Quad
And that’s why the tree
Will continue to be,
Since observed by
Yours faithfully,
God.
文中作者以打趣的方式表明他是基于经验承认了事实但是却是以上帝为名。而泰戈尔的思想是基于印度的传统经典奥义书,传达了印度人的世界观,因此两者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从总的来说在承认现实基础上泰戈尔具有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倾向是无疑的了。
3、泰戈尔的神秘主义
泰戈尔的作品很多弥漫着神秘主义,于是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泰戈尔是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著名的印度孟加拉学者Nirad Chaudhuri 在他的著作Thy Hand, Great Anarch.对此有精彩的评论,他认为真正意义的神秘主义是完全抛弃“自我”,但泰戈尔不是这样,他既有自我又同时是神的仆人,所以他至多是一个“半神秘主义者”。(Chaudhuri, 615) 这在他的著名小说《沉船》中也体现了出来。小说中虽然说几乎每个人都有,比如说主人公罗梅西和他父亲信仰的梵设,纳卡纳卡医生的母亲信仰正统的与印度教,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关心还是自己的亲人和爱人,他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医生的母亲病得很严重但是她不愿别人服侍她,因为她是虔诚俭朴的印度教徒。但是当她看到梵设会员汉娜妮娜时却禁不住新欢她,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他们之间有一场对话:
W:妇人H:汉娜妮娜
W: 亲爱的,我看你们父女俩简直是在帮着纳卡纳卡胡闹。你们怎么能够拿他的话当真呢?想你们这么大的姑娘应该尽情享受生活,你关心的事情应该是穿着和娱乐,不是宗教。也许你要问既然你这么说为什么不这么做,可你知道我不那么做是有原因的。我的父母一向严守教规,我们家的孩子都在极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受教养,可是你的教养和我们不同。我很清楚你是在什么样的空气 中长大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顺从天性……
W:你也许以为我是老古派,完全不懂时髦的打扮,可是我想我可以大胆说一句,对于头发的样式我知道的比你要多……
H:……(泰戈尔,226-227)
故事里的人物大多如此,均是性情中人,宗教远非决定性的力量。
4、泰戈尔与女性主义
泰戈尔的神秘主义倾向也可以在他的女权主义思想中得到反映,这首先跟他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泰戈尔认为进化是一个不断变得精致高雅的过程,进化过程就是从无生命的物质到动物到人的过程。关于女性主义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受费格森的影响他宣称就像智人取代比其大的多的生物一样,女人最终也会超过男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指责掌权的男人热心于建立各种各样庞大但却有害的组织, 比如说国家。而对妇女给予厚望,他在The English Writings中写道妇女可以带来新鲜的思想,拥有同情心和决心投入社会建设工作。他称男人为“bigger creatures”, 认为男人终将为女人让位。(Tagore, 416). 很显然泰戈尔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完全从平等的诉求中寻找到立足点的, 而是采用了一种有趣的思辨,以上泰戈尔的论述与其说是为女人辩护倒不如说是一个宗教式的预言。
5、结语
泰戈尔是位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就算仅仅想对其思想进行全面探究也是个浩大的工程。因此本文主要从泰戈尔思想中的三个方面论述了其思想的特点。泰戈尔出生在有着神秘主义传统的印度,而后又赴英伦求学,因而思想横跨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泰戈尔作品所具有的理想主义、神秘主义和女性主义,才使他的作品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Chaudhuri, Nirad C. Thy Hand, Great Anarch.[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615.
1987.
[2]Russell, Bertran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5, 623.
[3]Tagore, Rabindranath.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s. 2 and 3[M].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6. 11-16, 416, 912.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2篇
泰戈尔说:“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此岸的触手可及与彼岸的虚幻飘渺都是一种美,也许你在此岸羡慕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彼岸眺望此岸的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九年级飞鸟集读书心得电子版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九年级飞鸟集读书心得1自然的诗歌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泰戈尔的《飞鸟集》一定是最清新的自然诗集!随便翻开这本书的任意一页,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自然的词语,比如说:“瀑布”、“鸟儿”、“云”、“太阳”等等。不过,虽然写的都是大自然的事物,但隐喻的却是各种各样人生的哲理。
印度是一个“诗的国”。诗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印度文学巨匠泰戈尔。泰戈尔闻名世界。《飞鸟集》是他的代表的诗集之一。他在诗中写到“假如你为了思念太阳而落泪,难道你没有错过群星吗?”是啊,其实太阳跟群星一样,其实都是宇宙之中的一颗星星,但由于太阳直接给人类带来光明,而星星只会在夜晚的天空里眨眨眼睛,于是在我们眼里,太阳发光发热,而群星的闪耀连月亮的光辉都比不上。于是我们注重了太阳,忽视了群星,注重了伟大,忽视了渺小——但实际上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太阳,难道还要放弃星星的美丽吗。何况很多星星其实比太阳还要大许多了!
“鸟儿但愿它是一朵云,云儿但愿它是一只鸟”。我读到此句会心一笑,其实它们何必各自“但愿”呢?人们总认为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自己的东西总不如别人,但借来一用却往往发现,其实别人的东西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自己——不知道有多少你的“厌倦”,别人还在“但愿”呢?
“上帝期待,人能重拾童年的智慧。”那么处在童年的我们有怎样的智慧能让上帝也念念不忘呢?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又会丢掉多少美德呢!是可爱,是单纯、还是成人难有的真诚。长大后的我,能保留儿时的美好,不让上帝失望吗?
“人类自设障碍,对付自己”中国也有成语叫做自作自受。人类造出武器,相互攻打的也是人类自己。在这句诗歌写后的若干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消失,核电危机,哪一样不是“人类自设障碍,对付自己”呢?
《飞鸟集》是一本好书,从它至少有15个中译版本便可以知道,译者和读者对它的喜爱。《飞鸟集》诗歌集语含义非常丰富,就是相同的人,年龄和心境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当我学习疲倦后,看一看《飞鸟集》身心就会舒展开来,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它!
九年级飞鸟集读书心得2《飞鸟集》它是诗人泰戈尔的杰作。这部伟大的杰作由325首小诗组成,小诗虽然短小,却蕴藏着一丝童趣和深刻的道理。从不止哭泣的婴孩,到历尽艰险的探险者;从没有经验的青年,到饱经风霜的老者;从平凡不过的小草,到美丽妖艳的小花;从展翅高飞的小鸟,到洁净无暇的白云,无一不充满趣味。泰戈尔用了拟人的手法,让天下万物都活了起来,让它们有机会诉说自己的欢乐与痛苦。
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写道:秋天的黄叶,它没有什么可唱的,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这本书的诗句里面,有描写一片美景的,有描写一段对话的,还有凭着对生活感悟写出的警世格言。其中有一句:我今晨坐在窗前,时间如一个过路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这句话饱含的哲理其实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这些格言不但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警世作用,还能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泰戈尔用简洁的语言,构造了一个真理的殿堂。
不可否认语言的简略使得《飞鸟集》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影响其蕴含深刻无价的真理。从泰戈尔的文笔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认真的态度以及对爱的思索。毫无疑问,泰戈尔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他热爱生活,因此也隐去了生活中的苦难与阴暗,保留的是光明与欢乐。泰戈尔对爱的思索,更是深切,更是执着。男女间纯真的爱情,母子间温馨的亲情,人与自然间微妙的感情。一切人类可以体会的情愫,都被泰戈尔原原本本,又及其含蓄地表达出来。泰戈尔尤其崇尚爱情,他毫不吝惜地运用了大量比喻来赞美爱情的伟大与永恒,就像他写的那样:"我相信你的爱,就让这作为我最后的话吧。"
他把爱与真理恰到好处地放在生活这架天平的两端,没有丝毫的偏差。生活的天平——爱与智慧;生命的天平——爱与真理。这本书虽然难懂,但我们都能从中悟出一样的道理:爱是人生的基础,爱是人生的全部!不妨听着轻音乐,捧着《飞鸟集》,想想自己是一只飞鸟,在无尽的蓝天中自由的翱翔。
九年级飞鸟集读书心得3《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它由三百二十五首意蕴深长的小诗组成。泰戈尔歌颂这世间美好的一切,万物生灵在泰戈尔的笔下都充满了善意。溪流汩汩作响,那是自然对世界的馈赠。旭日冉冉升起,那是上天对人类的爱怜,诗人的双目滤去了世故与不安,让爱静静的流淌,让美默默的绽放。我们在《飞鸟集》中,追寻美与爱,谛听生命的祈祷,为明天的理想,添上坚定的翅膀。
我存在于世,是永恒的生命的惊喜。
赞美生命,是因为它的存在是一个华丽的奇迹。生命在无垠的宇宙间飘摇,我们常常为其脆弱流泪,也为其坚毅鼓掌。阿甘说过:“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而正因为无法预知的未来,才让坚持前行更有意义。
正如《飞鸟集》中提到的:“我存在于世,是永恒的生命的惊喜。”人生是变幻莫测的,此刻你脚下坚实的土地,可以让你赖以生存安生立命,而或许在下一秒,它就会变成沼泽泥淖,吞噬掉你的所有。而此刻你经历的狂风侵袭,在下一秒也可能阳光和煦。所以,在顺境中思虑危机,在逆境中坚信奇迹。要相信生命会在漫长的跑道上蜿蜒曲折出一个璀璨的梦,那些信念,会像夜空中的启明星,伴你度过最黑暗的夜,引领你去夺取属于你的绚烂明天。
永远不要折服于困难,因为活着就会遇到奇迹,因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有惊喜。
九年级飞鸟集读书心得4读印度诗人——泰戈尔大师的诗歌,不同于读那些明媚中带着忧伤和彷徨的青春故事,他的文字中有一种独特的新鲜。读每一首小诗就像在初夏滂沱大雨后的清晨,推开窗户,你会俨然发现一个清清白白的天空。
《飞鸟集》是一部格言诗集,由325首无标题小诗组成。泰戈尔在诗中把自己比喻成寻找理想境界的“永恒旅客”,像飞鸟一样漂泊寻找。在这部诗集里,泰戈尔把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约束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短小精悍的诗句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泰戈尔曾在书中写到:“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这句话虽然是写小动物的,但实际上是在给人类发出警示。面对生活的风雨,要有清醒的选择。学会舍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明智的选择胜于盲目的执着。不要为了身外之物而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例如友情、亲情,都是弥足珍贵的,需要我们珍惜和爱护,失去了这些,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死亡如秋叶般静美。”这是飞鸟集中极其有名的一句话。泰戈尔用诗来阐述生命,把生命比作四季。夏天激情澎湃,正如正值壮年的我们,是那么灵动。然而到了秋天,树叶频频坠落,枯干的枝条也没有了一丝生机,正如我们生命的尽头,一切变得安安静静,沉归泥土。告诉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像夏天的花朵一样绚烂,活出的一面,死的时候回首往日感觉不虚此生,不留遗憾,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安静祥和地离开。
“不要说这是早晨,并以昨天的名义将它打发掉,像初次看到的一个新生的、尚未取名的婴孩那样看待它吧。”泰戈尔在诗里还展示了“晨”另一种的意义。每日清晨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单调的、无休止的重复琐碎的小事,而是一种永恒的再现。因为晨在到来前,光明战胜了黑暗,自由战胜了约束,这是一支重要的插曲,它赋予了深刻的含义。
泰戈尔的《飞鸟集》曾在中国现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冰心在她的诗集《繁星》序里曾说过,她的诗受了泰戈尔的影响。《飞鸟集》虽创作于1913年,现在读来,仍然回味无穷,书中散发的清香,用轻松的语句道出的深刻的哲理,犹如醍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我想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原因所在,也是它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九年级飞鸟集读书心得5飞鸟的象征是什么?是自由。大诗人泰戈尔写的这一部《飞鸟集》,以抒情的诗篇记录着他对人生、自然与宇宙的深刻思想,给了我许多的人生启示。
《飞鸟集》中的语言优美,有许多饱含着理性的话语。其中便有一段:“权威对世界说道:‘你是我的。’世界便把权威囚禁在她的宝座下面。爱情对世界说道;‘我是你的。’世界便给予爱情以在她屋内来往的自由。”这段话用语言描写与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地诠释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说《飞鸟集》中的智慧是无限的。
这部诗集以“飞鸟”的名字命名,因为这部诗集是自由的完美体现。它带给人轻松愉悦之感,阅读过后,仿佛脑海中真的有一群群展翅翱翔的飞鸟,它们向往蓝天,努力高飞,把天空作为自己生命的起点、终点。这部诗集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应有一个信念,在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拼搏、迈进,正如天空中不停飞翔的飞鸟。
整部诗集由325段小诗组成,每段小诗都有它不同的寓意。我对于其中的一些感到十分地有道理,反复地阅读;可是另有一些我读不懂是什么意思。这里面蕴含的哲理非常广,可能因为我学识浅薄,人生经历少,才不能完全读懂。虽说如此,但这并没有打消我的阅读兴趣。作者写下这一部诗集献给后人,其实是给予了后人无限的精神财富。《飞鸟集》仿佛飞鸟般自由飞翔入人的脑海、心田,使人久久难忘。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3篇
至于我自己,与许多人一样,在中学时代从父亲的书架上读到《飞鸟集》《吉檀迦利》《园丁集》等作品;也曾痴迷地摘抄其中的诗句,为它们短小精悍中蕴含的人生哲思和深邃、宁静的美所吸摄。不过坦率地说,直到二十多年后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静美而不是绚烂,堪称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像德国学者温克尔曼评价希腊艺术时所言,那是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学者通常将泰戈尔的创作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代表作有《暮歌》(一译《黄昏之歌》)、《故事诗》等,中期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晚期有《山达尔女人》等。中国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作品都来自中期,特别是郑振铎先生所译《飞鸟集》,引发了中国读者对泰戈尔诗歌的普遍关注,也直接影响了冰心等人的创作。郑先生把它比喻为“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飞鸟”的含义,在诗集开篇两首有所透露,“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故此有人认为“飞鸟”即游荡之鸟,诗人把自己视为执著追寻人生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诗集的含蕴是丰富的,其中贯穿着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即对自我的反思与对人生的省悟。“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18)艺术的重要功能,就是认识自我和世界。诗人赞颂人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和创造的力量:
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25)
人不能在他的历史中表现出他自己,他在历史中奋斗着露出头角。(52)
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却不过如晨间之雾。(14)
为此,人需要保持谦卑与谦逊的姿态,以聆听与领受的方式,从世间万物与神那里获得启示:
神呀,我的那些愿望真是愚傻呀,它们杂在你的歌声中喧叫着呢。
让我只是静听着吧。(19)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57)
果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217)
在对人生的省悟中,诗人得到的神的启示,只有一个字:爱。就像他在诗集结尾说道:“我相信你的爱。”(325)因为相信,所以每个人要全身心地去爱,爱自己,爱他人,爱世间万物,爱那创造了这一切的神。爱,就意味着付出、奉献和牺牲,而不是索取。爱,同时也就意味着毫无偏见的爱,而不是爱己所爱。这是诗集最动人心弦的所在: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9)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56)
瀑布歌唱道:“虽然渴者只要少许的水便够了,我却很快活地给与了我的全部的水。(69)
生命因为付出了的爱情而更为富足。(223)
今天,正是由于爱――自爱与爱人――的长久匮乏,使得人与人之间陷入孤寂、麻木、冷漠、隔绝,乃至相互猜忌、伤害的困境。
《吉檀迦利》(1912)是为诗人赢得诺贝尔文学奖(1913)的重要作品。授奖词中说,这位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向我们展现那种在苍茫、宁静和圣洁的印度森林中达到完美的文化:首先寻求灵魂的平静,永远与自然生活协调一致”。它是一部宗教诗集,其集名在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是“献歌(献诗)”的音译,即献给神的颂歌。诗集显示了诗人深受印度传统泛神论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叫“梵”。人与自然、人与神是同一的,这就是“梵我合一”。当然,诗集已超越印度传统的宗教颂神诗,成为一部“生命之歌”,其中延续着诗人一贯的写作主旨,即爱;也描绘和赞扬了纯洁无暇的童真和童心。我们从第2篇中可以领略诗人作为“歌者”的抒情方式和语调: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2)
渴望,期盼,等待,错过,依旧不改初心……这些源于内心深处的真实而忠诚的情感,构成诗歌缓缓流淌的回环往复的旋律;这种旋律又加深了“歌者”情感抒发的强度和力度。即便是没有任何宗教意识的背景,也并不妨碍读者从中各自体悟生命的美好与希望的可贵: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13)
而泰戈尔诗中对无暇的童真的细腻描绘与赞美,则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作家如冰心等,去关注儿童文艺。季羡林认为,这是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新时代文学影响最突出的一个方面。
《园丁集》(1913)是一部关于爱情、自然,也是关于人生的诗集。我们在这部诗集中看到诗人个性的另一面:对尘世生活及其幸福的眷念与向往;与此同时,在爱情这一美好情感的催动与滋润下,青年男女身上所散发的人性光辉,与神性光辉的笼罩合为一体。而这如清风朗月般的光辉,又在诗性语言的咏叹与赞颂中折射出来,撒向每一位读者的柔软心间。在第1首中,诗人借用诗剧的对话方式,让仆人向女王深情表白:“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而他所要报酬不过是能够靠近她,亲近她,保持她的纯洁。这位女王象征着爱情王国里至高无上的君主,是抽象的;但在随后的诗篇中,每一位女子都有她们具体的形象,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微妙的情感悸动――
当她用急步走过我的身旁,她的裙缘触到了我。
从一颗心的无名小岛上忽然吹来了一阵春天的温馨。
一霎飞触的撩乱扫拂过我,立刻又消失了,像扯落了的花瓣在和风中飘扬。
它落在我的心上,像她的身躯的叹息和她心灵的低语。(22)
诗集中既有单相思的郁郁寡欢,也有初恋的不胜娇羞;既有期待中的坐立不安,也有幽会时的狂喜颤栗;既有相依相伴的甜美幸福,也有生死离别的锥心疼痛……诗人似乎在向我们表明,神秘莫测、难以捕捉的爱情世界,正是令人心旌摇荡的诗意王国。
终其一生,泰戈尔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还有大量的绘画、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论文。自然,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围绕着《吉檀迦利》,也围绕着是否要把奖项授予泰戈尔,瑞典学院当年有过争议。当时的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是极力推荐泰戈尔的。他说:“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里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情感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参见吴岩《〈泰戈尔抒情诗选〉译者前言》)泰戈尔曾于1924和1929年两次到访中国,同情并热爱中国。据冰心记载,当第一次他要离开北京的寓所,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Anything left?)。他愀然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Nothing but my heart)。”
(冰心《〈吉檀迦利〉〈园丁集〉译者序》)
【名家评点链接】
(泰戈尔的)特点是思想深邃,尤其是感情热烈,比喻动人。在想象文学领域,确实很少有人具备如此广泛多样的音调和色彩,能够同样和谐优美地表达各种激情:从灵魂对永恒的渴望,到被游戏的儿童激起的快乐。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1913)
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父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世界。
――冰心《〈吉檀迦利〉〈园丁集〉译者序》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4篇
《金色花》篇幅短小,而意蕴丰赡,是泰戈尔散文诗集《新月集》中的代表作。接下来是为大家带来的金色花教学反思,望大家喜欢。
金色花教学反思范文一我所上的《金色花》一课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后获得些许的赞扬。反思本节课一个个真实的情景,对于如何上好一节合格的语文课、建构活力课堂颇有感悟。
1、读出“语文味”,创造诗意课堂
程少堂老师认为:所谓语文味,是指在语文教育(主要是教学)过程中,在主张语文教学要返朴归真以臻美境的思想指导下,以共生互学的师生关系为前提,主要通过情感激发、语言品味、意理阐发等手段,让人体验到的一种令人陶醉的、富有学科个性和教学个性的审美。
在《金色花》一课中,我主要通过灵动多姿的朗读(听读、赛读、评读、范读等)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熏陶感情,从而读出“语文味”,创造诗意的课堂。学生读得非常认真,虽然读得不是很好。于是在我的启发诱导之下,有不少的同学大胆地用稚嫩的童声来读,重音、语速,情感都把握得很好。例如冯尔学当读到“我不告诉你”时,那稚嫩的略带撒娇的童声引起在场听课老师及同学们的笑声。
2、关注动态生成,把握瞬间精彩
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在“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的研究时,就提出:一个真实的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及多种因素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推进过程。他还指出:“要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要把个体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应该关注生长、成长中的人的整个生命,追求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用“动态生成”的观点来引领课堂教学,让我们的课堂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上《金色花》一课时,我在课的结尾设计了一个环节:以“假如你在妈妈生日的这一天具备了文中小男孩的神力,你会变成什么呢?” 请学生倾诉内心至爱。有一个男孩子说,会趁妈妈出去的时候,偷偷地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把家里的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也有同学说,希望变成一架飞机(一艘轮船),让妈妈乘坐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也有同学说,希望变成一棵树,春天勤生绿叶,长得枝繁叶茂,夏天母亲可以在树下乘凉,为她遮风挡雨,秋天树上的果实成熟了,母亲可以摘下解渴,如果她需要钱了,就砍掉自己身上的树枝去卖……我以及听课的老师都被同学们的真情深深打动了。在这种氛围中,许多上课很少主动举手发言的同学都纷纷发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此时下课铃声响起,我说出了此番结束语:同学们,沐浴着母爱成长的你们要懂得加倍地回报,去爱你们的母亲,爱你们的同学,爱你们的老师,爱祖国和人民。愿你们在被爱与给予中拥有一个丰富美好的人生!”
在这里,学生在老师营造的和谐的对话氛围中,与本文对话、与自我对话,敞开心灵,思绪飞扬,从而在熏陶感染中建构起新的思想链条,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李镇西老师曾经说过:“在课堂上,没有纯粹的理念,一切细节同时都是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人所上的《金色花》一课在许多细节处理上反映了教师的理念仍有待转变。如:问题的探究未够深入,学生的思维仍受着老师的操纵。我想,要上好一节合格的语文课,让我们的语文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归根结底还是要转变理念,提高自身素质,让语文课因每一个富有个性的“我”而精彩吧。
金色花教学反思范文二《金色花》篇幅短小,而意蕴丰赡,是泰戈尔散文诗集《新月集》中的代表作。它写一个假想——“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首句),并由此生发想象——一个神奇的儿童与他母亲的“捉迷藏”,描绘成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表现家庭天伦之爱,表现人类天性的美好与圣洁。这样一幅画面,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观照,揣摩其不同的意味。
乍一看,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儿童嬉戏的画面。画面的中心人物是“我”——一个机灵可爱的小小儿童。“我”的突发奇想,变成一朵金色花,一天里与妈妈三次嬉戏。第一次嬉戏,是在母亲祷告时,悄悄地开放花瓣散发香气;第二将嬉戏,是在母亲读《罗摩衍那》时,将影子投在母亲所读的书页上;第三次嬉戏,是在母亲拿了灯去牛棚时,突然跳到母亲跟前,恢复原形。“我”“失踪”一天,却始终与母亲在一起,对母亲非常依恋。“我”幼稚天真,却藏着自己的秘密,惟有他母亲不知道,最后母亲问 “到哪里去了”,“我”说“我不告诉你”,这是得意的和善意的“说谎”,仍流露出对母亲的爱恋。总之,“我”是在以儿童特有的方式表现对母亲的感情。故事虽短,但是有完整的情节,情节发展有波澜。人物在情节的发展中各显现其性格:“我”的性格是天真活泼、机灵“诡谲”的,又是天生善良的;母亲的性格是沉静的、虔诚的,也是善良的、慈爱的。两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善良、善意,是母子两人性格表现的主旋律,而“我”的“诡谲”与母亲的“受骗”则与主旋律“不和谐”,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创造出特殊的意趣。
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侧重三点:一是诗的语言美;二是诗的画面美;三是诗的情感美。我觉得本课最成功的地方是最后一个环节:创意表达,升华情感美。在这一环节,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读了这篇文章,是否也觉得我们要为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作些什么呢?我们用有创意的作业,来表达我们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你忽然具备了文中小男孩的神力,你准备变作什么来表达你对母亲的满怀爱意?
学生自由想象,用“我要变作……”说话。
1)假如我变成了一条清清的溪流,我要在妈妈工作累时,让妈妈来到我身边,听我唱一支欢快的歌曲,抖落满身的疲惫;我要在妈妈口渴时,让妈妈品尝我甘甜的水,使她重新变得容光焕发!
2)假如我变成了一朵小小的白云,我要紧紧跟随着妈妈,使妈妈不管走到哪儿,都免受烈日无情地炙烤。
3)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中的涟漪,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泰戈尔《告别》)
学生表现都很活跃,在练习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母子深情的体验。总结这节课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在教学中,既鼓励学生读,又让学生明白应怎样读、为什么要这样读,使学生在充分体会诗歌蕴涵的感情的同时,还掌握了朗读技巧,不仅读懂了诗,也学会了怎样读诗。
二是简化了教学环节。以前教诗歌时,总是将“语言赏析”单独安排一个环节。这次我尝试将“朗读”、“理解”、“品析”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在“吟读”环节中,为读好最后两节,指导学生分析语言的句式排列;在“解读”环节中充分利用点评,指引学生在解读中赏析语言。这样的安排简化头绪,为学生赢得更多朗读和思考的时间,提高了学习效率。
三是美化课堂。恰当的运用多媒体,或创设氛围,或激发兴趣,或配乐朗诵,或画面点缀等,为课堂添色不少。另外,教师优美的语言也让课堂富有情韵。
金色花教学反思范文三这是一堂徒具骨架而没灵魂的课。整节课上下来总觉得缺了点感觉,我想那就是语文味儿吧。尽管在课堂上几次三番地想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情景中,但总是浅尝辄止,整节课还是游离于文本之外的。
预设的教学重点是“读一读、说一说”这两个环节,希望通过这两个环节学生能到字里行间去摸打滚爬,有所感,有所悟,但显然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缪老师和包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朗读指导不到位。
首先是朗读的目的不明确,为“读”而“读”,尽管朗读的形式有所创新,师生配合读、男女声合读等,但学生被老师驱赶地读,只求形式不求实效。二是朗读的形式把握不当,朗读的形式纷繁多样,不一而足,但各种形式的朗读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功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特别是齐读,是教师必须谨慎选择的,滥用齐读会使学生产生殆倦,压抑课堂气氛,齐读应放在学生对课文的情感有所了解、有所感触之后,它是教学效果的一个检测。第三是自身的朗诵功底还有待提高,教师范读的精神固然可嘉,但在电教设备如此先进的今天,完全可以采用一些名家的朗诵,以提高教学效果。
这节课的教学还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传统的未必是不好的。在我有限的视野范围里,语文备课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环环相扣,通过逐层深入的问题解读文章;一种是板块分解,通过各个环节来解构文章。凑巧这次龙飞采用的是第一种形式,而我则采用的是第二种,在备课时我参考了很多资料,龙飞上课时用到的那些问题我很多次地看到,但每次心里都很排斥,都老掉牙的问题了,拿不出手。我苦心孤诣地设计了“读一读、说一说、比一比、写一写”等环节,自以为创新高于一切,却忽视了语文教学中一些必不可少的环节,比如整体感知。因为缺少这一环节,学生对这首散文诗的理解总是支离破碎的。板块式教学的最大弊端在于割断了课文中原有的情感脉络,语文的“听、说、读、写”很多时候是一个综合体,不能截然分开。作为一名新教师,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改一改浮躁的毛病,对传统的一些教育方法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上创新。
新课标中强调语文应该注重整体感知和熏陶感染,教师应努力调动文字本身的力量,引领学生去感知文字背后魅力。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良好的文本感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其中分析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大学时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自己读文往往囫囵吞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而现在走上讲堂发现把“感觉“说出来是见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对自己没有感觉的文章产生感觉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说实在的,对泰戈尔的《金色花》我兴趣不大,我也无法体会其中蕴含的母子情,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慢慢有了感觉,但始终不是自己的,我想这是我的课上不深刻的根本原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只是一个笑话,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对文本的解读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而如何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是这节课留给我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以上几点导致我这节课如浮光掠影一般,留给学生的东西并不多,他们随我在地面上挖坑,却没有深入去取水,他们的心灵没有得到滋养。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一堂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堂课应该像一部小说一样,有悬念、有,使观赏者不忍释手。但显然我若要到此境界还需要一定的时日和磨练。这次开课留给我很大的思考空间,我,将在语文教育的道路上摸索前进。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川端康成;《雪国》;物哀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95-01
《雪国》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之一,其曾于1968年以《雪国》为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雪国》讲述的是一名舞蹈研究者岛村与一名艺妓和一位纯情少女之间的感情故事,川端康成用淡淡的笔调,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哀怨和冷淡的世界。
一、川端康成生平和创作风格简介
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之一,他于1899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北区,幼年的川端康成先后失去了父母,后来又失去了姐姐和祖父母。不幸的童年在川端康成的一生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旅途中度过,心情常常苦闷抑郁,形成了独特的感伤和孤独风格。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100多篇小说,成为继泰戈尔和阿格农之后,亚洲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不仅获得了日本最高文学奖项――艺术院会的会员,还曾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歌德奖章”,以及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勋章。
川端康成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在描写爱情,但他笔下的爱情和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并不一样。川端康成并不着重去描写爱情中的幸福欢乐和缠绵悱恻,也不去描写爱情里的种种不幸与痛苦。他作品中的爱情常常表现处理一种淡淡的孤独且感伤的情感:平平淡淡地开始,平平淡淡地结束,没有任何起伏,但留给人无限的回味。
除了爱情之外,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常描写死亡。由于川端康成自幼年起,目睹了父母、姐姐和外祖母的相继离世,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不自觉地写到死亡。同样的,川端康成笔下的死亡与其他作家所描写的死亡也是不大相同的。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死亡都被当作故事结束的方式之一,而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却常常以死亡为起点来开始一个故事,如《白色的望月》《水月》以及《山之音》等。
川端康成的语言清新秀丽、平和优美,文章虽读起来和口头语言颇为接近,但用语简明、描写准确,没有任何多余的词汇。他的作品纤柔流畅,将人物的情绪、故事情节和自然物象Y合在一起,如同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可以说在日本美、东方美之上,川端康成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
二、《雪国》中的“物哀”之美
《雪国》这部作品,集中表现了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中的“物哀”思想,在这部作品中,爱情的虚无之美、雪乡的洁净之美与作者个人的悲哀之美达到了极致,令读者看完之后既感到淡淡的惆怅,又深刻体会了雪国之美。
《雪国》描写的是一名叫做岛村的舞蹈研究者,从东京来到多雪的上越旅馆,并在这里结识了驹子。驹子不仅年轻貌美,还会弹三弦琴,在两人交易的过程中,驹子对岛村产生了真挚、深厚的感情。但在岛村心目中,只是将两人的情感看作是露水情缘。驹子在了解到岛村的心意后,尽管很难过,但也表示理解。她甚至对岛村说,让他一年来一次就成,甚至带着夫人一起来玩也是欢迎的。岛村第一次来雪国时,便喜欢上了驹子的年轻貌美,而驹子则欣赏岛村的丰富学识。岛村第二次来雪国的路上,见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名叫叶子的姑娘,岛村对美丽的叶子也心存遐想。而那时叶子则在照顾一位患病的男青年,这位男青年名叫行男,行男却对驹子一往情深。在行男临死之前,叶子曾跑来找驹子,恳求她去看望行男一眼,但驹子并未前去。后来村里剧场失火,叶子从剧场二楼掉下来摔死,岛村虽始终惦记着叶子的美貌,但此刻也只是略表同情而已。
《雪国》集中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既有对男女恋情的悲哀,也有对世间自然万物的悲哀。《雪国》中,驹子真心爱着岛村,不能自拔,但在岛村心里,却清楚地认识到驹子对自己的真爱只是徒劳。这种由男女恋情而出发的物哀之情延伸到第二层,便是对于世间众生的悲哀。川端康成在创作《雪国》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扩张时期,在整部小说中,川端康成并没有描写任何军国主义战争场景,但其将现实抽象化,把世间万象贯穿在虚无的雪国世界中,暗生出世间万事万物皆徒劳的感慨。
在《雪国》中,川端康成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描写着雪夜的美丽、夕阳的美丽、月色的美丽:“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山头照满了月色,这是原野尽头唯一的景色,月色虽已淡淡消去,但余韵无穷。”甚至在叶子死去的时候,川端康成仍在写着月色、写着银河,这正是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中虚无思想的表现。正如川端康成最喜欢的《枕草子》中的一句话那样:“往昔徒然空消逝。”在川端康成看来,只有空虚才是真正的美,而所有的美最终都是徒劳的。
参考文献:
[1]陈汝霞.川端康成小说的叙述技巧研究[J].商业故事,2015(6).
[2]杜晓丽.川端康成笔下女性的美丽与哀愁――以《伊豆的》和《《雪国》》中的女性形象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5).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