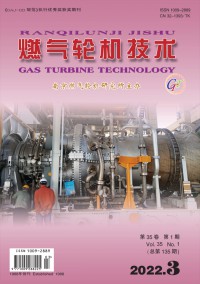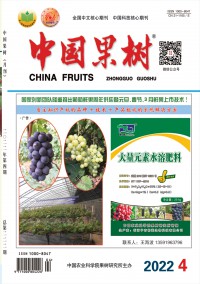夏至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夏至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夏至诗句范文第1篇
云有万仞山,云有千丈水。自念坎壈时,尤多兢慎理。
山束峡如口,水漱石如齿。孤舟行其中,薄冰犹坦履。
孱颜屹焉立,汹涌勃然起。百丈为前牵,万险即平砥。
破之以筼筜,续之以麻枲。砺之坚以节,引之直如矢。
夏至诗句范文第2篇
1、《夏夜知君暖》这是一部都市情感剧,改编自作者福云朵朵的小说《甜心教练,撩个校草打篮球》。讲述了青梦大学新生苏暖夏与风云校草君夜甜蜜撒糖,带领青梦篮球队的故事。
2、梦大学新生苏暖夏为完成父亲遗志,从怪力少女变身篮球队甜心教练,集结了一群拥有篮球梦和超高颜值的“天才怪物少年,试图挽回球队被解散的命运。苏暖夏意外发现风云校草君夜球技高超,为了能让他加入球队,苏暖夏使出浑身解数,24小时“关怀”不断,君夜渐生兴趣,终于“傲娇”地答应入队。
(来源:文章屋网 )
夏至诗句范文第3篇
又是骄阳似火的7月,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三下乡活动了,然而收获是不同的,相同的是倍感充实,而这次的三下乡之旅,让我真正的从实践中学习到知识,也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今年我参与的队伍是外语系大学生党员骨干挂职实践服务队,听从城南街道办事处的安排,被分配到黄铺居委会挂职.短短的几天,我了解到黄埔居委会确确实实是与群众直接联系的机构,看到了居委会工作的干部对待群众耐心和蔼,有礼有心,服务到位的的态度,很多细节让我感受到了无论作为一名党员还是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定义.比如,有一名老人来到居委会反映情况,梁书记让老人先坐下,认真地听老人反映情况,然后耐心地同老人讲解.这一幕,我没有看到作为一名书记与群众的距离感,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美好.这几天梁书记给我们安排的工作主要是一些文件资料的整理,如整理妇女育龄信息表和户口登记本等.在挂职期间,我们还随党政办林书记去看望五保户,到每家每户派发宣传“建设广东园林城市”信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去看望了一名五保户老人,他不在家,推开矮小的瓦房的一扇扇破旧的门,房里漆黑一片,蜘蛛网横挂着,从林书记那里了解到,这位老人一个月前发生了车祸仍住院中,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再看看老人居住的简陋条件,那一刻,我的心特别的疼.我突然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珍惜,有些我们看不在眼里的东西,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宝贝,我们要在学习工作之余,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在派发宣传单的过程中,群众们对身穿“大学生“三下乡”黄色服装的队伍很欢迎也很热情,比如,有些群众会主动过来询问情况,微笑有礼地听我们讲解.
每个活动都让我有所感悟,而领导的关爱与指导也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在这几天,忘不了书记与各位主任的热情款待,那慈父慈母般的话语.最难忘的是,挂职接近尾声时,我们学院的领导与城南街道办的领导和我们大学生党员骨干挂职实践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开的总结会议.会议上,党工办林书记的“三个心”及“三个对不对得起”生动讲话让我们很受鼓舞,他还恳切地提醒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不应斤斤计较,而要敢于吃苦不怕吃亏,鼓励我们用心用实际行动去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一段话语,深深的打动了我,感觉眼前开阔,思想又上升了一个高度.这个会议是主要是在于队员们的收获总结上,听着队友有感而发的言语,看着他们陶醉的神情,还有许多共鸣的感受,积极踊跃的场面十分地打动人心.我们发现,这次三下乡,我们学会了感恩,我们都十分感激我们的母校给我们灌溉的知识,我们感激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指导与培养,我们感激我们的领导给我们关爱与机会,我们感激一切.这正是林书记所说的“三个对不对得起”中的对不对得起国家,原来这个定义也体现于此.
当然,还有我与队员之间的一些小故事.短短五天,我十分高兴又结识了新的队友,通过沟通交流的桥梁,我们共同感悟到了合作的力量.我是队伍通讯小组中的一员,在写通讯稿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觉得自己写得不错的通讯稿,在另外两名的通讯员的审核修改下,总是有着自己发现不了的瑕疵,于是明白了成立通讯小组的意义,因为彼此的合作,我们把通讯稿完成的更加完美,同时在讨论定词用语中,我们也互补中学习了新的知识.此外,我了解到宣传小组的感人事迹.我们得知宣传小组的成员在紧迫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份效果不错的“建设广东省园林城市”的墙报,付出的代价是牺牲自己的午休与晚休时间投入工作之中,并且按时到挂职地点上班,没有耽误安排下来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三下乡活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圆满结束.我带着一份感动与思考起程,想想我们分别的那一幕,想想我们共同度过的那点点滴滴,想想我们志愿者们留下的足迹,想想这些天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真的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少的经验和收获,它也是这片天空下不灭的回忆,这将成为我人生的一笔财富,值得我永远珍藏.
夏至诗句范文第4篇
2016年2月最后一周,主管部门官员在全国电视剧行业年会上的发言,引发网络剧行业的极大震动。
在那次会议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和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分别作了题为“2015年~2016年电视剧管理”和“网络剧的发展和管理”的主题报告。
李京盛在发言中提出:网络剧审查将进一步加强,实行线上线下统一标准。罗建辉更是在发言中严肃指出当下网络剧的诸多问题。
“电视不能播的,网络也不行。”此语刷爆了业内人士的朋友圈。
此前,根据2012年主管部门下发的管理细则,网络剧主要采取“自审自查”的管理方式。虽然每一家视频网站都设置了审核员、总审核员,但是网络剧与电视剧“尺度不同”几乎已经成为惯例。
如导演郑晓龙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导演协会开会时,大家都说咱们去拍网剧吧,为什么?网剧审查不严啊,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是先审查,而网播剧是后面有了问题再审”。
严管之下,洗牌在所难免。但是对于那些更具雄心的从业者而言,它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大网络剧时代的来临。
很多网剧的营销诉求是“挑战底线”。
其实,网络剧加强监管的态势自2015年底就变得明显。
2016年1月21日,乐视热播网络自制剧《太子妃升职记》因“有伤风化”被要求下架。同时还有五部热门网络剧被举报后遭事后审查,其中两部永久停播。春节期间大热的同性恋题材网络剧《上瘾》也在2月22日晚全网下架。
“审查标准明朗化,对行业是件好事。”被称为国内“网剧第一人”的制片人白一骢对《t望东方周刊》说。
2016年春节期间,由白一骢担任总制片人的搜狐自制网剧《示铃录》上线。它的原著《怨气撞铃》,是一部带灵异色彩的悬疑小说。白一骢说:“灵异内容在网剧里去掉了,现在的标签是‘悬爱’,悬疑、爱情。”
“网剧现在还是少年初长成。”罗建辉在2015全国电视剧行业年会上表示,网络剧的优势是“题材丰富活泼,手法不拘一格,体现年轻人的审美兴趣”。
他接着指出了现阶段网络剧的问题:制作粗糙,精品较少,跟风严重,部分题材把关能力明显不足,刑侦、灵异、暴力题材把关尤其不足,造成恶劣影响;故意打球现象严重,有意冲击底线(例如某些剧专门表现同性恋内容)。低俗化倾向突出,很多剧都存在创作者主观意识媚俗。
“确实有一些球的事情存在。”视好传媒CEO孙福国对《t望东方周刊》说,有些网络内容制作方把“重口味”当做噱头,从而提升新作的知名度,这是目前业内不能回避的现状。
白一骢的团队多从传统电视剧领域转行而来,主创“自审”的底线会画得高些。他也感觉“相比那些敢打球的人来说,不敢打球的人可能会吃亏。”毕竟从结果来看,有“敏感元素”的网络剧因具有话题性,更易成为“爆款”。
相较于2014年的1400集,2015年网剧达到了1.29万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资本和技术能力比较欠缺的影视机构选择敏感题材,在营销上以此作为卖点、博眼球。
专门从事网络影视营销的暴点文化传媒创始人忻云告诉《t望东方周刊》,的确有很多网剧的营销诉求是“挑战底线”。
他认为,前述的同性恋题材网络剧《上瘾》,在营销方式上就过于高调“卖腐”。
目前,针对网剧的管理思路和措施仍在研究中,审查细则还未出台。 “超级网剧时代”到来
就实际情况看,“先播后审”的模式让网剧制作者承担了更大风险。但是在网络剧的小成本时代,风险指数还相对较低。而且,作品一旦成为话题之作,盈利便不再单纯依赖点击率和广告,下架的损失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补偿。
例如,《上瘾》即使下架,也可以继续依靠积累的粉丝,通过售卖DVD和周边产品的方式盈利。
如今严管到来,靠挑战政策底线成为“爆款”的做法肯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超级网剧”的涌现。
所谓“超级网剧”,强调大制作、强班底和优质内容。2015年下半年以来,单集百万制作费的网剧比比皆是。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网络剧有20余部,其中有5部“超级网剧”的投资更高达5000万元至上亿元。
2015年9月,爱奇艺自制剧开发中心宣布2016年将推出30部以上“超级网剧”。腾讯也在2015年10月公布了包括《鬼吹灯》在内的8部顶级自制网络剧计划。
网络剧终会走向“优胜劣汰”“内容为王”的时代。爱奇艺自制剧开发中心总经理戴莹对《t望东方周刊》说:“网剧的精品化已经成为主流。”
“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不好的东西自然会被淘汰,市场本身就是最大的良性驱动力。”孙福国认为,监管新形势下,一些不够专业的小公司会退出,更有实力、早已做好准备的公司将会与传统影视机构比拼“硬功夫”。
“想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的人,并不会依赖投机取巧的方式。”他说。
“弃剧”和“追剧”的选择权握在网友手里。《暗黑者》上线时,白一骢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像变态一样”地盯着电脑,去看网上的评论和点击数据。
《示铃录》也让导演林楠体会了一番犹如“股民看盘一般”的心情:“拍过不少电视剧,以往拍完就在电视上放,不去管了,现在每天都在担心数据涨幅不好。”
“传统影视制作者离观众声音远,网络剧却要面对网友的嬉笑怒骂,拍得好,网友说‘加鸡腿’。拍得不好,网友找你‘谈人生’。”白一骢告诉本刊记者,“因此网络剧的制作团队都相对年轻化,年轻人承受网友评论的能力更强,调整效率也高。”
他认为,网络剧制作班底和电视剧的差别只在年龄分布上更趋年轻化,而制作上的专业水准不应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观众在要求内容质量。
新片场是一家新媒体影视出品和发行平台。CEO尹兴良告诉《t望东方周刊》,以前很多人拍网络剧只是小打小闹,近两年网剧趋向成熟,优秀人才更多地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关注的是网剧主创是否有成长性、基本功是否扎实。” 网播的标准统一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网络剧输入电视渠道的势头已经十分明显。在此背景下,网络剧、电视剧采取同一标准实属必然。
2015年下半年起,一些视频自制节目已开始反向输出电视台。戴莹告诉本刊记者:“传统影视和网剧互相扶持促进是一个良好的互补方式,未来的互动可能会越来越多。”
业内人士分析,过去网生内容“自审自播”“先播后审”的原则将不会改变,未来网络剧的审查标准会更加明确详尽。它虽然与传统电视剧还会有所区别,但不会有本质变化和较大差距。
一种推测是,未来网络剧的审查标准将与地面电视台非黄金档电视剧看齐。
网络剧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网播以获取最大的利益。编剧李宗梅便把“电视上不能播的,网络也不行”理解为“部分实现网播的双赢局面”。
其实早在2014年,就有业内人士指出,网络剧很有可能成为电视剧的未来。不过,尹兴良认为,网络文化本身对多元化内容有更大包容性,“与传统影视还是存在不同。”
因此,网络上播出的剧集不一定都会被电视台购买。白一骢用“客厅文化”来形容电视剧文化,而网络剧的发展空间在于针对年轻的网剧观众,制作差异化内容。
比如,电视剧观众总体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科幻题材难以获得良好的收视效果。但2015年科幻类型的网络剧前景看好,因为网络剧观众对科幻的接受能力更强。 “刷量”网剧难长远
热潮之下,网络剧盈利模式不成熟、变现回本难依然是普遍情况。孙福国表示,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与规则的逐步建立,盲目进入网络剧行业、通过打球企图“捞快钱”的人,很有可能会“挂掉”。
目前,广告收入和付费观看仍然是网络剧的主流盈利模式。除了少数具有“硬实力”的大网剧之外,大部分产品处于只能回本、难以盈利的状况,甚至有一部分血本无归。
这也催生了业内的“刷量”黑幕,即在网络剧刚上线时,通过雇用水军制造话题和点击量。
“刷量”网络剧往往没有过多的成本和广告投入,忻云把这叫做网络剧第一季的“裸奔”――制作方寄希望于在“裸奔”期间积累起人气和价值,吸引第二季的投资。
忻云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的内容可能制作粗糙,营销上也没有准备。”暴点传媒便遇到过一些因为准备不足而被视频网站回绝的公司,这让忻云哭笑不得:“营销也需要准备时间,一个礼拜做出的营销,效果怎么会好?”
“跟风是普遍存在的。”白一骢说,“很多不专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制片人甚至都不看剧本,雇用月薪几千元的编审给身价几百万元的编剧提意见,这样的指手画脚合理吗?”
在白一骢看来,另一种跟风体现在“卖腐”上,而“卖腐”便能产生“爆点”是一个伪命题。“虽然偏好二次元的用户在社交网络的活跃度更高,但不代表基数更大。”
“无论是大网剧还是网络节目,爱奇艺目前的大方向仍然是做泛大众化的内容。”戴莹对本刊记者说。
在网络剧市场由量到质的变化中,“大网剧”会切走最大的一块蛋糕,剩下的市场将由更多元化的“小网剧”主宰。
尹兴良更认为,利用多元化内容在垂直领域深入、吃透细分市场,将是更好的策略。
这正是尹兴良所在的“新片场”的方向之一。它专注于培养网络剧的原创人才,并使其领域各自不同。很快,“新片场”将推出“东北话分类”。
夏至诗句范文第5篇
与智者同行下句是与善者为伴,与智者同行,与高人为伍。与智者同行的意思是与有智慧的人一起行走,与品行高尚的人结队。智者最早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他们的思想奠定了智者学说的基础。
其他代表人物有:普罗狄柯、希庇阿、安提丰、特拉西马库和克里底亚等。由于史料失传,人们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著述状况所知甚少。对智者的研究,主要依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等人有关著作中对智者活动、论断的记载与转述。
(来源:文章屋网 )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