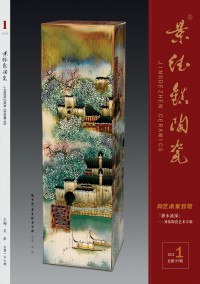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的观与思

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陶艺学会等主办的2021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展览,主办方的视野是国际性的,除中国外,展览汇集了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多国陶艺家的作品;策展人的眼光既青睐知名大家,也关注年轻新秀。展览使用了中性的“陶瓷艺术”名称,而未使用具有一定特指含义但又语意模糊、尚未达成共识的现代陶艺、当代陶艺等称谓,也暗含包容多种艺术风格的策展指向。
一、旧作和新貌
按理说,“双年展”是呈现艺术前沿面貌的展览形式,艺术家应该拿出新作,但在此次“双年展”中,尤其是在特邀艺术家单元中,有不少早年旧作。不过,由于展品说明文字中并未标明作品创作时间,我只能凭以往看展记忆来判断是否旧作。正如哲人所谓“人总是带着已有的认知去观看世界”。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些熟悉的艺术家,我或者多次见过他们的作品,或不同程度地认识了解作者本人,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20世纪八九十年身于现代陶艺创作。吕品昌《中国写意No.44鉴宝者》、吕金泉《庭院婴戏》、金文伟《景德镇•一种方式》、周武《山望》、戴雨享《金榜题名•明帽》、孟庆祝《壶神系列》等都在多年前展览上见过,刘建华《水中倒影》亦是20年前创作的老作品了。有些作品,穿过时间长河沉淀为经典,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如周国桢创作于2000年的作品《静观》,斑驳陶土捏塑出猫头鹰身形,白瓷嵌出圆睁双目,材料和造型的表现水乳交融;有些作品,经过时间洗涤后留下的是历史价值、纪念意义。李茂宗作品《天合系列•内在自然No.6》,破形与裸露的泥,让人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李先生造访大陆时的现代陶艺启蒙时刻。秦锡麟的青花釉里红《迎春》、青花《芦苇深处》,此类风格作品因开创民间青花和现代艺术交融而在中国现代陶艺发展进程中留下印记。对更多作品,我难以分辨新与旧,因为它们在我对艺术家原有认知之外:韩美林作品《一线之间》,通身黑釉、镶器造型,一条曲线从上到下贯穿器身,线条似乎来自远古岩画,也可能是连绵草书。钧瓷作品《烟霞飞瀑》,器物表面厚薄深浅不一的釉色和坯体表面的利落切割,挥洒出了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动势。两件作品在简洁的形式中蕴含着灵动与力量,显示出艺术家宝刀不老。陆斌《备忘录》,未看作者名字时以为是年轻学生作品,初看之下,让我联想到刘建华的《白纸》,但刘的作品瓷质白纸的尺幅甚大,陆斌作品尺寸单元只有50cm见方,看点在于这是一件和观众互动的作品——布满皱褶的瓷纸上写满了彩色的观众签名,据说是展览开幕式时写下,有待于艺术家再次对其低温复烧。陆斌就像一名老战士,一直在实验的路上,不断有新的推进。陈光辉作品《磐石》,与他之前创作多年的《椅子》系列虽形象不同,但作品中蕴含对雕塑体量、力量的追求仍一以贯之。黄焕义好像创作得越来越自由,《不可控》放弃了造型、放弃了审美,也放弃了跟观众的交流,不仅不可控,还不可说,难以理解其意。八旬老艺术家刘远长的《铜墙铁壁》比写意更写意,数个简化为块状体的人物,具足了铜墙铁壁的神韵。桌椅、桌上的瓷画、陶瓷文房,布置出了晚明士人的书房一角,墙上悬挂的瓷残件有点类似陆斌《化石》之趣味,这组作品迥异于赵兰涛之前以青釉、青花的壶、人体等造型为主的雕塑创作,而以他者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表达。钞子艺、钞子伟兄弟的《史迹》,展台上的一地旧书,是于写实中夸张变形表现老物件的创作风格延续。我从这些创作数十载艺术家们的参展作品中联想到,艺术家的风格应该有变,亦有不变。不能始终不变,落入僵化之境地,也不能总是在变,尤其不能总是循外界风向而变,变化的推动力应该主要来自自身成长经历及对外界的思考与回应。当然,“双年展”中更多的是年轻人的作品,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印象较深的有不少肖像作品,胡林琳的雕塑取名《林琳》,可爱的青春女孩,不知是否作者本尊。吴小艳《心象》也是一组肖像作品,一男一女间用链条拴着的人物关系,为这组人物雕塑制造了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潘炎金《二月豆蔻》,憨态可掬青春懵懂的半身肖像也许是作者的同伴们。新面貌中,或者是新材料的运用,如饶舜《哲之折No.1生命》,用彩色超薄泥如同折纸一般制成与传统陶瓷器物截然不同的新形态;又或者是对熟悉材料的创新使用,如胡海英《山水系列之一》,对数块工业瓷板进行错层拼接,使得在瓷板上绘制的只以线条勾勒和大块填色的山峰,形成山势连绵、远近不同的视误差。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现代陶艺第一批干将的“二代”和学生也已崭露头角,孟庆祝女儿孟胡蝶的作品《找碴对缝•回望“高岭”》,突出了金缮和锔瓷,它们作为修复瓷器的实用工艺,与修复“高岭”所象征的传统这一社会命题直接地联系起来。吕品昌的博士研究生黄山作品《汉风•列传》占据了上百平方米空间,泥片卷塑的人物、车马形象结合体量巨大的陶瓷建筑元素,雄浑飘逸,塑造出了一个年青艺术家对古代士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敬仰和向往;罗小平的硕士研究生杨起帆作品《侠系列》,或站或坐的三个人物,皆一身白袍、一顶斗笠,写意雕塑,颇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之洒脱气息。
二、材料和观念
此次展览上,老外的作品基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它们大多数更着意于表现陶瓷独特的材料语言。绘画的本质如果如格林伯格所言是“平面性”的话,那么陶艺的本质是什么?荷兰艺术家BabsHaenen的作品《溪流低语》,瓶身上的扭曲、堆叠、褶皱,有意破除通常陶瓷器物表面的平整、光滑。澳大利亚艺术家TedSecombe《夏日的雨》,在饱满的瓶身上,流畅的线条如雨丝流淌,结晶釉如绽放的花,宁静中有着古典的美感。美国艺术家MarcLeuthold《奥德利》,不规则造型形似盘子,目测非常薄,从圆心向四周发散美丽的细密刻纹,在边缘处有着明显裂缝。大多数老外作品似乎传递和强调的都是泥、釉、火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有些佳作在材料、技巧和观念上都有精彩表现。刘丹华作品《锦灰堆》,以弥漫于整个墙面的灰朵和两个展台上的大块灰堆组成,采用景德镇传统捏雕手法,作为艺术作品的灰,似花,形不是花;似灰,材质非灰,在艺术的仿真中,隐喻着繁华散尽、灰飞烟灭,有惨烈的美感。而固态的瓷定格了气态的灰,不仅是易碎和坚硬的对比,也可见人类总想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雄心与痴心。陈丽萍作品《云之思》《海之意》,以刻花装饰手法营造海浪波纹、云纹,在器物上方本应是纽盖处,置以一尊小巧的佛像,瞬间化平凡为神奇。张小池《化象》,是一组六个半身女孩雕塑的集合,两种材料的结合别有意趣,头部、肩膀、手部是涂了白色化妆土的陶瓷,身体部分则是褐色铁架子,女孩们有的手按着鼻子、有的手托着下巴、有的手盖着眼睛、有的手捂着胸口,动态变化的手俏皮地把瓷和铁两种材料关联了起来。熊开波的作品《天地正器系列》很好地把握了陶瓷和青铜器两种材料兼而有之的感觉,而非用陶瓷去效仿另一种材料语言,作品中既有沉郁厚重,也有勃发的刚强。杨若飞《梯田印象•四时之景•孟春No.1》是具象地貌的抽象表达,对真实物象进行提炼、提纯,以简笔画的线条勾勒、黄与灰等釉色填色,以及刮去釉后裸露出土地般的颜色,达成与梯田山路一致的视觉感观,几乎是以儿童画般的单纯,巧妙绘制一幅宛若梯田地貌航拍图,可谓得其神、简其形。也有一些作品,我看到了作者想要强调的材料语言和复杂的技艺手段,但我没看到他想表达什么。获得高岭奖银奖的谷金康作品《束缚与突破》,用白瓷泥做出了丝绸的细腻质感,但直至看到作者接受采访时言“作品在外观上采用了传统的定窑象牙白釉色,在被包裹器物的选择上主要选取了孩儿枕、龙首大净瓶、童子诵经壶等古代定窑瓷器中的代表性器型,主要想表达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学院毕业生回到传统的陶瓷产区后渴望突破传统的束缚,以求创新的强烈愿望”,我才对作品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张威的两件参展作品《针究》系列,造型不同,黑色表面均密布细小圆点,据说一件作品要扎入数万颗大头针,但我觉得其最大意义可能只在于炫技,展示过程的复杂性。同样还有郑清海《千手》,密密麻麻白色瓷泥手的堆叠,是手,还是手,除了炫技我没看到别的。耿雪的影像和装置作品《金色之名》,则带来更多哲理思考。影片呈现了一个黑白世界,泥土塑造的人物仿佛在真实与幻象、阴阳两界之间穿梭。他们共同侍奉着一件庞然大物。这件巨物内部呈现金色,发出诱惑的光色与声音,使人们前仆后继、劳作不息,他们取出彼此身体的一部分,完全吞噬。这个看不见全貌的庞然大物,是炼丹炉?纪念碑?还是传说中的巴别塔?它仿佛是欲望和权力、集体化乌托邦神话的显现。耿雪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含义,而以隐喻和象征手法,支撑起一个开放、多义的作品。陶艺的本质是什么?这不是容易随口给出答案的问题。但我想,材料只是手段,技巧也是手段,它们都不是本质,也不是艺术创作的目的,艺术终究还是表达观念、情感的审美创造。
三、模仿和学习
在规范标注的前提下,一篇有独到发现的论文仍然可以引用他人成果,但一件志在突破的艺术作品,可以“引用”别人的成果吗?获得高岭奖金奖的张琨作品《画像系列》,以马赛克式的瓷片镶拼方式,用数万块不同颜色、不同肌理的小瓷片,组成十幅人的眼部图像,让人想起一句老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观眼识人,从中看到年龄、神情各异的人,也像是可以放大看去,看到芸芸众生,堪称致广大而尽精微,所表现的对象是广大的,而手段极精微。有人从中联想到了纽约地铁站的马赛克拼贴画。例如:86街车站里艺术家ChuckClose的十二幅大型马赛克瓷砖肖像画,但我认为他们的相同之处只是在于使用马赛克拼贴作为手段,而马赛克镶嵌画的历史可溯源至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手段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可以堂堂正正为我所用。以我有限的艺术观看经历为参照,我在展厅里发现了一些抄袭抑或模仿之作:刘伟琪作品《报纸•状态系列No.1》与陆斌2012年创作的《大悲咒•3》非常相似,同样的卷轴状,同样有残破,只不过陆斌之作是古旧经卷及佛经文字,而这件作品则是卷起的旧报纸及新闻文字,想当年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黄鹤楼》一诗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相形之下,古人有自知之明,今人有掩耳盗铃!抄袭和模仿如何区分?叶永青对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的画当然是正宗抄袭——几乎一模一样的构图和色彩,而模仿的情况更为复杂,既可能是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必要的学习,也可能是偷懒的效颦,例如:蔡峙雄《册页系列•奇石》,在瓷板上画国画册页,与陈丹青在油画布上画印刷品画册,算是一种低劣的模仿吗?艺术家展望自1995年开始创作不锈钢雕塑作品《假山石》系列,在艺术圈几近无人不晓,作品在人造不锈钢材料和东方园林山石这原不相干的两者间营造张力,是一种逆向的思考。此次“双年展”中数个形似《假山石》的作品,不排除对展望作品模仿的可能,但只是用陶瓷材料模拟假山石的皱、瘦、透、漏,偏向于正向的美化,熊祖超《石空•山水之骨》如此,詹伟《蓝金符号》也如此,只是詹伟在表面做了蓝釉、金箔、缩釉等装饰处理。于超的青花动画短片作品《春风如约》,剧情取自于张钊维导演、2015年在中国台湾首映的纪录片《冲天》。该片讲述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空军英勇抗战以身殉国的史实,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的画面以动画方式呈现,《春风如约》不仅取用了剧情,部分画面更与纪录片高度一致。在对获奖艺术家的采访中,于超说“构成短片的每一帧,都是手工绘制的青花瓷板,先后经过了故事设定、镜头设计、动画设计、泥板制作、转描、烧制、拍摄、后期制作等工作流程”,但作为动画片关键环节的“故事设定、镜头设计、动画设计”都取自于《冲天》,最起码,应该写上“改编自纪录片《冲天》”吧?
四、作品和空间
正如学者所总结的“关于物性、剧场性与场域特定性已成为以装置艺术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的所谓三大美学特征”,“双年展”中的装置艺术,与展示空间共同构成了更好的艺术表现。黄春茂作品《“约翰•曼德威尔爵士”的中国空间》是一个封闭的艺术空间装置。黄春茂历来擅长高贵雅致的礼品瓷设计,在这件作品中,他借用欧洲14世纪《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的描述,再现了游记中描绘的华丽中国宫殿:桌上摆陈着他本人设计的茶餐具瓷器,周围搭配了镀金的树枝、华贵的椅子等,富丽堂皇而神秘,而这一切用墙壁围合起来,观者只能通过墙上的孔洞窥探,这很接近于杜尚最后一件作品《给予:1、瀑布,2、点燃的煤气》从门洞里窥伺的观看方式。这个封闭的艺术空间装置,用并不特殊的瓷器、家具等物品创造了一个特殊场域,也创造出新的意义。朱乐耕作品《生命之廊桥》,泥片卷成的花苞、白色卵石,它们本来是艺术家之前为韩国酒店创作的陶艺壁画之局部,这次被设计为两个独立的墙面,中间以廊桥贯通,观众从廊桥走过,即是走入作品构成的场景,360度无死角地体验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一种在场的“剧场性”,即观者不再是静观凝视艺术作品,而是进入由装置构建的剧场与之互动。刘丹华《锦灰堆》的展陈,也是营造出了天和地的感觉,墙上的灰朵犹如飘散在空中,展台陈列着如同地面上的大灰堆,全方位地呈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也不是所有的大型装置作品都能创造出剧场性,董枫作品《苹果》,在几十平方米的展台上堆满了数百上千只外形相同的陶瓷苹果,不知是否受到了艾未未陶瓷《瓜子》的启发,但我只看到了以巨大博人眼球、以重复取胜,总之我从它们身上一无所获,无论是美感还是观念启迪。不得不说的是,此次“双年展”展出的几乎都是很纯粹的艺术作品,虽然也有《疫情中的白衣天使》《不负韶华》两件抗疫主题作品,但总体而言,与当下美术界大热的主旋律创作保持了一定距离。陶瓷是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创造,也是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但是作为现代或者当代艺术一部分的陶瓷艺术,并不居于当代艺术的主流地位,不过就像硬币的两面,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方面,陶瓷艺术远离资本和政治,较好地保持了艺术的独立和纯粹性;另一方面,陶瓷艺术太沉醉于对材料、工艺的把玩,太强调自身尤其是材质的特殊性,这使得它缺少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学习交流,也缺少和社会的互动及表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如文学上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也如戏曲中的宋元杂剧、明清传奇,怎样的陶瓷艺术将代表这个时代,将进入历史?从“双年展”中,可以看到雕塑、装置、器皿、绘画等多种形式,看到陶瓷、钢、木、亚克力等多种材料,看到动画、影像等跨媒介作品,看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创造力,瓷的可能性更趋丰富,这当然是好现象,毕竟,只有百花盛开、百舸争流,才能创造这个时代艺术的盛大气象!
作者: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