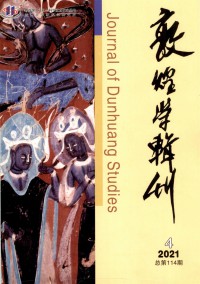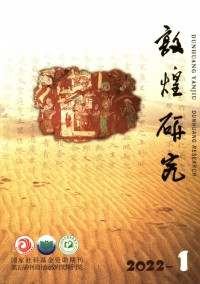莫高窟教案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莫高窟教案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莫高窟教案范文第1篇
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集结团队的智慧,充分调动了所有成员的主体意识,使所有教师在教研活动中都能行动起来,有所收获。尤其是在评课环节,改变以往感性的评课方式,评课教师依托课堂观察数据,从课程性质维度、教师教学维度和学生学习维度,分别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观测和分析,以形成更为科学、理性的教学评价体系。
一、 同备一节课,集合智慧出范式
我校五年级语文教研组成为这种研讨形式的先行者。在“课堂:给学生带得走的阅读力之深度教研”主题活动中,五年级的张老师为大家呈现了一堂研讨课――《莫高窟》。整节课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思路清晰,准确把握了文本的重难点。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让学生通过优美的画面去体会感悟莫高窟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整节课流畅自然,感性中凸显理性的深度,赢得了专家和老师的充分肯定。
“深度教研”凸显集体的智慧,教研组选定合适的文本,所有成员同备一节课:先是教师自己研读教材,链接相关素材,提出思路,进行说课,在说课中去粗取精,完善教案。如:重点对文本中的过渡句的教学说课,《莫高窟》一课中在描写彩塑和壁画之间有一个过渡句:“莫高窟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理解过渡句是引导学生揣摩作者写作思路的切入点,是引导学习谋篇布局的契机。通过一对关联词连接起描写莫高窟的两个重要部分,一句话连起文章的两个段落,这样承上启下的句子便是过渡句。过渡句是一座桥,衔接层与层之间的意思,过渡得好,文章就会前后连贯,结构严谨。通过这样对于文本中重点内容的细致说课,让教师在备课时更能准确把握教材主体,训练重点准确。说课完毕,再由年级骨干老师组成备课核心组,整合老师们的教学设计,带着大家的理解和思考,完成新的教学设计。
二、 同上一节课,文本细读抓问题
有了合适的教案,接下来是课上的体现。第一轮研讨课中,一位教师利用新的教学设计上完课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1. 从教师指导有效性来看,教师的讲解过多,约束了学生思维的广度;有些问题过于细碎,提问设计缺乏整体性。2.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关注度不够,教学机智还需进一步提高;评价方式也较单一,未能持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3. 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形式基本合理,但是在个别环节的时间分配上,应视难易程度给予相应的缩减或延长,老师提出的研究问题目标要明确,以便学生更好地展开研究。
在小组教研时,针对这些问题再次修改教案,同时根据第二位执教老师的个性风格,设计出新的教案。第二位老师的课要关注之前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同时,还要关注是否有新问题生成。于是,第二轮研讨活动开始了。
三、 评价的转变,关注程度趋理性
深度教研,重要的转变点便是评课方式的改变。以往评课都是老师们根据自己听课的感觉,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而深度教研却是通过一个个鲜明直观的数据,理性化地对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听课时,在教室的四个角落都坐着手拿观测表的老师,位置不同的老师观察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教师需要高度集中,及时记录观察内容,同时进行简要分析。如观察“教师的教学机智”,具体从学生的错误类型、教师对错误的态度和教师对错误的处理三个方面进行,其中,学生的错误主要分为知识性错误、表达错误等六种类型;教师的态度分为赞许、接纳等五种类型;教师的处理分为鼓励、引导、自己指正等九种类型。在观察的过程中,这一组的教师记录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典型行为和频次,并尝试着从这些方面去研究教师应该如何处理学生的错误。在评课时,评课教师通过对这些具体数据的解读,对执课教师的教研课进行准确的评价,既肯定课上所表现的教学机智,又给教师提出了更加合理化的建议,引出更加深刻的思考。
莫高窟教案范文第2篇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寓言故事的基本情节及其表现方法,熟悉其配画、插图的画法风格,进一步了解文学与艺术形式的联系。
过程与方法目标:用丰富的绘画手段表现单幅或者连环画面,在合适的机会利用学生的寓言配画作品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进行策划、制作表演与展示,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创造力和综合实践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体会寓言和神话故事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领悟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人文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把握住寓言和神话故事的中心寓意,并选择恰当的情节把它表现出来。
难点:寓言或者神话故事中最能体现寓意情节的选择以及画面绘画艺术的个性化设计。
课前准备:
教师:寓言、神话资料,范作,学生作品等。
学生:寓言、神话资料及颜料、彩纸等绘画工具。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角色表演(狐狸和乌鸦)
师:你知道这什么故事吗?选自世界上最古老、影响最大的寓言《伊索寓言》。由于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富于哲理,在全世界流传两千五百余年而经久不衰。
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为我们熟悉的‘寓言和神话故事’配画上插图。(揭题)
二.新授
1.欣赏壁画、石画(出示古老的石画)
师:寓言和神话是人类最早的文化产物之一。人类很早就会使用这种极古老的文学形式,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二千多年前的汉画像砖上画神话故事。都是人类生活智慧和艺术想象力的结晶。
2.什么是神话?说一说你熟悉的神话故事。
神话:通过对各色神话人物的塑造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渴望。
(《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沉香救母》《嫦娥奔月》《精卫填海》……)
3.什么是寓言?说一说你熟悉的寓言故事。使人趋向聪明、理智、沉稳。
寓言:通过简洁幽默的小故事来表达深刻的道理。
(《狐狸和乌鸦》《龟兔赛跑》《揠苗助长》《班门弄斧》《疑人偷斧》《杯弓蛇影》……。)
4.看图区分寓言和神话,进一步了解寓言和神话的区别。
5.师:下面就让我们来做个游戏,怎么样?(看图猜故事)
师:你是怎样猜到的?(引导学生说出画面创作的要素)
生1:
我是通过故事中主人公特点看出来的
师:(板书:主人公的特点)
生2:还要看故事的主要情节与场景
师:(板书:情节与场景)对啊,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或几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情节,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的特点,就会很容易的表现这个故事了。
师:比如说揠苗助长,我们应该抓住哪个故事情节
生:农夫乐呵呵的正在往上拔禾苗。
师:狐假虎威呢?
生:……
三.欣赏优秀学生作品
四.合作与互助
创作表现
1.小组讨论
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寓言和神话呢?现在让我们分小组讨论一下,在讨论之前呢,老师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们首先来选择一个故事,再来分工合作,看看故事适合哪种方法来表现。
生:(讨论)
2.学生汇报
师:哪个组先来说说?
生1:我们组每三个人又分成了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画一幅画。
生2:我们几个商量了,XX、XX和XX画背景。XX、XX和XX主要人物,最后我们几个一起来表演。
师:你们组太有创意了,让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还有哪个组想汇报一下?
生3:我们想用彩泥来表现《
》。
生4:我们组想画寓言故事《龟兔赛跑》,一共画4幅连续的画。
师:那能说一下,在这个故事中你们要抓住那四个主要的情节画呢?
生4:第一幅是起跑的时候、第二幅是兔子跑在乌龟的前面、第三幅是兔子睡着了,乌龟超过了它、第四幅兔子在奋力的追赶,而乌龟却取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
师:看来你们所有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任务,那老师就期待着你们的作品了。
3.学生分小组创作
五.表演与展示
快乐评价
1.欣赏学生作品
师:(完成的作品粘贴在黑板上)欣赏各小组作品,说出你最欣赏的作品,在选择一幅说出应该改进的地方。
生:……
2.第二小组运用做好道具,上台表演。
生:(表演)
师:同学们,他们表演的好不好?
生:好
师: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送给第()小组。
同学们,故事伴随着我们成长,神话让我们有一双飞翔的翅膀,寓言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道理,那么老师也希望,在今后的每一天一比一天过得更美好。
六.拓展与延生
激发兴趣
1.欣赏运用其他材料和方法表现的故事作品,拓展学生的创作思维。
2.自行设计主人公,自编自演一个寓言故事。
板书
寓言和神话(造型大胆夸张)
莫高窟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
一、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除各地区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光外,区内独特的民族风情,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人文景观十分,游不尽的丝绸路,看不厌的九寨沟,神秘的莫高窟,还有黄龙、天山、昆仑、峨眉、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仅中国30处世界遗产内,西部12省区就有9处,其中文化遗产5处,文化与自然遗产1处,自然遗产占3处。中国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院研究显示,在西部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100多种垄断性旅游资源,其中已开发的只占总量l/7。无论是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自然旅游资源,还是文物古迹、民风民俗等人文旅游资源,都有着巨大的挖掘潜力。
但就旅游业目前的总体发展状况来看,水平比较低,总量规模不大,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且地区间旅游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实际属于低投入低产出,与资源丰富程度不相符,存在“守着金饭碗没饭吃”的情况。尽管西部各地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仅2001年、2002年和2003年三年期间北京市的旅游外收入是西部12省区旅游外汇收入的1.7倍和1.5倍,广东省的旅游收入是西部12省旅游收入的2.6倍和3.5倍。由于西部有效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数量较少,进而形成了西部旅游资源的“丰富区”,旅游开发“低谷区”和旅游经济“贫困区”的现状。另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市场结构也不平衡,入境旅游比例较小,是目前西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制约西部旅游业发展的“瓶颈”所在。
(一)观念滞后。
旅游开发需要突出西部的地方特色。西部旅游业目前高成本低效率的开发模式与陈旧的旅游业发展观密切相连。目前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仍在走与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走过的老路,依照东部经验,并没有开发西部特色,走新路子。西部旅游业观念之所以滞后,其主要原因在于西部经济的落后。
(二)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尚未形成特色互补效应。
在东部地区,旅游业已形成了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产品和特种旅游产品并存的多元化产品供给结构。但西部地区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显得不足,旅游产品仍以观光旅游为主。即使在观光旅游产品中也仍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现象,以相互简单模仿为基本特征的“塑像热”、“造庙热”、“仿古一条街热”、“人造景观热”轮番出现,致使旅游产品间的特色无法形成互补效应,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在相互抵消中下降。
(三)投资主体单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能对旅游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良好的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旅游景观的吸力不仅来自于其本身的旅游美学价值,也来自于其可进入性。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西部地区交通设施较为落后,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与东部地区相比都有较大差异,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公路的通车里程里占了全国的55%,通车密度比较低,尤其是代表现代化交通的高速公路,近年来所有大的发展,但总里程数仍然较低,无法满足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甘肃敦煌这一世界知名的景点就因交通不便而对其旅游收益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目前尚未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投资严重依赖政府。
(四)产权不明晰、责权不明确、管理体制落后。
落后的旅游产业观、管理体制加上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最终难免会促成难以扼制的破坏性的资源开发行为。西部地区旅游开发经营中的体制问题,主要是政企不分、责权不明。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旅游景区普遍实行公益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低投入、低产出;低开发、低保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公益型管理普遍地为经营型管理所代替,资源开发投入大幅度增加,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企不分的经营型管理并非一定能够达到“高收益、高保护”的目标,反而束缚了许多旅游景区的发展,也造成了许多因非理性决策而导致的资源滥用现象。旅游景区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可以解决旅游开发及保护过程中的政企不分问题及资金不足问题,从而促进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良性互动。
二、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条件
西部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原始性、独特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的差异性,构成了世界级的旅游资源,是西部发展的优势所在。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机遇。
(一)政府导向功能进一步加强。
西部要发展,就必须培育出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而投入少、效益高、关联性强的旅游业显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所以政府在战略上倡导“大力发展旅游业,把旅游业培育成为西部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已有多数地方政府将旅游业列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二)交通状况明显改善。
西部开发公路建设总体计划目标是打通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通江达海连接周边国家的通道,完成西部地区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等项目的建设。“十五”期间,交通部投入西部交通建设的资金将不少于493亿元,占交通部用于公路建设投资总量的52%;加大对西部地区乡村通达工程的投入,投资比例将占到通达工程投资总量的70%;预计用于西部地区交通建设的科研开发资金达到10亿元。另外,国家鼓励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到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三)旅游设施更为齐全。
伴随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西部地区旅游设施较以往也大为改观,各地都建立了设施齐全的星级宾馆、饭店,旅游景区、景点建设更为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管理更加规范。以新疆冬季旅游为例,它起步比东北晚,近年来,新疆用于冬季旅游设施的投资达3亿多元,是前50年的总和。目前全疆己有大大小小近百处滑雪场,其中天山国际滑雪场的一条天然滑雪道就长达6000米,这在国内首屈一指。
(四)旅游商品更加丰富。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积极开发旅游商品,完善旅游服务体系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开发具有以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为主旅游商品是现代旅游经营者为之奋斗目标之一。很多地区均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地方的独特的旅游商品,制造品牌效应,不断的推陈出新,观光节、香包节、文化庙会、旅游交易会等都是旅游商品展示自己魅力的舞台。
参考文献
[1]肖星,中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开发探索[J],开发研究,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