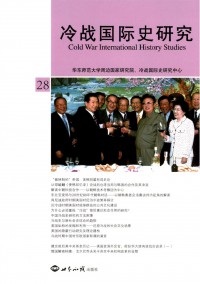战士的名字
战士的名字范文第1篇
志愿军烈士知多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抗美援朝战争馆”,是展示志愿军烈士功绩的地方。笔者独自站立在“志愿军烈士墙”前,怀着崇敬的心情,凝视着墙上的数字。
“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人。
“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市、自治区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在此之前,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一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单独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
笔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情况是:战斗和事故死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医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还有部分患病者病死。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2000年10月16日,据《报》所提供的数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曾组织工作人员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的烈士人数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指出,从20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到除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的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于2006年公布了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权威的数字。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报道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
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披露的伤亡数字是1,168,160人。
1995年7月,美国官方在华盛顿博物馆里的朝鲜战争纪念馆旁,修建了朝鲜战争美国士兵群雕和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的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失踪者8177人;受伤者103,284人,合计165,707人。
关于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笔者曾采访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原副司令员。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对笔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低。”
183,108名志愿军烈士,祖国人民想念你们,如今你们都在哪里?
约18万志愿军烈士长眠在朝鲜
笔者曾采访过志愿军老兵曹家麟。曹家麟,1950年10月入伍,原志愿军第六十七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三次以志愿军老战士的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地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战士的名字范文第2篇
骑士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之前。大约在11世纪中期,一批意大利阿马尔菲商人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向当时统治此地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提出申请,希望建设一个意大利会馆。慷慨的哈里发将城内基督徒聚集区的一小块土地交给他们支配,而该区域正好邻近圣墓教堂和圣母玛利亚修道院。随后,意大利人重建了之前被战火摧毁的医院,并建立了另一所女子医院。在第一次前,一位本笃会的欧洲修士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是传奇人物――“被祝福的”杰拉尔德。他被医院的救死扶伤善举感动,打消了返回欧洲的计划,留在耶路撒冷并投入医院工作,最终成为男子医院的院长。他德高望重,乐善好施,积极救助基督教朝圣者,也医治穆斯林患者。
随着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克,杰拉尔德和他的医院受到了十字军战士的敬仰,声望日隆,于是杰拉尔德和几位修士脱离了原来的本笃会,建立自己的慈善组织,要求修士“安贫、禁欲、听命”,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慈善、医疗和修道组织,并最终得到了教皇的官方册封。由于十字军控制的圣地并不太平,在保护欧洲朝圣者的过程中,医院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医院骑士团。1120年,杰拉尔德逝世后,法国人雷蒙・杜・皮伊继承了他的遗志,并第一次采用了“大团长”这个称呼。与悲天悯人的老团长相比,新团长更加冷静、干练,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骑士团逐渐从保护朝圣者的医生、慈善修士转变为骑士和职业军人。而与普通的为了救赎或是冒险获取财富的十字军士兵不同,医院骑士团更加安贫乐道,更加吃苦耐劳,很快就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对其政局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在之后十字军国家与穆斯林之间的征伐中大放异彩。
医院骑士团最鼎盛时,在耶路撒冷国拥有7座大的要塞,140多座其他建筑。但在1187年哈丁之战中,由于耶路撒冷国指挥上的失误,在阿拉伯强人萨拉丁大军的围攻下,包括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在内的基督教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圣城耶路撒冷更是被迫向萨拉丁投降。这段历史在电影《天国王朝》中有戏剧性的展示。此后,朝圣的时代逐渐远去,十字军运动也陷入低潮,随着最后的堡垒阿卡的陷落,医院骑士团于1291年从战火中的阿卡撤退到爱琴海上的塞浦路斯,后又来到罗德岛,将这座海盗出没、近乎荒芜的岛屿构筑成地中海东部最繁华的贸易口岸和坚固要塞。
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里时,罗得岛上的医院骑士团是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惟一的基督教力量。15世纪到16世纪初,医院骑士团独自在罗德岛上抵御了奥斯曼帝国和位于埃及的穆鲁克苏丹国的3次围攻。1522年,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指挥20万军队乘坐着400艘战舰围攻罗得岛,而骑士团仅有7000余名士兵,在此实力对比悬殊的形势下,骑士团依然独立坚守了6个月,消灭土耳其军队达5万余人。最后,骑士团与土耳其人达成协议撤出罗得岛。
很快,骑士团在欧洲君主的支持下,来到了有着“地中海心脏”之称的马耳他。马耳他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得现名,是“蜂蜜岛”的意思,因为当时马耳他盛产蜂蜜而闻名地中海地区。1565年,来到马耳他仅43年的骑士团,再次面临苏莱曼一世的围攻,在又一位传奇般的大团长瓦莱特的指挥下,上演了荡气回肠的马耳他保卫战,令全欧洲惊叹,赢得了“欧洲之盾”的美誉。在随后的岁月中,马耳他的医院骑士团长期扮演着南欧安全屏障的角色,且长期继续着对穆斯林世界的“圣战”,以马耳他为基地,通过海上力量沉重地打击穆斯林海上贸易,遏制其向南欧的扩张。
瓦莱特和大团长宫
从国土面积来看,现在的马耳他仅有316km2,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184名,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袖珍国之一。马耳他是扼守大西洋通往地中海东部及印度洋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海运的枢纽。由于马耳他孤悬地中海中心,故有“地中海心脏”之称,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诺曼人、西班牙人、圣约翰骑士、法国人、英国人都曾经占据这片列岛。
笔者走在马耳他的大街小巷,感受着东西方文明在城市中的碰撞和融合。来到马耳他,首先要参观的就是位于首都瓦莱塔的骑士团“大团长宫”。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位于大港区北部,正是马耳他保卫战中指挥骑士团奋勇抗敌的大团长瓦莱特主持建造的,城市也以其名字命名。瓦莱特本身就是一座坚固的要塞,在近500年的时光冲刷下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面貌。瓦莱塔建在希贝拉斯半岛的高地上,三面环海,仅一面通过地峡与陆地相连。主城门有高达47m的巨型棱堡进行防护,两侧分别是圣雅各内堡和圣约翰内堡,可以给来犯之敌形成交叉火力。海角顶端是在大围攻中坚决抵抗土耳其军队的圣埃尔莫棱堡要塞,已经和瓦莱特首都融为一体,互为犄角。
笔者来到瓦莱塔城市的中心――共和广场,广场前屹立着著名的骑士团大团长宫(Grand Masters Palace)。该宫殿建于1570~1580年间,是昔日骑士团大团长的官邸,今为总统办公室和议院所在地。与其他国家戒备森严的元首府邸不同,这里更像是向游客宣扬马耳他历史,特别是医院骑士团丰功伟绩的博物馆。
走进大团长宫,即可看到地中海式的海神庭园。其四周的回廊建筑极具特色,海神的雕像耸立在庭园中。骑士团在马耳他时期,从陆地骑士逐渐变成了一支专业的海军力量。参观大团长宫,就必须细细地欣赏宫殿中那些华丽的厅室。精美绝伦的壁画展现了骑士团波澜壮阔的历史,穹顶上那庄严的医院骑士团特有的八角十字徽章更增添了几分庄严。
其中有一副著名的奥斯曼军队围攻马耳他森格勒阿半岛的画作。画中无数土耳其士兵将两座棱堡要塞团团围住,中央是森格勒阿半岛,另一侧是比尔古半岛。为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瓦莱特在两座半岛中间用木桶搭起了一座浮桥,可随时在两座要塞中调动兵力,提高作战的机动性。而另一幅画作显示的则是骑士团在独自抵挡奥斯曼军队进攻长达数月后,终于迎来了西班牙援军的登陆。这支多达8000人的西班牙精锐部队,在从意大利返回的部分医院骑士团骑士的带领下,彻底击溃了土耳其人,解救了马耳他之围,这就是发生在1565年的著名的马耳他大围攻事件。
还有一副画作描绘的是3艘医院骑士团海军长期使用的桨帆船,围攻一艘悬挂着土耳其新月旗的奥斯曼帝国盖伦大战舰,显然这艘奥斯曼战舰已经被骑士团海军所俘获。其实,在马耳他大围攻数年后的1570年,包括骑士团海军在内的欧洲基督教神圣联盟海军,以206艘桨帆船和6艘加莱赛战舰,与拥有216艘桨帆战舰、56艘桨帆快船和64艘小型弗斯特船组成的庞大土耳其海军,在希腊勒班陀以西64km的帕特雷湾交火,著名的勒班陀大海战打响了。医院骑士团派出3艘桨帆战舰与数倍敌军展开激烈的海战,最终寡不敌众,血染海疆。但神圣联盟取得了最终胜利,并且此战彻底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实力,令马耳他在今后200年间再也没有受到后者的严重威胁,他们的战舰让穆斯林谈虎色变,八角十字旗飘扬在地中海蔚蓝的海面上。
此外,宫殿中还挂着多名骑士团大团长的画像,这些大团长或着戎装,或着黑色修士服,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自信。其中,有一名叫作曼努埃尔・平托・达・丰塞卡的大团长画作最为精美,他头戴银色假发,身着银色铠甲,身后是作为战利品的穆斯林星月旗帜。丰塞卡作为第69任大团长,于1741~1773在位,是18世纪统治时间最长的大团长,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不再是欧洲最大的敌人了,对地中海也没有了野心,反而为了遏制俄国的发展,欧洲还需要依靠土耳其,因此,此时的地中海风平浪静,一片和睦。
但和平生活最容易让人腐化堕落,骑士团越来越奢华,大团长也安于享乐,丰塞卡更是首次采用了“显赫的殿下”这种称谓,并公开在纹章中添加了一个王冠标志,显示出此时的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已经将自己视为君主,而不再是“被祝福的”杰拉尔德院长所倡导的、瓦莱特大团长所坚守的谦逊的修士了。不过虽然丰塞卡挥金如土,但他对马耳他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创建了马耳他大学,将瓦莱塔港区设置为自由港,进一步刺激了马耳他工商业的发展,促成了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同时,他也是骑士团在马耳他岛后期少有的铁腕人物,带领骑士团抵挡住了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王国企图对马耳他岛的兼并。丰塞卡之后的继任者或资质平庸,或缺乏魅力,作为军事组织的医院骑士团的光辉逐渐消散,而骑士们也在地中海的暖阳下丧失了斗志,最终被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皇帝赶出了马耳他岛,渐渐淡化了军事色彩。
军械库中的铠甲珍品
在大团长宫的另一侧楼廊内,有两个军械展厅,展示着骑士团各种盔甲、刀剑、枪炮等,这里其实正是医院骑士团的军械库。
军械库以15~18世纪的盔甲和武器为主,这一时期正是医院骑士团从罗德岛大围攻中败退到马耳他,以及在马耳他抗击土耳其人入侵的时期。特别是1530年,查理五世向骑士团移交马耳他:“将马耳他岛、戈佐岛、科米诺岛赏赐与医院骑士团,以使他们能够安宁地执行宗教义务,保护基督教社区的利益,凭借其力量和武器打击神圣信仰的奸诈敌人。作为回报,骑士团应于每年万圣节向兼任西西里国王的查理五世进贡一只游隼。”这也是马耳他之鹰的由来。比较可惜的是,军械库中没有找到13世纪十字军时期经典的医院骑士团链甲。在那个年代,医院骑士们通常穿着全身锁链甲,头戴桶盔,外面穿着黑色修士罩袍、戴着头蓬,胸前绣有白色的八角十字,手持长剑和盾牌。这样的形象在许多影视、游戏作品中都有体现。
军械库中第一件盔甲是一套15世纪骑士团士兵的板甲。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在盔甲工艺上也出现了重大变革,全身板甲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链甲。医院骑士团也接受了这样的改变,其主要原因是医院骑士的作战人员在人数上与土耳其对手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因此更加倾向于追求装备的精良。由于骑士团自身生产能力有限,因此往往花重金从意大利、英格兰、德意志订购欧洲最精良的板甲。这些全金属板甲昂贵、沉重,但防护力更加强悍,在要塞防御战中,这样的板甲往往能够抵御土耳其人弓箭的射击,而早期十字军的锁链甲则会被长弓轻易击穿。这些板甲也为骑士团赢得马耳他大围攻的最后胜利打下了装备基础。
而在展厅中心线上的第一个展柜,展示了骑士团的敌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铠甲。两个人偶模型身着马耳他大围攻时期典型的土耳其武士配备,尖尖的伊斯兰风格头盔、胸前带圆形板甲的全身锁链甲、金属圆盾以及长长的土耳其弯刀。展柜背后陈列着大量当年缴获的土耳其弯刀、圆盾和火枪,这表明了在15世纪时土耳其军队已经大量装备并使用火枪这种新型武器,给医院骑士团传统链甲带来严重威胁,也促使其更新更好的全身板甲以抵御土耳其人的进攻。
从这套早期的士兵板甲中已经能够看到后世的盔甲发展方向。其中肩甲和腋甲合为一体,在心脏等重要部位又与胸甲重合,拥有双重防护。而在板甲的活动连接处采用了双铆钉的设计,使其更加可靠和坚固。另外,盔甲下部有下部裙甲,可以保护臀部和大腿部。不过,这套士兵盔甲的头盔部分是一个无面甲头盔,在西方术语中有专门的词语“Morion”来表示,也是现代钢盔的始祖。
这里还有一套1500年的意大利板甲,处于分解状态,透过玻璃橱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板甲的组成,包括头盔、颈甲、前胸甲、后胸甲、肩甲、腋甲、腕甲、大腿甲、小腿甲、膝甲等。其中这套板甲采用的头盔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意大利或基督教欧洲区域广泛使用的一种典型的骑士头盔,面甲可以向上翻起,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封闭头盔。这种头盔经常出现在波提切利(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等画家的画作中。在一侧的其他展柜中,还能看到许多头盔,有些将颈甲与头盔合为一体,这样既可以防止对方对颈部等重点部位的打击,还能够防止头盔因为重击而脱落。
在展厅当中有很多展柜,里面都是大量的头盔、铠甲、盾牌,包括大量长得像人脸一样的头盔,这些头盔都有一道或两道长长的帽檐,可能是在地中海地区强烈阳光下作战用于遮挡光线的吧。这些甲胄有些闪亮光洁,有些已经锈迹斑斑。由于骑士团从12世纪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当一位骑士去世或退伍时,他的全套装备往往要传给下一位骑士使用,而到马耳他后骑士团更是规定所有过世而退役的骑士的武器装备都必须上交到团部来保存,以便随时投入使用,这也是军械库存在的初衷。
在这些展柜中还有很多比较独特的铠甲,和制式铠甲相比有许多有趣的地方。这是马耳他大围攻时期的胸甲。在一套前胸甲上,其心脏部位竟然铸造了一个真实的心型构型突出于盔甲表面,犹如一块保护心脏的附加装甲。而这颗金属心脏上方铠甲表面又刻绘了两道纹路,犹如两条丝带悬吊着这枚心脏一般,似乎是一种宗教寄托,毕竟医院骑士团与其他骑士团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是一个基督教修士团体。而在这套胸甲的旁边是一套已经锈蚀很严重的胸甲,正面刻着一枚医院骑士团标志性的“马耳他八角十字架”。这种十字早在第一次时期就已经被医院骑士团采用,又称“阿马尔菲十字架”,据说起源于更早的意大利阿马尔菲航海共和国,而阿马尔菲城也是主教教廷,十字军们正是从意大利坐船到达中东的。这个八角十字其实是由4个V字合并而成,8个锐角代表着8种美德――忠诚、虔诚、诚实、勇敢、荣誉、无惧死亡、对穷人和病人伸出援手、尊敬教会。这个八角十字已经成为医院骑士团的标志,广泛应用到制服、旗帜、徽章上,成为“守卫信仰,拯救苦难”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心脏纹饰的盔甲还是八角十字的盔甲,都布满了弹坑,说明这型盔甲的主人是马耳他大围攻中英勇抗敌的骑士们,这些弹坑明显是被火枪打中但未击穿,证明了全身板甲在防御上的优势。
在另一侧的展柜中有很多最开始提到的“Morion”无面甲头盔,顶部有竖起的冠状突起,整个头盔雕刻着非常华丽的花纹。这种带冠头盔叫“Chapel-de-Fer”或者“Hron Hat”,头盔旁边摆放着两块与展示头盔相同重量的木块,能够让参观者举起以体会这些头盔的重量。其中代表无面甲花冠头盔的木块竟然重达10kg,而传统的带面罩的全封闭骑士头盔只有2.5kg。
战士的名字范文第3篇
一件为卷轴刺绣画(图1),画心直54厘米,横32厘米,画面绣有一只在花枝上腾飞的雄鹰,左上角绣有一行黑字“英雄伟志”,后面绣有画作作者的红色印章。画面的上方题有两行手写钢笔字:“贝恩士中校纪念中国陆军暂编第二十师师长安纯三赠”。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装裱处已有残破和虫蛀,但刺绣的画面依然线丝色彩鲜艳,历久如新。
另两件为锡制大盘,是原主人从中国云南带回来的一大堆锡制品中的较为精美的两件,大盘上分别绘刻有福禄寿老翁(图2)和麻姑献寿(图3)图案,口径均为33厘米。那堆锡制品中有大盘、小盘和杯子,还特别刻有“贝恩士中国一九四五”或者“贝恩士中校”的字样,看来是他特别订制的东西。锡制品的底部分别刻有产地和商号“个旧罗乾元号特造上锡器皿”“松茂昌记”等字样。
还有两件是两对绣有花鸟的红色缎面枕套。一对上面没有字,另一对上面绣有“白恩思教官纪念182D师长杨洪元赠1944.10”字样(图4)。
这些物件上都贴有注明原主人英文名字“Bain”的小纸条。据此可知,贝恩士和白恩思应该是同一个人,都是他英文名字的译音。从物件透露出的信息推断,“Bain”在抗战期间曾以中校的军衔在云南呆过,做过教官。
还有一对玉壶春状的青铜器(图6),通高16.8厘米,上面贴了个小纸条,写着贝恩士的英文名字“Bain”,那肯定也是贝恩士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古董。青铜器的外表有一层漆黑发光的所谓黑漆古,从它们的铜质、瓶颈兽头提耳和瓶身两圈图纹来看,应该是属于明清时期的东西,于是也买下。
回家后在网上查到那两个中国军队师长的资料:
“安纯三,少将。彝族,别号德纲,云南镇雄人。1942年任滇黔绥靖公署步兵第三旅旅长,1943年任第一集团军暂编二十师师长,1948年H月任云南省第一区(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4日在昭通起义。1950年参与组织叛乱,任滇黔边区游击总指挥,同年被俘后干关押中病逝。”
杨洪元,少将。云南大姚人。1943年任第一集团军一八二师师长。曾参加过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在对日作战中身先士卒,异常勇猛。1949年12月在昆明起义。
因为不知道“Bain”英文全名,他的资料就不那么好查。依据现有的贝恩士的名字,查飞虎队队员的名单,似乎没有他。那么他是否是后来的中美联合航空大队或者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军官,或者是跟随史迪威将军在云南指挥协调抗战的军官?抗战期间他在中国呆了多长时间,活动的范围多大以及成绩如何?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件记录了中美两国携手抗战的历史,还记录了中美两国军人的友谊。
战士的名字范文第4篇
最遭恨的字眼
如果问二战结束后的反思中,被清算最彻底的字眼是什么,你也许会想起法西斯、纳粹抑或是日本军国主义。其实,真正的答案是一个让不少人十分陌生的字眼――普鲁士。
普鲁士是欧洲历史地名,在这里建立的普鲁士王国曾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邦国。19世纪,普鲁士王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然而,现在如果拿一张欧洲地图,人们却找不到普鲁士这个地方,因为普鲁士在二战之后遭到了同盟国的彻底清算,拆得连毛都不剩一根了。
其实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这个字眼就已经上了同盟国的黑名单。1943年,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在德黑兰聚首,三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在战后,德国可以被允许存在,但作为德国一部分的普鲁士一定要在地图上被抹去。
二战结束后,说到做到的同盟国把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及其周边地区补偿给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的剩余部分被划给波兰。至于奥得河―尼斯河以西的普鲁士地区,则和其他德国领土一起被分为四块,分别由美、苏、英、法占领。在被占领的德国土地上,所有能让人联想起普鲁士的东西都被抹去,地名被更改、人民被驱逐、宫殿被拆毁。
仇恨往往来源于恐惧,为什么普鲁士这个字眼会被如此惧怕,甚至被定性为“万恶之源”呢?
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客观地说,普鲁士被视为公敌,遭到比纳粹主义更彻底的清算是有理由的。它不仅是军国主义的发源地,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建军史比建国史还要长的国家。
普鲁士在地理上位于东欧,这个一度被视作是德国代名词的邦国,本来并不属于德国。普鲁士最初形成的历史颇具传奇色彩。
公元1187年,圣城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萨拉丁攻克,欧洲人不得不组织第三次去收复圣地,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也在其统治的德国境内招募了一批贵族骑士参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与阿拉伯人的主力接触上,巴巴罗萨就在一次游泳时被呛死了。
主帅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死得这么窝囊,这批德国骑士们当然不好意思回国。就这么在中东地区飘着,一待就是几十年。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这帮人成立了一个名为“条顿骑士团”的军事修会,成员既被要求有着修士的虔诚与牺牲精神,又要继承骑士职业的砍人技术和军事素养。公元13世纪中叶,条顿骑士团受雇于波兰的康拉德公爵去征服位于其北部的普鲁士地区。战斗力爆表的条顿骑士团面对当地未开化的原住民,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任务。扫平普鲁士地区后,流浪许久的骑士们深感此地水草丰美,离德国老家又近,于是干脆在此地过起了日子。原本属于东欧的普鲁士地区就在条顿骑士团的影响下逐渐德意志化。条顿骑士团成了普鲁士最早的祖先。
条顿骑士团这段先有军后有国的开拓史,决定了普鲁士天生“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更为纳粹后来吹嘘“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找到了历史依据。的确,骑士的尚武精神、修士的严谨性格、流浪者对土地的渴望,在普鲁士的这片土地上三位一体。普鲁士从出生起,就是欧洲大地上的一个怪胎。
形神俱灭的阴魂
条顿骑士团的建国史,仅仅让它的邻居们多了一丝戒备。但到了1700年,世俗化的普鲁士王国正式建国时,欧洲各国才真正感到了它的可怕。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周边分布着瑞典、俄国、奥地利、法国等强邻,这种环境促使普鲁士以他国无法想象的疯狂优先发展军事。尤其是第二任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间,普军人数在二十多年间由原先的8万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的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
疯狂的军事投入,不断的对外征战,认定“强权就是公理”的政治理念,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普鲁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就是我们今天一再痛斥的“日本军国主义”所效仿的模本“普鲁士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
面对这样一个穷兵黩武、妄想并吞欧洲的国家,不是没有国家看出它将来必成祸害。邻国“抹杀普鲁士”的尝试其实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开始。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打败普鲁士后,曾一度要求其割让60%的领土。然而,拿破仑战争后重新崛起的普鲁士不仅更为强大,还统一了分裂已久的德国。
1871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战败被俘,普军进入巴黎,普王在凡尔赛宫被德国诸侯拥为德国皇帝,是为威廉一世。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挡住普鲁士进一步的扩张步伐了。
幸运的是,一战中德国的战败为邻国们再次提供了一个清算普鲁士的机会。在一战后对德国领土的分割中,普鲁士地区被削弱得最严重,1920年生效的《凡尔赛条约》又将西普鲁士省的一部分割让给波兰,东普鲁士的默麦尔割让给立陶宛。条约还特别规定要德国解散延续数百年的“普鲁士军官团”,该组织一直被认为是普鲁士精神的象征。
一战战胜国对于普鲁士的处置甚于拿破仑时代,但依然没有阻止这个阴魂在二战中重新复活。相反,战胜国对于普鲁士的有意压制,反而激发了德国人对这个名词的怀念。纳粹在崛起过程中就一再利用德国人的这一情结。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一职时,特意将宣誓就职地点选在了波茨坦的腓特烈二世陵寝旁,并鼓吹要把“普鲁士精神与新的运动”结为一体。被与纳粹绑在一起的普鲁士,因而在二战之后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彻底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战士的名字范文第5篇
流泪的《索尔弗利诺回忆》
1859年6月的意大利正在度过它艰难而又不平凡的日子,法国大帝拿破仑三世联合了意大利北部的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帝国进行了一场拉锯战,而他们双方的主战场就在撒丁王国的国土之上。双方在这场战争中死伤无数。
6月25日,一个来自瑞士日内瓦的英俊青年简•亨利•杜南途经撒丁北部的索尔弗利诺,他满怀热情地希望能够晋见正在指挥大战的拿破仑三世陛下,但他目光所及却看到了索尔弗利诺极其悲惨的战后情景。
刚刚结束的法奥之战把4万多死伤的士兵遗弃在这里,伤兵们都在烈日蒸晒下嚎叫,乌鸦与苍蝇围绕着腐烂的伤口。
由于是著名的银行家,杜南立即出资动员组织当地的居民(包括医生和护士)收容和安置4千多名伤兵,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护和治疗。
在结束了对陛下的晋见之后,杜南返回到日内瓦,他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士兵为了自己的祖国而英勇战斗,却在受伤之后被人们无情地抛弃?为什么那些在腐烂的伤口下的士兵竟会像被人丢下垃圾一样,任其被野兽啄噬?杜南决定写一本书,一本可以唤醒人们良知的书。
1862年11月《索尔弗利诺回忆录》自费出版,杜南把它分别送给他的朋友和欧洲各国的君主和政治家。在拿破仑三世看到这本书的一瞬间,他哭了。
杜南在书中提出两项重要建议:
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平时开展救护训练,战时支援军队医疗工作。
签订一份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及各国志愿者的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的国际公约。
英国的南丁格尔女士复信积极支持他的建议。日内瓦公共福利会的成员为杜南的著作所感动,决定把他的建议付诸实施。
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
在日内瓦公共福利会的大力支持之下,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五人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瑞士陆军总司令杜福尔将军担任主席,杜南担任秘书,其他三位成员是:莫瓦尼埃律师、阿匹亚医生、莫诺瓦医生。杜南到处奔走,行程3千多公里, 10月26日至29日,16个国家的36名代表在日内瓦雅典宫召开预备会议。
1867年,第一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巴黎举行,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杜南在会上首次提出1864年日内瓦公约所采纳的人道主义原则应扩大适用于战俘。
1871年,由于杜南一心投入到红十字会工作中去,无心顾及自己的事情,他所经营的银行终于倒闭,仅仅47岁时就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在此后的12年里,他简直成了流浪汉,经常睡在亭子间或公园里,贫病交加,受尽了折磨。
后来杜南先生被收容进一所老人院,在那里度过了八个春秋。直到1895年一位新闻记者路过那里,偶然听到关于杜南的传说,才把老人的情况刊登出来。这篇报道轰动了全世界。瑞士联邦委员会颁发特奖,雪片般的问候和赞颂的信件飞向杜南先生的小屋。梵蒂冈的教皇亲自写信给他,德国为他筹集了一大笔基金,许多红十字会邀请他做名誉主席,瑞士举国上下都在关心他,帮助他。1901年,挪威政府授予他首届诺贝尔和平奖,但杜南未能去领奖,因为那时债主还在向他逼债。1910年10月30日,杜南在海登医院逝世,终年82岁。
医学救援不只是在战争
从历史上看,虽然杜南不是第一个主张在战争中采取人道措施的人,然而,把在战争中采取人道措施的想法变成长远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却是杜南所倡导和推动起来的。杜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尊重人的生存权利,并认为应以不存歧视的态度向一切受苦的人提供救助。他首先成功地说服了索尔弗利诺的村民,照顾和对待受伤、垂死和已死去的敌方士兵象照顾己方的士兵一样,一视同仁;继而又把这个思想观念宣传给社会人士和政府官员,从而为广义的人道理想,亦即为红十字的基本观念奠下基石,又为后来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他所一手缔造的红十字组织虽然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只能尽量去援助那些可怜的伤病员,但他曾经说过:“医学救援不应该只是在战争,而应该尽力去援助一切可以援助的贫苦人群和濒临死亡边境的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