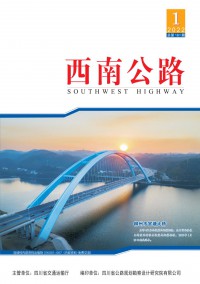巴南区教委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巴南区教委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1篇
互发短信三四年 一朝翻脸公堂见
1997年,32岁的古玉文被提拔为重庆市巴南区南湖中心小学校长。1998年9月,18岁的小雯调到小学下属幼儿园任教。在前两年,他们之间没有说上十句话,见面只是点点头而已。
2001年3月的一天,由于幼儿园内部有些矛盾,古玉文等校领导前去协调。事后,学校请幼儿园老师吃饭,青春靓丽的小雯给古玉文留下了良好印象。然而由于和幼儿园工作联系不多,古玉文此后渐渐淡忘了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孩。
5月中旬,古玉文突然收到小雯发来的短信,大意是向他问好,并请多关照。古玉文没有回复,不是端校长架子,而是他根本不会发短信――那年头互发短信还不多见。后来,小雯又给他发过两条短信。古玉文学会了发短信的方法,出于礼貌,他给小雯回复了一条。
之后,他们的短信往来越来越频繁,短信内容多为问候,偶尔也有几条插科打诨的段子。古玉文没料到,这些看来“很正常”的短信,让他在几年后麻烦不断。
去年7月中旬,小雯突然到区教委反映古玉文对其性骚扰。“报复!”这是古玉文得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据了解,小雯在区花溪镇开办了私人幼儿园,一直想调到那边去。因为调动没成功,她便怀疑是古玉文从中作梗。古玉文认为,自己在调动中起不了多大作用。经过调查,教委得出古玉文没有对小雯性骚扰,只是向其发过“和校长职务不相称的信息”的结论。
去年8月8日,小雯以人格尊严权纠纷为由,把古玉文推上被告席。小雯说,从2001年开始,古玉文就对其进行骚扰,既有言语和行为,也有短信。小雯提交了古玉文从去年5月3日至6月20日发来的19条短信。其中有“好想陪吃陪睡呀”、“我需要你”等内容。小雯称自己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并影响了夫妻感情,请求法院判令古玉文向其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1万元。就在审理期间,小雯丈夫已向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由于“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此前刚刚被纳入修改中的《妇女权益保护法》,这起被称为国内“性骚扰进入立法以来的第一案”,引起广泛关注。不管结果如何,古玉文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改变――去年8月,他被调到当地教办,削职为“民”。
80条信息洗清白 一审认定未骚扰
去年11月18日,区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此案。法庭上,双方都抛出了“撒手锏”。小雯的“撒手锏”是一份根据19条短信形成的专家意见书。这份有北大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杨大文、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等8名专家签名的意见书认为,综合短信内容看,古玉文的行为符合性骚扰的基本特征,是一起典型的性骚扰案。
古玉文则申请区法院向联通巴南分公司提取80余条短信息。它们是小雯在去年6月1日至6月21日期间发给他的,其中部分和小雯所说的19条“信息”点对点对应。比如古玉文当初发“我需要你”信息后,小雯很快就回“老兄呀,我哪次写申请不就形式上过一下而已,下期你还会在你办公室对面瞧见我的,哈哈哈”、“你的需要让我很满足”两条信息。在法院调取的80余条短信中,小雯称古玉文为“老兄”,古玉文则称小雯为“小蚊子”。 “性骚扰的显著特征是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信息、行为、环境等方式侵犯他人的人格权。”古玉文的律师聂静认为,综合互发的短信看,面对古玉文的“骚扰”,小雯非但没有不快和反感,反而比较愉悦,“因此不构成性骚扰”。小雯的人则辩称那80余条短信的来源不合法:“根据《电信条例》的规定,法院无权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
今年2月7日,巴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案。和上次开庭时记者云集的壮观场面相比,公开宣判显得冷清了许多。古玉文、小雯均有一些亲友前来旁听。由于上次休庭后双方“交过火”,法警特别提醒双方亲友分坐旁听席两边。
法院认为,小雯无证据证明古玉文以语言和行为骚扰过她;根据《民事诉讼法》等规定,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故而该院向联通公司调取的80余条短信合法;而根据双方往来的短信内容分析,小雯对古玉文发来的“”信息并未如其所言“严词拒绝”,反而将古玉文当作朋友对待,因此不能证明她反感,所以那19条“信息”不能作为认定古玉文构成性骚扰的依据。
法院同时认为,小雯提供的专家意见书仅依据原告单方陈述形成,不能作为断案依据。
当法院宣读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时,小雯表情十分复杂。“要上诉”,她说完后匆匆离去。据其人事后称,当初她也向法院申请调取过短信,然而不知何故没有成功,“那些没有调取到的短信比现有的19条信息下流得多。”据联通公司解释说,短信息最多能够存贮90天,“小雯申请法院调取时已过了90天,无法再查询。”
古玉文的妻子两次开庭都到现场,这个略显老实的女人说:“我相信丈夫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我的确给小雯发过和校长职务不相称的信息,但决不是性骚扰。”走出法庭,古玉文苦笑着总结教训,“那就是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
(本文男女主人公均为化名)
【律师看法】江西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武向春手机短信由于迅捷性及私密性日益受到使用者青睐,但它也同时给人们带来困扰,本案是典型的以短信侵犯妇女性权利为诉由的一起民事纠纷。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2篇
“玩老鹰抓小鸡了!”一位50多岁、身体消瘦的男子,不停地挥动着左手保护“小鸡”。
这个男子叫朱怀圣,他自幼残疾,右手腕以下空无,一直在川鄂村小当老师。从2009年开始,他用单手为留守儿童撑起了一个“家”。
“不能让悲剧再发生了”
2009年暑假的一天。
“娃儿啊,你啷个就这么走了呀……”朱怀圣隔壁家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原来邻居家一个留守儿童和几个孩子到堰塘里游泳,一个年仅十岁的男孩跳下水后,再也没有爬上岸来。孩子的父母闻讯从广东匆匆赶回,一路上数次晕厥。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朱怀圣的心。
“不能让悲剧再发生了!”他和妻子覃国碧商议,“我们把周围的留守儿童叫到自己家里来吧。”
善良的妻子答应了。
于是,他们腾出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屋,用平时吃饭用的高板凳当课桌,把两块木门板卸下来,拼在一起,制成了简易的乒乓球桌……
听说朱怀圣要办留守儿童班,村民们纷纷支持。
“以前在外打工就怕孩子出事,觉都睡不好,现在朱老师办了这个班,觉也能睡安稳了!”家长廖太明感慨地说。
家长陈良圣闻讯后,专门从广东寄来300元钱,朱怀圣如数送还:“我在家也做不了什么,顺便带几个娃娃,还收钱,岂不让人笑话?”
没几天时间,朱怀圣就招来十几个孩子,一个留守儿童班开学了。
“我更愿做孩子们的‘临时家长’”
在一间破落的土坯房里,朱怀圣正在给孩子们上书法课。
因右手残疾,朱怀圣自幼练习左手书法,无论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粉笔字,都写得苍劲有力,潇洒飘逸,令孩子们神往。
“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朱老师的书法课了。”川鄂村小教研组长朱安科说,“从朱老师身上,孩子们不仅学到一手好字,还有他身残志坚的精神。”
虽然没有课表,也没有固定的课程,但在朱怀圣的留守儿班童班里,每天除了辅导朗诵、作业外,还要练书法、唱歌、讲故事、打球、做游戏,孩子们过得非常充实。
“在班里,我更愿做孩子们的‘临时家长’,如果强调了师生关系,就会产生距离感,召不拢这些孩子。”朱怀圣说。
孩子们每天回家前,朱怀圣都一再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到家了打个电话报平安。
一些孩子因山路太远不能天天到“校”学习,朱怀圣决定每月1日、11日和21日上门辅导。
8月1日,是约定去看望马敬涛等孩子的日子。
一大早,朱怀圣就出发了,因手疾不能骑车,他只能步行,走到半路,突遇暴雨袭来,被淋得浑身湿透。为不让孩子失望,朱怀圣冒雨前行。
当他来到马敬涛家门口时,这个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正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等着他……
大爱无限
“师母,今天做的什么饭呀?”
刘红云摸着肚子调皮地问道,她的父母在浙江打工,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跟奶奶在家相依为命,平日里难得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有你最喜欢的洋芋饭!”尽管家里只有洋芋、玉米这些粗粮,但为了给正长身体的孩子们足够的营养,覃国碧总是变着花样给孩子们做各种饭菜。
差不多半数孩子的家都在十里之外,中午得在他们家吃一顿饭。由于“家庭人口”陡增,生活压力猛然加大。幸好朱怀圣的两个儿子都已参加工作,可以提供一些支持。
“只要父母乐意帮助留守儿童,我们花点钱也愿意。”两个儿子孝顺地说。
朱怀圣家的善举感动了乡亲们,他们不时送些猪肉、鸡蛋、蔬菜来改善孩子们的营养。在广东打工的堂兄朱怀照,也伸出援手:出资将自家连同朱怀圣的房子一同整修,现已硬化了院坝,添置了乒乓球桌、篮球架等。
大爱无限,朱怀圣的善举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2011年暑假期间,奉节县教委派出两批次专业人员前往朱怀圣家,协助他辅导孩子们,同时决定免费提供一批桌凳等用品。
兴隆镇党委书记赵崇刚、镇长刘光华等也先后带着现金、大米、食用油、棉被等前往朱怀圣家慰问,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有这么多人关心留守儿童,孩子们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朱怀圣用左手抹掉眼角的泪水,嘴角露出了微笑。
【幸福数据】
我市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截至2011年8月底,已有1068万人参保,其中357万名60岁以上老人按月领取不低于80元的养老金(国家最低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5元)。到2011年4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全市所有区县(比全国实际进度提前一年)。
截至2011年7月底,我市已累计投入68亿元,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2080所,解决了127万农村学生的寄宿问题。其中去年累计投入17.1亿元,建成寄宿制学校480所,较好地解决了47.7万在校学生的寄宿问题,其中包括20.7万留守儿童。“蛋奶工程”已在留守儿童中实现全覆盖,惠及全市中小学生300多万人次。已在30个区县31所实验学校推广“4+1”培养教育模式,从思想政治、人格品质、心理情感、行为养成、营养健康和安全等五个方面着手,帮助留守儿童消除情感缺失等问题。
我市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已有十年,取得一定成效。截至2011年9月底,全市在建工会签订集体合同6177份,覆盖企业11183家;签订工资集体合同3516家,覆盖企业6479家,企业职工工资在协商中实现了大幅增长。
【幸福语录】
薄爷爷,我们现在的生活真幸福!
――云阳县凤桥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康漪琳致信市委书记
以前每当有人提起留守儿童时,我就会低下头,忍不住伤心地想,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后来,谭新生伯伯与我结了对子,对我说,傻孩子,你爸爸妈妈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啊,你应该感到骄傲。从此,每次听到那四个字我就昂首挺胸。有了谭新生伯伯,我吃上了鸡蛋,喝上了牛奶,不再孤独了。
――石柱县冷水小学留守儿童曹盾
为了我的养老问题,四个儿子闹了矛盾。前年,修公路占了我的地,我只花一万余元就办理了养老保险。如今,每月能领到580元养老金,再也不用为养老流眼泪水了。
――万州区九池乡龙王村村民张大树
我填报志愿时,选的都是重庆的大学,说白了,就是瞄准两江新区那五大战略产业!
――高三毕业生伍华
虽然不缴费也可领钱,但现在有能力就多缴点,以后生活也更放心。
――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一人、南川区兴隆镇农民梁大生
这比养个亲儿子还好,每个月都能按时领钱,以前想都不敢想。
――开县铁桥镇农民王易成拿到养老金后说
我第一次来主城,这里(“感受新重庆”农村优秀留守儿童夏令营)吃得好,住得好,好耍惨了。
――石柱中学初二学生、留守儿童谭晰宇
孙儿的父母虽然外出打工,但镇党委、政府如此重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孩子并不缺少温暖。
――大渡口区八桥村留守儿童黄帅昕的婆婆唐治群
企业蒸蒸日上,通过工资协商,今年,我的基本月工资涨了600元,住房公积金也涨了130元。
――重庆建工三建后勤职工郭汉羽
短期内看似增加了“开销”,但却因此“收获”了职工劳动积极性、形成企业员工“共同体”意识。仅今年上半年,企业规模产值就已超过去年总和,达到24亿元。
――重庆建工三建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帆
农转城后,从去年8月开始,我的保险就转成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每个月给我缴纳的保费从按我工资的12%计算,变成按工资的20%计算。我太幸福了。
――巴南区接龙镇荷花村原村民李碧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康复;体育康复;城乡统筹
前言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谓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缩小城乡的区别,最后都变化为社区。而中国社区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手术后恢复或者残疾人的体育康复没有具体的实施,大多数人都是出院后自己康复,其实这是社区康复CBR(Community Based Rehabilitation)的一个重要步骤,本文就是要讨论现阶段如何将社区康复与我们常见的体育康复有机的结合起来,为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提供一定。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以重庆市主城区(渝中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和垫江县、奉节县、梁平县、彭水县的公共体育场所以及该地区从事体育锻炼的患者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1)资料法。搜集了国内有关社区体育研究的相关文献,查阅了近几年重庆市政府下发文件,重庆市体育局长会议、重庆市体育发展大会及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群众体育的相关文件,重庆市各区、县体委的相关资料。(2)问卷调查法。本文就体育康复在社区中的开展进行了调查分析,共同调查了社区28个,发放患者问卷1 630份,回收1 587份,回收率97%,其中有效问卷1 546份,有效率95%。(3)访谈法。走访了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渝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垫江县、梁平县体委领导及其体育公共场所锻炼群众共49人。(4)数理统计法。运用归纳、分析的方法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
二、社区体育康复的现状
1.国家政策的现状。2000年,民政部、卫生部等14个国家部委文件指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将残疾人社区康复作为重要工作内容。2002年8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民政部、财政部、公安部、教育部、中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康复工作的意见,其总体目标是:到2005年,在城市和中等以上发达地区的农村,有需求的残疾人70%得到康复服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达到50%。到2010年,在城市和中等以上发达地区的农村,有需求的残疾人普遍得到康复服务: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达到70%以上。到2015年,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重庆市社区体育康复现状。(1)领导重视不够。部分领导认为社区康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能把社区康复纳入社区总体规划之中,是社区康复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认识不够。人们对社区康复的理解混同于综合医院所开展的现代康复诊疗技术,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很难开展工作;残疾人本人及其家人对康复的认识与参与性也差,使得社区康复的推广受到影响。(2)专业人才匮乏:重庆市康复机构、专业康复人员都严重不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师又普遍缺乏康复知识,没有接受过正规康复知识系统培训,所以这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难得到持续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撑。(3)经费短缺:当前政府的资金投向主要是经济建设,对社区康复的投入还远远不足,有些地区在搞试点时,由国家拨给经费,试点结束,经费用完后,社区康复也随之陷入窘境;有些社区因经费困难,社区康复工作根本就难以起步。(4)康复设备资源不均:社区康复的设备主要是社区申请举办康复站,残联配备一定的设备,设备的多少、好坏,全根据当地的经济和重视程度来定,有需求的地方可能没钱配备,配备好的地方可能缺少技术支撑,往往造成设备的资源不均,甚至是空置浪费。 转贴于
三、发展对策
1.体育康复工作人员的培训。根据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与配套实施方案中的康复训练与社区康复服务“九五”实施方案中服务指导网络的精神。要发挥技术资源的中心作用,由有能力承担康复体育教学部门、人员担当培训工作。编写教材,配合音像材料对各省残疾人综合服务机构的人员进行培训。然后由各省级的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对省内县级人员培训,直至各社区的康复站人员。体育康复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知识,即康复医学知识和体育训练的知识。所以可以由负责康复训练的人员参加,学习体育方面的知识,也可以由负责体育工作的人员参加,学习康复方面的知识和康复体育的特点。国外有以康复和体育两方面的人员一起开展康复体育的形式。应该像重庆市全科医疗中心一样,定其举办康复培训班,针对各社区体育教师,聘请专业的康复学者进行培训。 以社区内体育教师为体育康复骨干开展社区体育康复。社区内体育教师是体育康复骨干开展社区体育康复的重要环节,因为现在毕业的体育教师就具有一定的体育康复知识,在校时系统学习过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传统康复体育训练手段等,只要稍加培训就可以进行体育康复的指导土作。还可以依托学校,利用学校的运动设施进行体育康复的指导。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不用再建立体育康复站,可以缓解我社区康复经费紧张的问题。社区内体育教师对社区残疾人及需要体育康复的患者情况熟悉。社区内体育教师担任基层社区体育康复员最有利的两个条件,一是社区内体育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地点都在社区的学校内,熟悉和了解病患与残疾人的体育康复需求。符合开展社区体育康复的需要,利用学校运动设施为其提供就近,就地的体育康复服务的要求;二是大部分年轻体育教师有正规高校教育背景,具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专业的体育运动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更多的体育康复知识。从而增加自己在社区内的作用,还可以适当收费,增加经济收入。我们从康复服务与运动保健中寻找出一个结合点和两个提供的工作方法,即利用我市社区服务功能网络建设的时机,将残疾人社区体育康复工作介入到社区内体育教师的日常工作之中去,为社区内体育教师提供系统而持续的康复技术专业培训。 体育院校开设体育康复专业的可行性。体育康复是根据疾病的特点采取各种体育锻炼方法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它通过体力活动对人体的影响,来治疗疾病和创伤,预防并发症,加速功能和劳动力的恢复。在医学科学中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是运动医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康复专业是国家教委根据社会发展对体育人才的需求趋势,于20世纪80年代末增设的新专业,是培养较系统掌握体育科学、人体科学、卫生保健和康复医学的专业。体育康复专业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体育、休闲体育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而“吃香”起来的热门专业,而且还是一门可以独立“经营运作”的专业。重庆地区的体育院校开设这门专业可以为重庆市的体育人才多元化培育及体育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
[1]徐杏玲.对大学生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的调查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0,(4).
沈永梅.社区康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广矿医学,2007,(4).
黄耀明.社区康复模式及本土化发展策略探讨[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1):20-24.
熊小兵.以乡村医生为康复技术骨干开展农村社区康复[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5,(2).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4篇
一、区域统筹的主体是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所谓区域统筹,就是按行政区域在一定范围内统一管理和指导中小学后勤工作。实行区域统筹一般要成立一个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隶属区县教委管辖,成立后可以设立以下部门:编外人员人事管理部、基本建设部、教育技术装备部、财会中心。仅仅设立几个部门还不能算实现区域统筹,真正实现区域统筹还要在具体工作上做到以服务学校、服务师生为目的统分结合,统得有力、分得有效。
二、区域统筹模式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区域统筹的主要目标是使学校后勤管理服务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和精细化,不断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为师生员工的生活服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素质教育服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形成师生满意的基础教育后勤服务体系。
区域统筹要协调好劳动和社会保障、建委、财政等相关部门,从而实现“四个统一”,即劳务统一管理、工程统一招标专业介入、物品统一采购、财务统一收支。
1.劳务统一管理
目前,很多学校都雇有临时工,如宿舍管理员、食堂工作人员、门卫、电工、维修工、水暖工、保洁员、司机和安全保卫等。在教育系统人员编制中没有完全考虑这些人员需求,而学校又需要这些人,只能雇用临时工来负责这些方面的工作;有的学校就把其中一些工作承包给社会上的专业公司,例如保安、绿化等,还有一些学校把学生食堂承包给社会上的一些公司(个人)经营。
雇用临时工和对外承包,都存在诸多弊端,一是临时工工资或承包企业的利润加重了学校的负担,甚至可能转嫁到学生身上。二是人员大多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应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了避免留下“后患”,一般的学校都会在十年期满之前解除与临时工的合同,学校这些工作又不能没有人做,只能再招人,从头开始培养训练。每一个临时工与学校单独订立合同,劳务关系都是个人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一旦工作中出现失误给学校造成了损失,个人又无力赔偿。
实行区域统筹后非教育系统编制劳务人员由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编外人员人事管理部统一管理,不同地区可以根据本地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实现。
经济发达地区可采取企业承包经营为主,直接管理为辅的形式。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通过对社会服务环境的考察,然后分类进行服务招标,保洁、食堂经营、校内超市经营、保安、绿化、校舍维修、设备维护等都是可以列入招标范围的服务项目。学校的财务工作不能委托社会上的公司来管理,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的财务中心可以全面负责,另外宿舍管理员、司机等工作,社会上没有专业公司从事这方面的业务,这类纯粹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由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直接招聘劳务人员。
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议实行直接管理为主,承包经营为辅的方式。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编外人员人事管理部统一考试招聘,统一签订合同,统一支付报酬。编外人员人事管理部搞清本系统所需各种劳务的情况,面向社会招聘有相应技能的工作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考试合格的由学校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统一签订雇用合同,派到学校承担相应的工作,这些人派到学校后具体工作由学校负责管理,工资由后勤服务中心发放。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这些人的考核、续聘、解聘,考核以用工单位的意见为主。
在学校非教育系统编制人员劳务用工改革过程中,仅靠教育系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才能成功。学校非教育系统编制人员劳务用工改革关系到财政方面,还关系到人事、劳动保障、法律,启动改革之前要将这些部门领导召集到一起统一思想,会商改革的具体方案,各部门群策群力,这项工作才能做好。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是保证这次改革成功的基础,研读相关法律,聘请专业法律专家参与,改革就有了足够的保障。
2.工程统一招标专业介入
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设立基本建设部,统一负责所属学校的新校舍建设和既有建筑维修,以及与建筑有关的水、暖、电、气、路等市政工程的管理。
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是集中大量“国家未来”的公共场所,在工程建设上要高标准严要求。学校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应该更具有安全性、教育性、思想性、艺术性,学校建筑的根本属性是教育性。学校的建设工程不应该单纯遵循国家规定的招标标准,而应该提高标准。
搞好学校的建设工程关键要提高招标标准: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普遍提高一个层次。既要规定造价在50万元以上的工程就必须实行招投标,不论是新建工程,还是维修改造工程;又要规定重点项目必须实行招投标,并应详细规定重点项目的内容;还要规定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根据不同建设规模、不同用途规定设计、施工、监理的不同资质等级,原则是比国家或地方规定的资质提高一级。其他投资额较小的维修工程也必须以招标的形式确定几家长期合同服务单位。承包小型维修工程的施工单位招标,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工程管理部拟好入选条件,由专家组负责评判确定,第二年再次评选时要把上一年在教育系统的业绩作为考核的重要参考。凡是在施工中出现安全事故、质量事故、治安问题、劳务纠纷的一律排除在第二年参选范围之外。如果辖区内学校不多,也可以由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雇用一批专业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学校的建设工程管理主要是学校管理和教委直接管理两种方式,或是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无论是教委还是学校,管理者也大多是教师,他们缺乏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是否照图施工,施工中所使用的材料是否合格,管理工程的教师根本不懂,由教师管理工程不仅不能发现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问题,还有可能出现一些由于不懂工程而提出一些违背建设工程法规的要求,造成建设工程在建设阶段就存在隐患。有监理的工程,监理如果负责任工程质量相对较高,监理如果不负责任或根本没有监理介入,那么学校工程质量就没有了保障。
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基本建设部应聘用一批专职和兼职的专业人士参与工程管理,这些专业人员应以建造师为主,专业要齐全,至少还要有一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有这样一支队伍监督施工,就能够克服本系统人员不专业、发现不了施工问题的弊端。还可以同一家监理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合同,费用包干,由这家监理公司负责监管所有工程,这主要针对维修工程而言,新建工程一般都需要进行监理招标。专业施工,专业监管,教育系统建设工程专业人员介入才能实现有效管理。但也不能只交给基建方面的专业人士来管理,因为建筑物用途不同,都会有一些自身的需要,学校的建筑物也是一样,而且不同学校,教学目标任务不同对建筑物也就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因此,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的基建工程部必须有懂教育教学的人参与管理。
3.物品统一采购
教育系统需要使用的物品很多,书、本、笔、粉笔、实验设备、教学仪器、化学药品、办公桌椅、计算机等,所谓的统一采购,指的是统一进行政府采购,但也不是学校所需所有物品都进行统一采购,本、笔、粉笔、化学药品等低值易耗品由学校根据需要自行采购,而像计算机、办公家具、学生课桌椅、印刷设备、摄影摄像器材一般都应通过政府采购。
根据法律规定,凡是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物品一律进行政府采购,教育系统有不少物品需要统一采购,但经常会发现一些学校违反政府采购规定,“擅自采购”某些物品,更多的是政府采购来的物品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现在的一些电子类教学仪器设备。
本该采购的不通过政府采购单位自行购买,有时是因为同类物品突然损坏,而这件物品又是教育教学必需的,通过政府采购需要40多天的时间,不能及时到位,会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因此会不时出现“擅自采购”的情况。
一些高水平的产品往往只有少数厂家能够生产,而政府采购时,如果将采购产品的技术参数确定为这类产品,有变相指定生产厂家的嫌疑,而不能把更高技术水准的参数加入进去,采购来的产品就不能满足教育教学使用的需要。以现在普遍采用的计算机为例,有些教学软件只能在硬件配置较高的计算机上运行,而采购时又不能把配置要求提到这个程度,就造成一些教学软件在学校成了摆设。
通过政府采购买来的教育教学设备,不能全面享受后期维护保养升级换代服务。采购与使用脱节,采购者不是使用者,这往往会造成供货商只重视采购环节,对售后服务环节不够重视,甚至直接省略售后服务环节,形成设备买来之后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的情况。
毫无疑问,教育系统购买物品应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实施政府采购。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设立教育技术装备部负责教育教学设备、办公家具等学校大宗物品的采购,应该通过与政府采购办的沟通,建立一套机制,避免出现学校擅自采购、采购的设备不能满足需要、采购来的物品缺乏售后服务。
第一种:定点供货商机制。定点供货商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确定,每年采购一次,规定只负责供应小数量物品,需要物品数量超过规定,必须履行政府采购程序,单独立项进行采购,这样就解决了突然损坏、无法维修,而教育教学又必需的设备购买问题。
第二种:自行采购机制。在采购那些技术要求高的产品时,应通过沟通,与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达成一致,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在了解所采购物品的特殊性后,一般委托项目单位自行采购。
第三种:使用者直接参与机制。让学校参与政府采购过程,完成采购后举办供货商与使用者见面会,见面会上将政府采购相关档案交给学校一份复印件,让学校对所提供的产品、厂家有一定了解,对政府采购合同有所了解,与供货商见面,商定供货时间、交接人、联系方式,并让学校方面参加验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招标文件中对售后服务有所规定,在合同中约定好保修、回访、维修等一系列问题。
学校后勤服务中心教育技术部必须认真研究政府采购的有关政策法规,熟悉政策法规才能很好地利用政府采购平台为学校购置质优价廉的各种物品。在了解政策法规的同时,还应对教育教学需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进行政府采购时才能提出恰当的指标体系,这样才能采购到教育教学真正需要的装备。
4.财务统一收支
现在各地学校的财务管理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但大多是以区县财政拨款、各校自主支付为主方式的各种变形。政府投资建设,政府管理运行,这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证广大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平等享受受教育权利。学校的开办资金多由财政保证也是由国家性质、学校性质决定的。国家非常重视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财政资金越来越充裕,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是逐年增加,同时,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配套的管理措施接连出台,预决算制度、零余额账户、国库直接支付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相继出台。学校处在旧的财务体制与新的财务体制交替时期。人员工资由学校发放改为财政直接划转到教师个人账户,基本建设工程款改学校支付为国库直接支付,择校费、捐资助学款由学校收取使用改为财政收取,教师培训、学生活动、维修改造资金改按定额拨款为按项目拨款,一系列变革的出发点都是让教育系统资金使用更加合理、更加规范。
由于旧的财政体制和新财政体制正处在交替期,教育系统的财务人员多是由教师转行从事财务工作,财政体制的交替使学校的管理者和财务人员很不适应。第一,预算执行过于僵化,学校预算经常不到位,有事无钱,或是有钱无事的事情经常发生。第二,项目带资金,没有项目就没有资金,有些学校千方百计拼凑项目,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第三,实行国库直接支付,增加了建设项目的审批手续,使建设项目实施起来更加困难。
教育系统内部财务管理模式也必须随着政府对财政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建立统一的财务中心是教育系统适应财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明智选择。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设立财务中心,财务中心人员组成必须是业务能力强、对财政资金使用规则清楚的人,但是财务中心不能涉及学校的日常开支,学校的日常开支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管理,学校仍保留现金会计,主管会计的工作全部收到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成立财务中心后实行资金统一收支。财务中心负责整个行政区域内教育系统的所有资金的收支,包括全系统的预算、决算;全系统所有建设项目、所有采购项目的立项、资金申请、资金支付。
实行财务统一收支,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关于预算的编制、项目的确定、项目的执行、项目结算都要有严格细致的规定,所有人、所有事必须照章办事。
实行财务统一收支,很容易造成财权过度集中,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约束过度集中的权利,避免权力的滥用。实行财务统一收支,财权集中,由少数人进行管理,在编制年度财政预算时必须保证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避免不了解情况的胡乱决策。
三、区域统筹模式的发展
1.实现区域统筹应树立的观念
实现“四个统一”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学校后勤管理区域统筹,同时必须具备三种观念,区域统筹模式才能得到更好的应用和发展。
(1)要树立法制观念,实行区域统筹是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作出的选择,国家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法制化,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同样需要遵守法律,依法照章办事。国家有各种法律规范雇佣关系,也有相关法律管理建筑施工、政府采购,对财政资金的管理法规更是不胜枚举,各省市还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实行区域统筹应该以遵守这些法律法规为前提。实行区域统筹不是为了规避这些法律法规,而是为了更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2)要树立标准化观念,实行区域统筹,学校的后勤管理有了政府的影子,体现了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学校后勤工作相当繁杂,要想管好,少出差错,进而不出差错,必须对各项后勤工作提出标准,食堂卫生标准、食堂工作人员操作规范、学校环境卫生标准、学校绿化管理标准、学校财务工作操作规范等,只有把这些标准制定出来区域统筹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推行。
(3)要树立精细化观念,实行区域统筹,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既是一个管理部门,又是具体工作的操作实体,既要管理面上的工作,又要管理具体的建设工程、设备的采购。学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必须精细,要精细到人员培训内容的选择、人员录用考核、人员聘用合同条款、设备采购的技术指标和财务支出的每一个步骤,从而减少其中的漏洞。
区域统筹是加强学校后勤管理的需要,是国家政策法律在教育系统的延伸,是当代中国教育系统后勤管理的理性选择。
2.完善区域统筹模式需借鉴社会化改革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
中国高等教育社会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九章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指出:“建立新型中小学后勤服务保障体系,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标引进优质企业从事中小学生活服务、校产物业等经营管理,增强统筹力度,加强资源整合,建立集团式、集群式、集约式中小学大后勤服务格局。”广东省进行了构建基础教育后勤服务保障体系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深圳政府花钱买服务的模式,其他省市也进行了学校后勤工作社会化的实验研究。例如重庆市渝北区食堂社会化改革模式,巴南区物流统一配送管理模式;上海市、湖北省高教和普教相结合为中小学服务模式。许多地区学校还创造了内部承包模式、委托管理模式。区域统筹模式的完善需要借鉴这些社会化改革的理论、思想和经验,需要在学校后勤改革的实践中证明并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