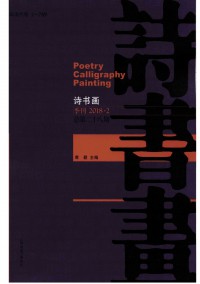颓废非主流

颓废非主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颓废 象征主义 中国新诗 接受 变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2-0152-07
颓废原是西方象征主义的审美范畴。在西方文学史上,较先使用颓废(d$cadent)这个词的是法国批评家德西雷・尼扎尔,1834年他以此批评浪漫派过分注重细节和雕琢而破坏了整体。后来象征主义颓废文学接受这个批评,并将其“雕琢”内涵发展为“精致”。19世纪80年代,法国出现颓废主义文学。一些诗人创办《颓废》(D6cadent)杂志。在巴黎出现的“颓废派’’事实上是象征派的前身,兰波、魏尔伦参与其中。当时Decadent杂志驰名文坛,声誉鹊起,活跃于巴黎拉丁区的青年诗人无不自豪地宣称自己是Decadent,“颓废派”引领时代潮流,摇身变为一个毫无贬义的先锋词汇。戈蒂埃1868年为《恶之花》所写的再版序言里,第一次将这个词赋予褒义,激赏、赞许颓废文体。颓废文学构成对经典或传统文学的修正和挑战,否认理性的价值,主张个性的极端自由,崇尚感官本能的放纵,追求艺术上的精致,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表现。
20世纪20年代,颓废风伴随现代文艺新来中国,对中国新诗创作和理论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中国现代诗学立足于自己的审美语境,大多将颓废阐释为堕落、怪诞,主要从伦理道德和社会现实层面来接受,而不是诉诸先锋性、唯美性。作为一个中国现代诗学概念,颓废逐渐剥离原本涵义而呈现一种本土化的态势。自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Ⅲ始,不少学者关注颓废问题,但很少从发生学角度将这个概念内涵进行历史还原。本文从历史语境去探讨这个诗学范畴的发生和演变。
一、颓废论的接受
(一)最初的译介
中国对decadent的译介,最早见于1920年3月《少年中国》l卷9期刊载的吴弱男女士的《近代法比六大诗家》:“巴黎有一大诗人名Stephane Mallarme是Decadent派。”作者似乎有所犹豫,未将Decadent翻译成中文。田汉也有所回避,他在《少年中国》发表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百年祭》没有意译成“颓废”,而是煞费苦心,采取音泽方法,译为“醴卡姚”:“总而言之为欲研究‘近代主义’Modernisme的,尤以研究近代‘醴卡婉象征主义’Decadent Symbolisme的所不可不知。”这里,“近代主义”和“象征主义”分别是Modernisme和svmbolisme的意译,唯独“醴卡蚍”是Deadent的音译。1921年1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用中文的“颓废”将Decadent译出。这是较早的直译。但周作人赶紧在后文解释。说波德莱尔“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这真是欲盖弥彰,“貌似的颓废”,一语道破对“真正的颓废”的警惕。
中国诗人、批评家对颓废派与象征主义的关系,以及象征主义的颓废倾向是有所了解的,但在对“颓废”意义的阐释上,出现有意味的偏差和误读。宗白华较早将颓废运用于新诗批评。1920年7月,刚到德国留学的宗白华,有感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有人撰文提倡“憎厌之歌”、“悲怨之曲”,直率发表自己意见:“我觉得中国民族现代所需要的是‘复兴’而不是‘颓废’,是‘建设’不是‘悲观’”。将“颓废”等同于“悲观”。宗白华洞悉国内颓废论者受到西方诗学影响。深刻指出:“法国颓废派的文学不足以振兴法兰西的民气,而罗曼罗兰的乐观文学于将来法国,将来欧洲必定有好影响。”李金发用“颓废派”来称呼波德莱尔。而不是像当时国内很多论者那样称波德莱尔为“恶魔派”诗人。李金发是深切了解波德莱尔及颓废的含义的。而国内多数译介者,称波德莱尔为“恶魔”诗人,不称“颓废”诗人,在他们看来,后者有某种程度的道德背叛和贬损。因为在中国文化和语境里,“颓废”绝对不是个褒义词,它常跟“堕落”、“异端”连在一起。对这个词的翻译可以看出接受者的微妙心态和文化价值取向。
(二)否定和质疑
1922年,梅光迪在《学衡》撰文,批评新文学运动倡导者非创造家乃模仿家,指责新文学运动“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梅光迪将Deeadents称为“堕落派”(包括美国意象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他显然鄙视、贬斥Decadents。梅光迪认为白话诗“只为诗之一种”,并且“非诗之正规,此等诗人断不能为上乘”。他说:“今之Vers Liber有康布利基女诗人Amy Lowell(即艾米罗威尔,意象派主将,笔者注)为之雄,其源肇于法,亦Decadents之一种。一般浅识之报章,多录其诗,为之揄扬。然其诗非诗也。”学衡派从否定的立场,贬斥堕落派,锋芒逼向白话新诗。这是一种一箭双雕、一鞭抽二羊的技法:暴露白话诗麒麟下的马脚,撩起新文学运动倡导者“数典忘祖”、“拾洋人余唾”这条不光彩的尾巴以现其丑,是学衡派论战的刹手锏。其实,1916年梅光迪和胡适在美国讨论新诗问题,表示对“新潮流”,怀疑时,就提及象征主义和颓废派,称“法之Verlaine,Bardelaire为颓废派”,并认为美国的新诗运动和意象主义“其源肇于法”。学衡派对颓废诗学显然是否定的,并且批评的锋芒指向“五四”白话新诗。
对颓废的误读和质疑多来自现实主义文艺观的论者。“二战”滞留欧洲、1947年归国的罗大刚,热心介绍法国左翼文学。20世纪30年代,罗大刚曾以“陈琴”、“罗莫辰”等笔名在《现代》、《新诗》上发表很多不同凡俗的诗歌。他深谙象征主义三昧,但在里昂和巴黎研习现代文艺时,因“二战”炮火洗礼而转向现实主义文学。罗大刚《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一文将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对比,高扬前者的雄奇奔放而质疑后者的颓废:“如果说罗漫主义文学是金鸣玉振的雄健交响乐,象征派诗人的歌吹,只仿佛是房中乐。波特莱,韦尔兰,玛拉美都直接间接地歌颂颓废的美,作秋虫的……勒尼叶(Herry de Regnier)那套‘我吹一支细细芦管/足可以使森林吟哦’的纤巧的玩意,也不能使所谓后期象征主义的苍白的面目,增加一丝泼辣的生气。”作为资深的诗人和理论家,罗大刚对象征主义的颓废美持审慎态度。
谢冰莹对颓废持明显的否定态度。1932年,她与顾凤城、何景文共同编写的《新文学辞典》对“颓废派”、“象征主义”以及二者的关系都有解释和论述。《新文学辞典》认为:“颓废派是堕落人们的意思。最初是说罗马文明烂熟的末期的堕落时代人们。但现代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国文学家的一派,这派的特色是:一注重情调的神经艺术;二极端地离开自然,注重人工的;三,神秘的;四探求异常、惊异等。”《新文学辞典》将“象征主义”定义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典型,是小布尔乔亚的不正确的颓废的倾向。”而“颓废”一词在谢冰莹等看来,就等于“没落”,“没落是不能随着时代而前进,落在时代的后面。如现在颓废派的文学,即是一种没落的文学”。
阶级革命论者也对现代诗学的颓废提出质疑和批评。革命文学阵营警惕颓废的人生态度和“唯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认为他们与民众斗争和审美理想脱节。正如瞿秋白所疾呼的:“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
茅盾1920年2月在《小说月报》11卷2号发表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明确主张要提倡象征主义,但到了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1923年态度开始转变,他的《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总结“最近两三月来常常听得的论调”是:“反对‘吟风弄月’的恶习,反对‘醉罢、美呀’的所谓唯美的义学,反对颓废的,浪漫的倾向的文学。”茅盾认为这三类文学“是物腐虫生的自然趋势”。1925年5月,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则对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直接的全然否定。
一些接受过唯美颓废主义影响的作家,在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语境下,都进行了自我调整与清算。譬如郭沫若早期的作品《王昭君》、《聂篓》,都有唯美颓废作家王尔德的《莎乐美》影响的痕迹,但1925年他就预感:“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像这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莫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郭沫若毅然转向并投身革命文学大潮。田汉在“五四’’时期的诗歌和戏剧创作,譬如《梵峨嶙与蔷薇》等作品,都有唯美颓废主义倾向,他还撰写长文《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介绍象征主义诗学,又翻译王尔德的《莎乐美》,并组织南国剧社公演。1930年,他从象征主义的唯美颓废残梦中走出,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清算“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底感伤的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了”的“过去的南国”倾向。
1930年鲁迅剖析“急进革命”论时,深刻地阐述了“颓废者”的享乐、刺激与革命的关系,认为颓废者“因为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便流落到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剌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是那颓废者的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鲁迅特别举引波德莱尔为例,说“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1931年,鲁迅批评用“美名”来掩饰自身“溃败”的文艺家时,提及“颓废”,并以之解释所谓的“放达”。鲁迅用极具反讽意味的语语分析说:“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日高逸,日放达(用新式的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
1930年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最后一章讨论“世纪末”文艺思潮。他判定:世纪末的思想完全是一种黑暗、绝望的思想,并将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划为世纪末思潮的代表。徐懋庸分析说,世纪末是法文fin de siecle的译语,从创作手法到表现题材,法国颓废派的特征为:反科学的倾向,自己崇拜的倾向,偏重技巧的倾向,无感觉的倾向,偏重“恶”的倾向。这是不值得效仿,应该予以否定的。
1946年末,上海《文汇报》发起一场关于波德莱尔诗歌的论争,也涉及到颓废问题。九叶派诗人陈敬容翻译了不少波德莱尔的诗歌,激赏波德莱尔――从他的诗歌到颓废直至爱猫这样的嗜好等。认为“波德莱尔的诗,令人有一种不自禁的生命的沉湎”,里面有“无比的‘真’,有人认为波德莱尔颓废,那只是他们底臆测之词,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底里”。林焕平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率先对陈敬容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认为闻一多、卞之琳和艾青等重要而又有才能的诗人,好不容易从波德莱尔的倾向中跳出来,而陈敬容又要人们跳回去,这在“此时此地,诗多么不合时宜!”李白凤指责陈敬容企图抬举象征派在中国“低垂了八年的头”,这是“一种不健康而且有害的倾向”。覃子豪从阶级论出发,认为波德莱尔不过是“一群没落的小布尔乔亚的代表”,他“歇斯特里”的病态情绪和“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表达方式不值得赞扬。陈敬容赞美波德莱尔的“颓废”,在阶级论者那里,成为了需要否定的“19世纪末没落的小布尔乔亚一个共通的产物”。
(三)理解与评述
新文学阵营在对待颓废派问题上虽然不像学衡派那样完全否定和贬斥,但是在行为和观念上出现偏差和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刘西渭对“颓废”诗学含义有客观、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他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一文中谈到“徐志摩领袖的《诗刊》运动”“用外国的诗歌作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时说:“在另一意义上,这却形成颓废(不是道德上)的趋势,因为实际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都藏着颓废的因子。”刘西渭括号里的解释,用心良苦,表明他对这个词的理解至少是中性意义的,但也说明当时存在“道德”意义的理解――多数看法如此。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对现代诗学的“颓废”含有艺术之“精致”这层意义有明确的认识的,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刘西渭殊为难得。
另一个是朱自清。他认识到象征派的“精细”问题,说:“李金发先生等的象征诗兴起了。他们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他们要发挥词的暗示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文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个词去。他们是在向精细的地方发展。”而张若茗的《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蓝苞》,专门探讨了象征派与颓废派的关系,客观论析了象征主义颓废审美特征和晦涩(暗晦)理论,显示了认识的全面、客观和理性的成熟,这是少有的。但这仅是纯学理意义的译介,不是对中国新诗审美实践的观照。
当时大多数论者因袭中国传统看法,将颓废阐释为堕落。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民族审美模式对接受者理解域外文艺思潮产生牵制和误读。章克标、方光焘《文学入门》将Decadant泽为“颓加荡”,并解释为堕落:“世人叫他们颓加荡(Decadant),意思即是堕落之人。其中也有人厌恶这名词,于是同志中的约翰莫累亚斯Joan Moreas就提议改用Symbolist的名词。”实际上,象征主义的“颓废”并不是“堕落”的意思,也没有人对“颓废”这个名称厌恶或感到不好意思。
汤鹤逸《新浪漫主义文学之勃兴》论述了“颓废派”一词的来历:颓废派Decadent原为堕落人的意思。法国史书称,罗马文明已经熟烂而倾向衰灭为堕落时代,为此时代命名的是罗马人Decadent,因此以Decadent为颓废派。汤鹤逸认为“Decadent,若从道德上说来,诚为未合”,正是因为道德上为人所诟,有人不满意于颓废派的名称,仍改叫象征派。“Decadent的文艺,原可说是象征主义的文艺”,“颓废派和象征派,两派实质是相同的”。汤鹤逸引用德国颓废派先驱赫尔曼・泊尔(Hermann Bahr,1863-1934)的话,将象征派或颓废派的艺术特色概括为;1、颓废派艺术乃重情调的神经艺术,非重思想或感情的艺术;2、颓废派的艺术始终以侧重“人工”远避“自然”为主旨;3、颓废派的艺术渴慕神秘,务努力以求表现潜于事象里面的神秘;4、颓废派的艺术乃深恶一切平凡腐臭者,竭力以求异常者与珍奇者。“总之,所谓颓废派的艺术,实不外为神经过敏的近代人贪求刺激所生的艺术。”
茅盾《西洋文学通论》也引述过赫尔曼・泊尔(茅盾译为巴尔)的这段话,认为颓废派文学具有上述四个特征。《西洋文学通论》第九章“自然主义之后”,讲的就是自然主义文学之后的颓废派文学的各种主义。茅盾认为,社会迅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机械的动作、平凡的现实使人产生厌倦,要求刺激和强烈的震动,要求超现实的神秘的东西。一方面幻慕灵的神秘,一方面追求强烈的肉的刺激,这种世纪末思潮产生了颓废派文学。茅盾从神秘和肉感两方面揭示颓废文学的特质,这种观念实际上影响到他自己的创作。茅盾此期的创作力图以颓废――肉体的感官的对世界的追求,对抗腐败与衰退的革命性力量,他骨子里是一个具有一定颓废色彩的作家。
最有意思的是徐嘉瑞的长文《颓废派之文人李白》,将李白的喝酒与法国颓废派“聚集在巴黎咖啡店痛饮彻夜”相提并论,说李白的生活和颓废派“很类似”,他追求官能刺激,是“堕落”。李白成为颓废的浪漫诗人。1936年,朱右白《中国诗的新途径》提出中国诗歌的发展路径是“复兴唐诗”。他运用现代诗学概念“颓废”阐述唐诗,譬如认为唐代诗人的思想不出儒派(杜甫)、仙侠派(李白)、山林派(王维、孟浩然)、颓废派(杜牧)等四派,学李白不能得其真正思想便流入颓废派,颓废派“风流放诞,毫无拘束”,可谓“最不长进”。
二、创作上的呼应
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标举“为艺术而艺术”大旗的创造社曾经用力译介过唯美颓废思潮。1923年9月,郁达夫在《创造周报》发表长文《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介绍了颓废派核心刊物《黄面志》和英国颓废派诗人、艺术家比尔利兹(Aubrey beardsley)、道生(Ernest dowson)和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等。郁达夫称比尔利兹是“天才画家”、“空前绝后”,他“使《黄面志》的身价一时高贵”。郁达夫与病态的、沉溺肉体甚至有些堕落的比尔利兹等颓废派艺术家在精神上有相似之处。无疑,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颓废文学的始作俑者,很大程度上以《黄面志》及比尔利兹的作品为灵感之源。但是,当时最具颓废色彩的郁达夫,一旦被批评者如茅盾指名为“狄卡丹”(decadant),就有创造社同人主动出来为他开脱、辩护,譬如郭沫若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郑伯奇说“达夫是虚颓废派”。显然,“颓废”是不好的贬义词语。大家都躲闪,生怕沾染这不光彩的恶名。
但30年代前后有一批另类文艺青年自甘“堕落”,打出“颓加荡”旗帜,聚集在唯美颓废倾向的群体“绿社”、“幻社”等周围,以《狮吼》、《声色画报》、《金屋月刊》为园地,以金屋书店为核心,追求官能刺激,营造肉和色的艺术。他们宣称要打倒浅薄、顽固和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艺术,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他们是唯美主义者,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倾心并接近颓废派,主要代表有邵洵美、章克标、滕固、张水洪、滕刚等。
滕刚发表在《金屋》1卷3期上的《的狎曲》、《残句》、《朱唇开处》等诗充满肉的喧嚣。邵洵美1928年由金屋月刊社出版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从题名到内容都受到波德莱尔、魏尔伦的影响,象征主义世纪末的痛苦、对现世的不满这些颓废特质在邵洵美那里转化为人间及时行乐,诗美的追求下放为感官刺激。邵诗多写女性的香艳,红唇、皓齿、丰乳、蛇腰,这些妩媚意象洋溢着浓浓的粉脂气。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邵洵美的《火与肉》是一部唯美一象征主义倾向的批评论集,《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在论述万蕾(魏尔伦)诗学时极尽赞美之能事,徐志摩说邵洵美“是一百分的凡尔仑”。他们的创作和诗学主张有点类似参加颓废派时期的魏尔伦和兰波。
三、中西差异
颓废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现代颓废诗学具有这样的特点:反对世俗,批判荣禄,追新逐奇,崇尚自然,爱好怪诞,注重感官刺激和色情味道。这些与西方象征主义颓废派诗学的主张是近似的。但是,中国颓废诗学与西方象征主义相比,从诗学本质观到表现形态,都存在差异。
首先,与西方颓废主义相比,中国颓废诗学缺乏对现代性的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价值的显现,而审美现代性则是对这种理性束缚的质疑和批判,颓废主义正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中国颓废诗学并未对资本主义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意义加以区分,而是看作互相包含的现代性。中国颓废诗学也有某种程度的批判意识,但锋芒指向的是阻碍现代性的东西而不是现代性本身,譬如封建道德、社会现实等。有的论者注意到颓废诗学的非理性特征,譬如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但认为这种“反科学的倾向”是不值得效仿的,应该予以否定。
颓废非主流范文第2篇
自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来,海外汉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蔚为风潮”,而且能人辈出。王德威曾指出:“在中坚一辈的学者中,李欧梵教授的成就,堪称最受瞩目。” ①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和王德威一样,重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力图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推向晚清;另一方面,他从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美学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对立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视野中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特别是“城市-颓废”文学、文化问题的提出,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以“五四”启蒙为分水岭、建立在“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新/旧、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的常识框架,为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论线索。《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李欧梵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真的恶声”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印刷业和中国的现代性以及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问题;第二辑“浪漫的与颓废的”共六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所谓“五四浪漫个人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颓废”;第三辑则收入了两篇写作于70年代初的文章,这是他应《剑桥中国史》之邀而作的两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历程的长文。第二辑是全书的核心,用王德威的话来说是“最见其个人情性的发挥” ②。其中,《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和《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两篇文章,是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内部诸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
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以下简称《漫谈》)一文中,李欧梵首先指出:“从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谈颓废,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即使从新文化运动所用的词汇来看,一切都是一个‘新’字,气象一新,许多常用的意象指涉的是青春、萌芽、希望。” ③而“颓废”(decadence)却是一个有关于时间和历史逐渐走向衰落的概念。卡林内斯库指出,颓废概念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宗教主题——“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 ④。在基督教文化传统里,关于时间、历史的颓废和进步的意识其实构成了一种辩证对立的复杂关系,因为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信仰,使“千年至福的信念”和“末日的阴沉期望”共存于中世纪基督徒的内心意识中。而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信念的确立,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历史是无限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即所谓的“进步神话”,但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同样伴生出一种新的“颓废”观念。“高度技术的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为融洽。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觉来经验进步的后果。” ⑤这种“颓废”感从19世纪中后期法国象征派诗歌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现代性”自身的对立面——“美学现代性”。“这种美学现代性尽管有着种种含混之处,却从根本上对立于另一种本质上属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以及它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适’等等的许诺” ⑥。在这一观念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问题,李欧梵认为,虽然“五四”传统致力于求“新”,但是作为与始发于西方的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现代文学,“颓废”却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关键问题——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 ⑦
那么,“颓废”究竟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在所谓的“颓废现代性”和“进步现代性”相对照的问题框架下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国现代文学将呈现出怎样的美学和文化形态?在《漫谈》一文中,李欧梵从时间观念入手,指出“五四”时期《新青年》对“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进步的观念”等启蒙精神的呼唤,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时间观念的冲击,即“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所以,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种线性前进的时间想象导致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形态:“历史不再是往事之鉴,而是前进的历程,具有极度的发展(development)和进步(progress)意义。” ⑧因此,“五四”所继承的“现代性”其实是卡氏意义上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所谓的“进步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 ⑨由于“颓废”从未作为“现代性”的另一面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追求视野,因此,在一切都求新的“五四”时代,“颓废”作为一个关于堕落或衰败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不道德的名词”。
李欧梵独重“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因为“颓废”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美学立场,“它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谛” ⑩。因此,和当年夏志清立足于“纯文学”框架勾画出一条所谓非政治化的现代文学谱系一样,李欧梵则基于“颓废美学”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构建出一条“颓废”文学史线索。在《追求》第二辑的后三篇文章里,李欧梵追寻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谱系,它上接中国晚明文学、《红楼梦》,下接新感觉派、叶灵凤、张爱玲,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鲁迅和郁达夫。虽然中国的“颓废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的作品与西方的“颓废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然而李欧梵却进一步指出,这些城市颓废作家“在模仿英法颓废之余,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其资源仍来自‘五四’新文学商业化以后的时髦和摩登”。在这张颓废系列图中,他认为只有张爱玲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位女作家作品中的“荒凉感”,包含着对“时间和历史的反思”,是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和破坏的反应”。(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某些作品已经“跨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门槛”,但是鲁迅的“那种彷徨的心灵并没有完全迷失在虚无主义之中”,最终还是“退回”到中国现实中,加入了“他的同时代人的那种‘现代化进程’”。)
颓废非主流范文第3篇
在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里,被称为90后潮人的是——非主流!
非主流,他们是真正的潮流吗?或许他们只是愚昧的、思想的变态。而偏偏这些所谓的非主流却成了无数青少年的崇拜与模仿的对象。
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不少吧?现在的男生们越来越偏向女性化了,他们的头发比某些女孩的还要长,头发古灵精怪的,五颜六色,刘海遮住了半边脸,头顶的头发却像十天没梳过头一样乱糟糟的,头的背后更可怕,不是斜这边就是斜去那边的!在穿着上,他们也穿的很“非主流”,他们明明穿上一件宽大的T??匆?钌弦惶跽?诺目阕樱?挂?渖弦凰???ldquo;显眼”的女性长靴,手里还拿着一个手袋,娇娇小小地走在街上。大家说,这是男人吗?我想他们不并是中性的吧!
但这些打扮奇怪的男孩却觉得自己成为了今天的非主流,当他们走在街上时,回头率是百分之百的,他们却以为自己一身的打扮很潮,或许对于他们的“同类”来说吧,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颓废、恶心的。
提到我们的某些女生,心里面就往里头疼呀!他们使我们感到可悲、羞耻。
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的女生长期沉迷于网络虚伪的世界里,也投入到了模仿非主流的风波里了。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姐吸的是烟,抽的是寂寞”,多少无知的女生看到后就学人家抽烟,这是表示她们内心的寂寞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想,她们只是知道这句话是出现在“非主流论坛”里,她们看到那些颓废图片里的女主角在吸着一根烟,神情冷酷,后来也跟着愚昧地模仿起来了!
颓废非主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茅盾;子夜;颓废;研究
《子夜》是茅盾的力作,被誉为1930年代左翼文学家的代表作品。这本被瞿秋白称为“我国首部写实代表作的长篇力作”的书籍,其所表现出的浓烈的颓废色调,映射了当时社会的风貌。该作品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大环境,以民族资本家与买办金融资本家的冲突为叙述核心,再现了1930年代的我国社会的面貌。《子夜》中气势磅礴的描绘了我国民族资本家的悲惨境遇,充满了浓烈的颓废色调。[1]
一、奢靡的城市生活呈现出的颓废元素――工业文化对正统道德的渗透
提及1930年代的沪市,民众的印象是隐秘、刺激、冒险、物欲杂糅在一起。长时间居住在上海租界的茅盾,对上海租界区的繁荣感受是特别的。在提及《子夜》的美学创设时,茅盾曾指出,色调与声音在《子夜》中描述最多,与整篇文章的心理历程辉映。《子夜》的开头有着独到的韵味,首先,茅盾从自身的角度描绘出外滩的景象:碧波荡漾的苏州河、随风飘来的外滩公园中的乐曲、矗立的钢架、火花飞溅的电缆、呼啸而过的电车、浦东的客栈、闪耀人眼的霓虹灯等,这部分当代城市的经典画面,伴随吴荪甫的雪铁龙轿车飞旋的轮胎,就好比影片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形成一副都市奇观。茅盾《子夜》中的上海,充满当代工业文化冲击下的各类繁荣的、当代化的物质元素,并且随着当代文化的渗透,派生出各类事物。例如,生态被破坏的河流、充满暗色空间的奢靡音调、散发出的感官刺激与颓废色调,从另一种角度昭示了上海的某类特征。《子夜》也以吴老头这类传统的封建地主的角度,描绘了上海的“怪诞”,充满灯火的窗口、直插云霄的现代大楼、拔地而起的街灯,犹如张牙舞爪的怪兽,将吴老头推向“恐怖”的环境。在繁荣的大上海,接踵而至的各类感官感受让吴老头感觉头昏、耳鸣,最终走向死亡。这段描述,是工业文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同时也充满颓废感。[2]
1930年代的上海规模在我国首屈一指,有着“东方巴黎”的美誉,其物质文化的发达让其跻身全球闻名都市的行列。奢靡、平淡、浇漓、肤浅,豪华而贫乏、奢靡而颓废,是上海的特征。茅盾对上海的解读是极其到位的,是同年代的其它文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其精心描绘的上海是充溢着喧闹与神经质的怪诞的城市,并且在《子夜》这部作品中将其颓废元素描绘得淋漓尽致。[3]
二、屋内环境――色调丰富的丑恶空间
在《子夜》中,茅盾对屋内环境的描述最为频繁的就是吴公馆。吴公馆在上海代表着权势与财富,其奢华的装修与娱乐设备其实就是上海的浓缩。其客厅的奢华程度让人惊讶。而与舞厅、赛马场等屋外环境对比,其是柔和的,缺少刺激,但是也是暗箭丛生、勾心斗角的所在。其平静与祥和的表象下,更体现出了现实的惨酷,将人的迷茫、理智与非理智的斗争、现实与理想的碰撞描绘得入木三分。[4]
《子夜》对吴公馆客厅的描述是以吴老头的视角来进行的。吴老头眼中的客厅是辉煌通明的、人满为患的,并且有着各种彩色的灯泡,女人的装束极为大胆,物欲充满了整个吴公馆,吴老头承受不住,一命呜呼,更是为以后的描写奠定了基础。而对交际花徐曼丽的描写更体现出当代上海人的奢靡与颓废。在充溢着物欲的大城市,钱财与肉体的交易更是肆无忌惮,并且在吴公馆吴老头的葬礼上也出现了“死之跳舞”。让读者读来觉得无比悲哀,这部分人物在对感官刺激的追寻中,也充满了浓郁的颓废色调。[5]
而吴公馆里的活动还远没有结束。吴公馆的女主角,吴少奶奶对爱情的憧憬也与吴家的客厅联系在了一起。吴公馆里的布置豪华、古玩众多,然而吴少奶奶却觉得美中不足。那么到底是哪里“不足”呢?林少奶奶是有知识的现代女性,其对这类富裕的物质环境也欣然接受,然而在精神上,其有着自身的要求,其心中有着雷参谋的位置,并且迷恋爱情。因此,其珍藏着雷参谋赠与她的书籍与鲜花。投入到事业中的吴荪甫无法在爱情方面满足林少奶奶,物质世界丰盛,然而精神世界却是空洞的,这类精神世界的崩塌导致的孤僻、幻想,成为大上海的常态。[6]这类状态正是颓废形成的主因,人性在这类因素的作用下显得不堪一击,理智的吴荪甫在吴公馆内佣人王妈就是佐证。投资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吴荪甫也变得极为丑恶,而王妈就沦为了吴荪甫的发泄对象,其表现了吴荪甫的颓废,也映射了大上海的颓废。
结束语:
综上,茅盾原来想将《子夜》写成一本气势磅礴的小说,并且揭露1930年代的中国城乡的表象与实质,然而成稿后却倾向于城市生活的描绘。对1930年代上海的面貌实施了全面的描写。《子夜》的存在,充满了颓废色调,也杂糅了茅盾的真情实感。
参考文献:
[1] 许祖华,杨程.两种现代性下的“中国传奇”――以茅盾的《子夜》与穆时英的《中国行进》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14.
[2] 俞春放.真实性话语与现代性焦虑――从《子夜》谈当代中国小说经典的形成机制[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23(1):109-116.
[3] 田长明.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茅盾小说《子夜》主人公吴荪甫形象分析[J].课外语文(下),2016,(6):147-147.
[4] 高瑜.浅谈作家气质和人物形象对作品气韵的影响--以茅盾先生的《子夜》为例[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4,(2):55-55.
颓废非主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描写;象征;暗示;世纪末;时代寓言
对于从哪个角度看当代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下简称《布》)中布氏家族的衰落这个问题,不同的评论有不同的答案。社会一历史批评学派用社会一历史的眼光审视小说,认为小说揭示的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历史过渡;心理一哲学学派则从心理一哲学的角度阅读小说,认为小说揭示的是一段与社会现实无必然关联、非历史的灵魂演变史。对《布》的意蕴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笔者认为,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作为文化人的作家,在其艺术创造过程中都会受其所在文化背景的制约,所以作品必然要表现出其文化心态,于是当我们从深层文化意蕴角度来看这部人类巨著时可以发现,托马斯・曼对社会与人的研究,并未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层面上,还穿透了社会一历史外壳,对人类社会生存状况作了深入的思考,因而他的小说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同时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化哲学意蕴,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加深入地把握《布》的无穷魅力。笔者认为,这部投射作家生命体验的小说实质上在托马斯・曼的演绎下,运用描写、象征和暗示的手法,追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来表现作家所处的世纪末德国文化。换句话说,这部打上了托马斯・曼青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印记的小说,实际上已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一个象征隐喻。
读完这部厚厚的小说,掩卷遐想时,会发觉虽然书中都是有关布氏家族婚丧喜庆一类的家庭生活场面描写,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托马斯和汉诺对死亡的迷恋,以及疾病与健康的对立,履行市民义务和逃避现实、遁入浪漫主义的梦幻的对立等有关玄奥的形而上领域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布》是一部“时代寓言”的小说。说它是部“时代寓言”小说,是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地反映时代,摹写和揭示社会中政冶、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情况的“时代小说”。它缺少对于构成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基本的因素――经济因素的思考和表现,也完全没有企图追寻、分析造成这种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德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部小说中对布氏成员的生活状态进行真实的细节描绘中加上了许多暗示,使这个家族没落的悲剧有了象征意义。小说的副标题“一个家族的没落”,就蕴有浓郁的象征意识。没落象征着国家和民族的不振,布氏一家人的不同程度的病态象征着那个时代的颓废,布氏成员对没落结局的困惑象征着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犹如迷途的羔羊一般……特别是布氏家族最后两代人的生活面貌、精神状态更是对19世纪末德国人的颓废生活状态的隐喻。
伴随着德国19世纪末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德国也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型――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向以“颓废”为特征的非理性主义价值体系转向。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失去了传统理性原则的制约而走向尔虞我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那种人性自由、人人平等的理想的虚幻性,于是人类追求和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很自然地陷入了具有浓重“颓废”色彩的非理性境地。理性时代受到新崛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峻挑战,而且后者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蔓延到一切文化领域,上升为主流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叔本华、尼采、瓦格纳成了人们十分熟悉的名字。认为生存伴随着痛苦,意志是痛苦之源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尼采以超群勇气重估价值的批判锋芒、极度张扬个体生命的权利意志和酒神精神,以及具体体现浪漫派以艺术解脱痛苦的瓦格纳的音乐,成为世纪转折时代表征德国文化的三颗闪烁之星。
无疑,布氏第一代人老约翰和第二代人小约翰所生活的时代代表着受理性主义原则制约的时代。布氏家族从兴盛走向没落的过程也正是德国由受理性主义原则制约的时代向非理性主义原则制约的时展的过程。由非理性主义原则带来的这种颓废文化在小说中通过布氏第三代人托马斯和第四代人汉诺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身上集中反映出来。小说中托马斯继承家业以后,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竞选成功,被选为议员;购置了房产;……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可以望得到的、摸得着的标志和征候”。托马斯内外交困,经受着事业、家庭、情感和信仰的全面危机:一是公司利益亏损,家族财产又大量外流,布氏家族面临既不能开源,又无法节流的双重困难;二是弟弟克利斯蒂安吊儿郎当,儿子汉诺又无心继业经商,他被迫孤军奋战,看不到前途;三是妻子盖尔达和他志趣不合,隔阂越来越深,他不仅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反而因为盖尔达与一位年轻军官双双对对地搞音乐而妒火中烧;四是他越来越喜欢冥思苦想,这使他的内心产生更多的矛盾的痛苦,使他厌倦经商,厌倦生活。如此看来,托马斯的这种生存困境,其实暗示的不正是叔本华所描绘的悲观暗淡的宇宙图景吗?
与托马斯・曼的晚期小说《死在威尼斯》中的阿申马赫一样,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要花大量的精力来掩盖他日益增强的厌世感。他逐渐认识到了意志的可悲本质,在遗嘱中作出解散布氏公司的决定。因为他的内心是空虚的,他看不见有什么令人振奋的计划、有吸引人的工作值得他欢欣鼓舞地全力投入。他心中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预感,其中一个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是:这一切不会延续多久了,他不久即将离开人世了。托马斯・曼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现托马斯思考死亡与不朽之类的问题的心理世界。在托马斯的心理世界里,读者可以看出这其中隐含着托马斯心中的非理性逐步取性的过程。他本来认为他的生命在祖先身上就体现过,将来则借着子孙继续活下去。无疑,这种观念是与他的父辈相符合的理性观念。这种理性观念符合他的宗族意识、家长感、对祖先崇敬,而且对他的活动、他的野心、他的生存都是一种支持和鼓舞。但是托马斯失去了父辈的信仰。他的祖父约翰的世俗的怀疑精神,那种肤浅的“怡然自得”不能支撑他的生存信念。他也不能像他的父亲小约翰那样“把商人的极端讲求实际的思想、对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精神和虔诚的偏于形式的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很好”;对托马斯来说,这种信仰却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思想陷入了危机。“‘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复活’了;‘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没成型。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人为所欲为的世界;一个失去了理性 制约的时代,是非理性泛滥的时代。非理性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蔓延开来的。‘上帝’死了,却没有救活人自己,人类似乎到了在劫难逃的世界末日。”
在托马斯的身上展示了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心灵世界的迷茫痛苦。死亡成了托马斯解脱生存痛苦的途径。托马斯・曼是这样描写托马斯的心境的:
“他胸中洋溢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感激和满足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头脑这样征服了生命,征服了这个强悍、残忍、嘲讽的生命,可以任意摆布它、处置它,不禁感到无比的满足……这是一个受苦受难者的满足。本来他困于生命的冷酷和残忍,一直在含羞忍辱……如今他忍受世界一切痛苦都是合法的了……这个世界本来是人们想象中的最美好的世界,而这个伟大的权威家却以游戏的讥嘲证明它为最坏的世界……这一章的题目是:《论死兼论死与生命本质不灭之关系》。阖上书,向四周看了看……他觉得他的全身无限地扩张起来,心中充满了沉重的酩酊欲醉的感觉……”
这段描写,不正是叔本华的亡灵在托马斯身上复活的生动体现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成了托马斯战胜令他痛苦的意志的象征。
而布氏家族的最后子嗣汉诺更是颓废派的典型。他体弱,内向,没有朝气,不求上进。艺术使汉诺早熟,早熟得看破了红尘。汉诺“肓城府,会观察,父亲的希望、烦恼、心计他一目了然,教师的阴暗心理他更是一眼看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冷眼看世界”。汉诺“实际看到的比他应该看到的还要多,他的那双羞怯的、罩着青眼圈的金棕色眼睛很会观察事物。他不只看到父亲交际应酬显示出来的那种稳重和亲切,他也看到――用他的奇特的甚至使自己痛苦的锐利目光――这种做作对他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他拜会完一家后变得脸色苍白,一语不发,眼皮红肿,紧闭着眼睛斜靠在马车角上。他满怀惊惧地看到,一跨进另外一家的门槛,这一幅面幕怎样从父亲的面孔上落下来,他那疲惫的身体怎样变得行动富有弹力起来……议员在和别人周旋时的言谈举止,在小约翰看来,并不是那种为了保障某些实际利益……而发出来的自然、真实、一半并非出于自觉的言谈举止;相反,他这时的动作谈吐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费力的造作,因此,在做时毫无自然、从容、真实的感觉,而只是一种特别沉滞、殚精竭虑的故意卖弄。有时汉诺想到将来有一天别人也期待自己在公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下做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谈吐,他就不由得又厌恶又害怕地打了个冷战,急忙闭起眼睛来……”
汉诺看穿了尔虞我诈、相互吞噬的商业界,也看破了把威信、责任、权力、事业、普鲁士的纪律严明的精神奉若神明的生活。为了克服精神上的空虚和痛苦,他只有钻进音乐的天国。他认为那是一个“温柔、甜蜜、庄严而又能无限慰藉的音响的国土”。但是音乐艺术只能安慰人,却不能给人以希望,甚至会消磨人的生命意志。他感觉到音乐是美好的,但是这美好的东西“会吞噬一个人平凡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厌恶他所生活的现实环境――包括商业环境和学校。本是为增强他的体质的海边度假,却使“他的心变得比以前更柔软、更任性、更敏感、更富于梦想了”。他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既不给别人希望,也不给自己希望;即使是在音乐方面他也只是一味地享受、消费,没显出要当什么家的苗头。这也是典型颓废派的一个标志――无创造力和逃避庸俗的生活。他对生充满了厌恶,只是一心沉浸在具有颓废意味的瓦格纳音乐世界里,希望“用艺术的行为去克服自己心中的虚无”。他所热爱的瓦格纳音乐就像一个不祥之兆,一团死亡的阴影,给他带来的只是生存意志的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