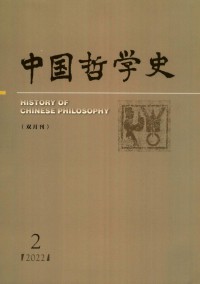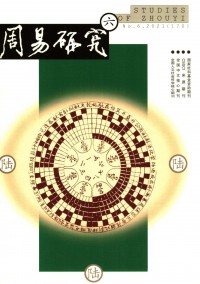朱熹的诗
朱熹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朱熹,孔子,诗教理论
翻开中国教育的历史书卷,堪称教育家的人不胜枚举。虽然他们的教育思想大都散见于各种作品中,但只要系统的加以研究便会看到他们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大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生活比孔子晚了一千多年,但是他在自己生活的年代把儒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使儒学思想在统治阶级的影响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朱熹与孔子都是中国古代的大语文教育家。虽然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是在1904年,但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却源远流长,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中国语文教育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孔子和朱熹都是对中国语文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今天我们把两位语文教育家的思想作一系统研究,希望能够从中得出一些对当今语文课程改革有益借鉴。
从总的指导思想来看,朱熹与孔子的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他们的诗教理论的其他方面有着很大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朱熹的诗教理论倡导“以理为本”,他认为天理是人性伦理的行为纲领。他的诗教理论无处不渗透着“理”的影子,“理”是他诗教理论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诗教理论倡导“以人为本”,孔子的诗教理论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他推崇诗教的宗旨是为了净化、美化人的心灵,并使人获得一定的能力。他认为学诗的最终目的是涵养德行以施行仁政。
因为指导思想以及生活时代的不同,朱熹的诗教理论跟孔子的诗教理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不同,以下我们具体从诗教的目的、标准、功能、过程、方法等方面来研究一下两位大家在诗教理论方面的见解。
从诗教的目的来看,孔子认为诗教的目的是“思无邪”。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礼记•经解篇》有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②]“思无邪”是心灵净化美化的一种至境;温柔敦厚,则是个体情感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水平。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教的目的是达到“思无邪”的境界。而朱熹则认为诗教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③],朱熹认为诗教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朱熹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懂“理”、明“道”。他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朱熹诗教理论的终极目标就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大语文教育家在语文教育目的方面的不同见解,孔子认为诗教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人的发展,达到思无邪的程度,而朱熹则认为诗教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懂理、明道。
从诗教的功能来看,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⑤]“兴”即赋、比、兴,指通过学诗可以学习诗的表现方法;“观”即通过学诗、采诗以提高观察力和认识能力;“群”即通过学诗、用诗以锻炼合群性,涵养与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的能力,以促进社会和谐;“怨”即指借诗以表达讽刺的方法,引导人们表达哀乐的程度要适中,表达的方式也不能太过。。孔子所说的“怨”说到底就是通过学诗来涵养人际交往的能力、态度与方法。而朱熹认为诗教是为了学习圣人之言、圣人之思、圣人之乐、圣人之经。他说:“圣人之言,足以为教;圣人之思,足以为教;圣人之乐,足以为教;圣人之经,足以为教”。朱熹认为教育是使人读书、识字,“成人”、“成智”,他希望通过教育能培养出“明人伦”、“复性”、“亲民”的人才,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
在诗教的过程方面,孔子主张自求、自得、自省、自成,注重创设情境,观察体认,群体交流和得体表达,很明显这是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过程论。孔子很注重学生的自我感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孔子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⑥]孔子的诗教过程论也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教育指导思想。而朱熹则认为诗教的过程可以分为端、变、规、止。他在《诗集传》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观,和之于颂以要其止”[⑦]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诗教过程注重文本本身的理,是以理为中心的。
在诗教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始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⑧],认为学习的东西最终能够用到现实当中,才算是完成了学习的任务,是以言语实践为学习的最终落脚点。而朱熹则认为学诗要以“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礼之”[⑨]认为学习诗的方法必须按照诗词的句式、注释、韵律等来进行。是按照一种纲领性的东西来对诗进行理解。朱熹的诗教方法更多的注重了诗的文本,而在诗对人的影响方面,则有所疏漏。
综上所述,朱熹跟孔子在诗教理论方面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孔子诗教理论的至境是美学,其目标是净化人的心灵,让学生的思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孔子诗教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的逻辑起点是学者通过学《诗》以陶冶情操并不断提升言语实践能力,在自求、自得、自省、自成中涵养学生美丽的人生。而朱熹诗教理论的至境是“理”学,他的诗教理论的各个方面都从属于文本,从属于理性,朱熹诗教理论的出发点是文本,落脚点则是“理”
其次,孔子的诗教是一种思想,是希望能够通过诗,来培养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能够使学生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价值,是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出发点的。而朱熹的诗教理论是一种纲领,他明确了诗教的目标、标准、功能等,使教学更容易进行,增强了诗教理论的可操作性,但是忽略了教育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一要本目的,因为朱熹的诗教理论是以教学过程为主的,所以操作性比较强,这也在一定程序度上导致很长时间以来语文教育注重“语”、“修”、“逻”、“文”,而忽视听、说等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
最后,孔子诗教理论的“兴、观、群、怨”是在一个开放的本体中,借诗以促进学生的发展。兴——观——群——怨提出了诗教的基本过程:创设情境)——观察体认——群体交流——得体表达。这在今天看来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朱熹的言教、思教、乐教、经教则是借圣人之言、圣人之道,来限制和束缚人的自由发展,以培养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
在新课程改革全面展开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作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因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也只有放眼中国语文教育的过去,取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之精华,并弃其糟粕,才能更好的找到中国语文教育的出路。
参 考 文 献
[1].杨伯峻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孟承宪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 靳健著: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 张隆华,曾仲珊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 毛礼锐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朱熹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朱熹 《诗集传》 前后稿嬗变
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其多为引用、解释《诗集传》,如宋代辅广的《诗童子问》,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明代朱善的《诗解颐》,胡广的《诗经大全》,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方苞的《朱子诗义补正》等著作。清代学者则更是撰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单篇论文,如冯景的《朱子驳诗古序辩》和《驳阎百诗毛朱诗说》,萧穆的《重刊朱子诗义补正序》,冯登府的《书宋本诗经集传后》和傅维森的《读朱子诗集传》,等等。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出现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著,研究不断深入,角度越来越新,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差异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诗集传》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诗经》宋学的开端,其总体上呈现怀疑、创新的学术特色,朱熹《诗集传》更是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时期起,欧阳修、刘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汉唐《诗》学的旧有模式,并且初步对《毛序》、《郑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将《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宋代《诗》学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是书上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划时代的学术论著。
朱熹前后期《诗》学思想差别极大:前期主《毛序》作《诗集解》,依《序》说诗;后期随着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及废《序》派学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最终废《序》解诗,弃前稿《诗集解》而更为后稿《诗集传》。由于前人对前后稿的嬗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出现了一些误说,束景南先生针对这些误说,在《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中的《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章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朱熹解《诗》的历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诗集解》与黜《毛序》作《诗集传》两大阶段。
由于朱熹废《序》言诗及其《诗》学思想的最终确立,后稿《诗集传》成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却最终失传。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辑稿》据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了朱熹《诗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为研究《诗集解》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辑本。
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
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嬗变,实际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诗》学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变过程已经原因的根本途径。
郝桂敏先生《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一书的第五章《朱熹的〈诗经〉研究》,谈到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提出:由于从理学角度看诗,朱熹对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进行了改造。
朱熹着手废《诗序》作《诗集传》的时期,正是其理学思想刚刚确立的时期。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论证。朱熹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有一个统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理,人类社会的常理便是“三纲五常”。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更是鲜明的凸显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诗时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在该书第四章《理学思想与朱熹诗经学之关系》中,他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其为学的根本即在“义理”之中。其为学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以后者为手段,前者为旨归。所以他的理学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经典,其注解既能够尊重文本求其本义,又能够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朱熹《诗》学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朱熹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对其治《诗》的影响是使其《诗集传》解诗之所以呈现出鲜明文学性的重要原因。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郝桂敏先生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以及檀作文先生的《朱熹诗经学研究》都对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是檀作文的《朱熹诗经学研究》及其单篇论文《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对此更是论述颇详。
朱熹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武夷山;朱熹;游道;旅游文化
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艺术,称之为游道。朱熹作为宋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旅游活动盛极一时。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日趋完备。士人漫游成风 ,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
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予少好佳山水异甚。”[1]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1]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活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他强调说:“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1]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1]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2]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学习、著述、讲学生活的调济。
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它描绘了孔子与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
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活信条。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活动过程,自然为智者所乐。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1]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1]这说明朱熹居崇安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年(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1]
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1],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1]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
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
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1]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朱熹一生游踪遍及中国半壁。
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1]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1],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与昼寒亭的静谧及瀑布的奇绝。
朱熹不怕旅途的艰辛,往往旧游或重寻。他曾与学友门人数人早发五夫潭溪,夜登建阳云谷山,冒雨登建阳龙湖山,一日行程百余里。因为泉石的招引,使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他知道无数风光在险峰的道理,因而寄语后来人,勿辞行路难。后来,他干脆在云谷山上筑“晦庵”,流连山间。林泉之胜、思想的自由及归途还可采薇蕨、蔬笋等乐趣,使他苦游不畏。朱熹具备如林语堂所说的胸中一幅别才,眉下一幅别眼,对旅游活动有较高的山水审美水平,故地重游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他能够随着一路景物的不同,时序的不同,随处留情随处乐,因而就不怕旅途的辛苦和屡次重游了。
四、“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游辞有艺
朱熹游目聘怀,题诗唱酬。他的武夷旅游诗雅赏风景,格调清新,情景交融,空灵轻逸,形神兼备,词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首先,他善用比喻来摹写物态特征,使之精当、新颖、富有美感,既有形似之感,更兼传神之妙。例如《天柱峰》中“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把大王峰比作天柱,突出了它的气势。把密庵瀑布比成“白龙飞下郁兰天”,[1]可谓形神俱显,活灵活现,令人心动魄摇,增加了艺术美感与诱人魅力。其次,他善用衬托的手法描绘他物,以对所咏之物起陪衬或烘托作用,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晚翠乍看浑欲滴,寒流重听不胜清,个中有趣无人会,琴罢尊空月四更。”[1]通过寒流、四更月、辞官归乡、旧友,来衬托出“清”的气氛及无官一身轻而悠游、弹琴、赋诗、饮酒的闲适之情。再者,朱熹还善用拟人的手法来活化毫无生命之物,从而闪耀出不凡的光彩。如《九曲棹歌》描摹武夷山的玉女峰:“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1]把一座山峰人格化了,描绘成婷婷玉立插花打扮的少女,突出了玉女峰的神韵。最后,朱熹旅游诗中也融入了丰富的典故和民间传说。如《九曲棹歌》中有:“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1]就用到了“仙人葬”的神话传说。朱熹的旅游诗状物写景准确而形象,细致而生动,悠然与神谋,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功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五、“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穷游尽理
朱熹旅游振策寻源,往往直到山中无往躅才肯罢休。他在游赏山水中没有忘记探求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作为儒、释、道三教同山的武夷山,深山穷谷中有不少道士、释子。一方面,朱熹心存仰慕,“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另一方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又不无表示怀疑,“我欲往从之,脱履谋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他又说:“眷言羽衣子,俛仰曰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1]作为入世的理学家,他显然不同意佛、道的出世偷安的做法,但对他们的人格还是持褒意的。他说“是其绝灭伦类,虽不免得罪于先王之教,然其视世之贪利冒色沉溺而不厌者,则既贤矣。”[1]
朱熹寄情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反映。《论语·泰伯》里有孔子一句政治名言,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朱熹浙东辞官归来退居武夷山讲学著述是他历来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周游列国后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决绝之言。好友陆游的诗“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两忘”吐露了对朱熹从此与世相忘的担心。而朱熹的《感春赋》提到的“悟往哲之明训”[1]回答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
朱熹寓学、寓教于游,让学生亲近自然,把旅游当作求知的课堂。在《武夷图序》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悬棺葬”进行的实地考察,“两岸绝壁人迹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船棺之属”,世传为仙人葬处,披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朱熹则大胆指出:“旧记相传诡妄,不足考信”,[1]而认为它是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悬棺提出了比较符合科学的独立见解。
朱熹认为世上万物皆有其理,通过旅游可以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在游云谷诗中他呤到:“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1]他平生三伏天不再出游,而是躲进深山避暑,为的是不欲暑行劳人,力争不伤不损。他穷游山中,往往循涧跻危蹬,披云得胜游,在游历观赏山水中领略玄趣,与月为朋与云为友,与环境合为一,从而达到物我相通、天人合一、独游不孤的精神境界,可谓因游及理,因景言理。
六、“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纪游不朽
朱熹观山临水有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在咏仙洲新亭的诗中吟到:“若无诗律好,清绝不成欢”、“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1]就说明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如《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九曲棹歌》、《武夷七咏》、《过武夷作》、《游密庵》、《密庵瀑布》等等,为我们勾勒了宋代武夷山水风景图,其中《九曲棹歌》更是被后世尊为武夷首唱的千古之作。
朱熹也留下了一些题赞。如武夷山吴屯瑞岩寺为唐代高僧扣冰祖庭。扣冰俗姓翁,名藻光,因能在严冬扣冰而浴,故称其抑制情感的“惺惺”之说与朱熹“灭人欲”之说相近,朱熹对其大为赞,并曾策杖寻访遗迹,除了写有《咏瑞岩寺》诗外,也留下了对配祀的唐、葛、周三将军的题赞,这些都表达了朱熹对这些神灵的崇敬之情。
朱熹在武夷山还留下了十几处之多的匾额和刻石。水帘洞为武夷三先生刘子翚、胡宪、刘勉之讲学处,朱熹也曾在此受教,为纪念先贤,朱熹题有“百世如见”匾额挂于祠中。在武夷山一线天附近,有“天心明月”摩崖题刻。明月倍受朱子垂青,这大概是因其品行高洁及受月印万川启发,形成朱子理学“理一分殊”结论的缘故。此外如还有五曲“逝者如斯”石刻,下梅邹氏家祠“爱莲堂”匾等等。这些题刻给武夷山留下了永恒的历史文化魅力。
总之,朱熹对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并形成自己的旅游之道。他赋予旅游更多的主观感受,以前很少涉及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其旅游有审美能力与意境领悟上的精进;他的旅游活动融入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遭际,从而丰富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内涵。明代周忱在他的《小西天游记》中说:天下山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能至是旅游的第一境界,能至才能享受,才能领悟;能言,即善于向人说出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旅游第二境界;能文为旅游的最高境界,只有能文才能感受深刻,才能传之久远。朱熹既能至又能言又能文,他的旅游活动已达很高的境界。我们有必要对其旅游活动及其思想进行挖掘,对其遗迹进行整理、保护。
参考文献
[1]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3]建阳蔡氏九儒研究会.考亭紫阳朱氏总谱[m].建阳:第三印刷厂,2000.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朱熹的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诗经;爱情诗;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214-01
齐风・102甫田:
褚斌杰:少女恋慕少年。程俊英:思念远人。朱熹: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无功也。姚际恒:此诗未详……《猗嗟》亦云“猗嗟娈兮,清扬婉兮”也。按《诗》多同句,而上二章之辞则全不合。方玉润:未详,词义极浅,尽人能识。惟意旨所在,则不可知。屈万里:此盖喜远人归来之诗。闻一多:无题解。属女词。
此诗从褚,归为爱情诗。
魏风・108汾沮洳:
褚斌杰:一女子夸赞其情人。程俊英:赞美劳动者才德。朱熹:此亦刺俭不中礼之诗。姚际恒:此诗人赞其公族大夫之诗。方玉润:美俭德也。屈万里:此盖刺某大夫爱修饰之诗。闻一多:无题解,属女词。
此诗从褚从闻,归为爱情诗。
唐风・116扬之水:
褚斌杰:女子投奔所爱之人。程俊英:揭发告密。朱熹: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桓叔。其后沃盛强而晋微弱,国人将叛而归之,故作此诗。姚际恒: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皆可以见国人之心矣。方玉润:讽昭公以备曲沃也。屈万里:列《诗序》,刺晋昭公……事见桓公二年左传。闻一多:无题解,归附篇。
此诗暂从褚斌杰,归为爱情诗。
陈风・136宛丘:
褚斌杰:一男子深爱一活泼善舞的女子。程俊英:写一个以巫为职业的。朱熹:国人见此人常游荡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姚际恒:此诗刺游荡之意昭然。方玉润:刺上位游荡无度也。屈万里:此刺游荡之诗。闻一多:无题解,属于第三类。
此诗暂从褚斌杰,归为爱情诗。
曹风・151候人:
褚斌杰:一说是女求男的情诗;一说是刺新贵。程俊英:与褚斌杰第二说相同。朱熹: 此刺其君远君子而近小人之辞。姚际恒:刺诗。方玉润:刺曹君远君子而近小人也。屈万里:《诗序》谓此为刺曹共公之诗,似是。闻一多:属于第三类,刺曹女也。
此诗从褚斌杰第一说,归为爱情诗。
小雅・199何人斯:
褚斌杰:一女子怀念和埋怨旧日情人。程俊英:同事绝交诗。朱熹:此篇专责馋人耳。姚际恒:刺馋。方玉润:刺反侧也。屈万里:……然为朋友绝交之诗,则文义甚显。
此诗从褚斌杰,归为爱情诗。
小雅・225都人士:
褚斌杰:送别贵族人士、女子返归京都。程俊英:忆念意中人。还列三说:刺诗;怀旧;逸诗。朱熹: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姚际恒:盖想旧都人物之盛,伤今不见而作。方玉润:缅旧都人物之盛。屈万里:此咏某贵家女出嫁于周之诗。
此诗从程,归为爱情诗。
争议较大的婚姻诗有3首:邶风・37旄丘、齐风・105载驱、小雅・197小弁。
邶风・37旄丘:
褚斌杰:女子疑丈夫有外遇。程俊英:流亡诗。朱熹:此诗本责卫君,而但斥其臣,可见其优柔而不迫也。姚际恒:引《毛传》“彼旄丘之上有葛,其节何蔓延而长?虽前高后下之丘,犹远相及。我之伯叔同处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何也?”此说存之。方玉润:黎臣劝君勿望救于卫也。屈万里:引《诗序》,责卫伯也……闻一多:无题解,属女词。
此诗暂从褚斌杰,归为婚姻诗。
齐风・105载驱:
褚斌杰:文姜往来齐鲁间,纵情游荡取乐。程俊英:齐女嫁鲁。朱熹:齐人刺文姜乘此车而来会襄公也。姚际恒:《小序》谓刺齐襄……《集传》皆以为指文姜,意亦贯。方玉润:刺文姜如齐无忌也。屈万里:此盖咏文姜与齐襄公聚会之诗。闻一多:齐女归于鲁(无刺意)。
此诗从程从闻,归为婚姻诗。
小雅・197小弁:
褚斌杰:被逐者的哀音。程俊英:被父放逐的儿子的诉苦。朱熹:幽王……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姚际恒:引《小序》《大序》,辩驳,引孟子言,引赵岐注,终无定论。方玉润:宜臼自伤被废也。屈万里:人子不得于其父母者所作。闻一多:伐木析薪喻婚姻,掎L言不得人也。
此诗从褚从闻,归为婚姻诗。
可能为爱情诗的有5首,是:郑风・77叔于田、郑风・78大叔于田、齐风・103卢令、唐风・120羔裘、唐风・122无衣。
郑风・77叔于田:
褚斌杰:一女子赞她所爱的男子汉。程俊英:赞美猎人。朱熹: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姚际恒:从《集传》,段不义得众,国人爱之而作。方玉润:刺庄公纵弟田猎自喜也。屈万里:旧谓共叔段不义而得众,国人爱之,而作是诗。闻一多:属女词。从朱说,“男女相悦”。
此诗从褚从闻,归为爱情诗。
朱熹的诗范文第5篇
Abstract: Cui Shu researches on "The Book of Odes " unconventionally and originally, cause for which is his special experience in reading "The Book of Odes", a good hom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ep influence of Zhu Xi's paleo-suspicion concept.
关键词: 崔述;治《诗》;疑古
Key words: Cui Shu; research "The Book of Odes"; paleo-suspicion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2-0306-02
0引言
据《清史稿》所载“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1]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之《点校说明》评价:“由于清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严格控制,使知识分子或则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很少说明和探讨,或则以微言大义、纬候灾异对《诗经》曲解。有清一代能跳出传统束缚,努力探求《诗经》本意的不过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人。”[2]可见崔述在学术上见解独到是早有公论的。
崔述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运用了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用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神话和传说。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后,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于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后知“六经”之精粹也。[3]可见崔述学术思想是从少年读书时怀疑传记所载古帝王、圣贤之事开始确立的。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崔述少年读书时为什么能看出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的地方,而治学又不胶固于古圣先贤之成说呢?如何对《读风偶识》乃至崔述整个学术成就的取得作以深刻而恰当的剖析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仍必须回到“知人论世”这一命题上来。孟子曾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所谓“知人论世”,就是指考察一部作品,一定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才能找到其根本,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得益于他少小时独特的读《诗》经历
崔述自叙他少时读《诗经》的经验曰:“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以故余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5]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自幼勤奋好学的他,在初读《诗经》时只读经文,没有传注,虽《读风臆评》也有评语,但他喜欢的是抑扬宛转的诗句。只有八九岁的崔述只熟读经文而成诵。中国古代学者尊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传统的治诗学者总死守自己的门派,不越雷池半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者都缺少新鲜的见解,使诗学的研究发展缓慢,但崔述能独自体味,别人的成见对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熟读精思之后,必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但某种观念在人思想中形成,自然会排斥其他思想。第一印象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对于善于疑古的崔述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即使他后来读了《诗序》也认为“不知其宝贵者何在”。
崔述以举人终其一生,年近花甲仅得一县令,在官位定势的时代,他本人地位不显,交友不广。他的治学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崔述认为:“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6]
所以崔述既无师承,又交游不广,没有师承,就减少了主观上要去维护某种观点的可能,也会尽可能少地受别人“成见”的影响,同时崔述本人也常对人们惯以自身经验去批评他人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必须排斥成见,方能获得文本意义上的正确理解。他对前代和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甚少。这虽有某些方面的缺憾,但也为他治《诗》独到创造了条件。
2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良好的教育环境是人成才的重要因素,顾颉刚认为:“崔述少年读书时,为什么能看出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的地方,实由于其父的教育方法。”[7]
顾颉刚肯定了崔父对儿子的影响。尽管崔述出身寒门,但其世代书香的世家。为他成才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前其曾祖父做过举人,虽不曾做过大官,但也曾选过大成县教谕,晚年隐居著书十余卷;其父虽仕途不顺,但后来开办了私塾,他把自己的雄心抱负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崔述的长兄死得早,父亲对述及其弟迈疼爱有加,但管教也很严厉。五六岁时述就跟着父亲读书,年仅十四岁即博览群书,这就为他日后的学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常让他闭门读书,不让他接触市井之言,不和游闲的少年交往。这就能使他更好的安心读书,他曾对崔述说:“尔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于明道经世之学,欲尔成我志耳。尔若能然,则吾子也!”[8]
崔述之所以取名为“述”,就是要述其父欲明道经世之志。其父崔元森认为:“于经则购自明以来诸家诠解,盈架上。毫厘之疑,必为诸生详辨之。务求圣人之意,不拘守时俗所训释。”[9]
他的这一辨伪原则直接灌输在崔述的思想中。《考信附录》中载有《先君教述读书法》,略云:“先君教述,……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合读亦五十遍。……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10]
前人以为传、记即是经,注、疏必得经意,把二千余年陆续发生的各家学说视为一个整体。但崔述在幼小时就养成了“不以传注杂于经”的这一基本考信方法,因此他又说:先君教述读注,惟圈外注有经旨未洽者不读,其余皆读,不肯失其本来面目也。[11]他的教育方法是要把材料认真分析,要回复本子之原状,让各时代,各个人,各本子均分开了,而不浑作一团,受父亲的影响,崔述从小就养成了爱分析的习惯。这种精神,前人太缺乏,他们囿于道统之见,以为圣圣相传,其心志必如一;贤者希圣,其解释的圣言也必合于原意。即使逢到不同的地方,也以圣人的早年、晚年区别开来。而崔述分得出各种事态的层次,懂得各家学说的演化。他认为一种学说不是突然出现的,所以要寻出它的前后左右的关系,《经传E祀通考》便是很好的例证。
3受朱熹疑古思想的影响
疑古辨伪,崔述当然不是开先河者,他的这一治学指导思想有其历史继承。中国的疑古辨伪思想,萌芽于春秋之末,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端,他开创了对古代传说考而后信的实事求是的平实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贡继承了这一思想,秦、汉间人的辨伪,司马迁应为首功。东汉时期马融、卢植、临硕、何休也都是疑古的佼佼者,魏晋南北朝时,有造伪者也有刘勰等人承担了辨伪工作,唐代的疑古辨伪为后人开拓了辨伪的渠道。宋人辨伪始于欧阳修,与他的后继者郑樵、朱熹为宋代辨伪的三个主要人物。仁宗时,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序》中指出了从黄帝以来到尧、舜这段古史是司马迁增益进去的,致使北宋辨伪之风非常盛行。陈澧《东塾跋欧阳文忠公文集》指出欧阳修对《易》、《十冀》、《周礼》、《中庸》、《春秋三传》都提出了怀疑,认为:“启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他的《诗本义》辨证毛《诗》、郑(玄)《笺》谬误的有一百一十多篇。”[12]
南宋的朱熹在治学论《诗》上深受欧阳修和郑樵的影响。在治《诗》上留下的辉煌的学术作品《诗集传》成了《诗经》宋学的脊梁, 到了明代,学风为之一变,理学家劝人不读书,名士劝人读小品文字,学者则劝人读奇书,除宋濂等个别之外,宋人疑古辨伪之风几为歇绝。到清代,尤其嘉庆以后,疑古精神又高涨起来。到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崔述发挥了他的极大的勇气加上沈潜三十年的功力,作了一部《考信录》,把战国、秦、汉间所说的上古、夏、商、西周以及孔子、孟子的事情全部考证了一下,无数伪史,又系统地说明了无数传说的演变,成为清代最伟大的疑古辨伪学者。正是治学思想的指引,才产生了《诗经》研究史上独具魅力的作品《读风偶识》。崔述的疑古辨伪的治学思想,追溯其最直接历史渊源,应该是朱熹,尤其他在治《诗》很多地方和朱熹是一脉相承的。
崔述的父亲一生崇信理学,在治《诗》上,尊崇朱熹的《诗集传》。刘师培在《崔述传》云:“父元森,治朱子之学。[13]”而崔述自幼又无师承,就学于他的父亲,崔述《考信录》做成之后,自己做了两卷《附录》,详叙他的家学渊源:“人之登显位享厚奉也,有崛起于寒微者,有蒙先世之业而得之者。其于学问也亦然。[汉]王充、[郑]康成,崛起者也,[汉]司马迁、班固、[晋]王隐、[唐]姚思廉、李延寿,则皆蒙业者也。”[14]他自己也认为是承袭了父亲的学业。他在《考信录》自序里提到的父亲教他的治经方法:“是崔述一生最得力的方法,这个法子实在是从朱熹得来的。[15]”可见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应该说是继承了朱熹。他的治《诗》反毛《序》而近朱《传》。
朱熹考辨《诗序》认为:“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讽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讽刺之,是甚么道理?”[16]
朱熹治《诗》,主张博采众说,“不用《诗序》,就诗论诗……间采三家,不拘门户……。[17]”杂集各家所长,博采同时代各学派学说,为朱熹研究《诗经》的一大特点,崔述在治《诗》上摒弃门户之见,杂采汉、宋,不正与之一脉相承吗?在治《诗》方法上,朱熹的着眼点在义理上,即是从思想内容上分析的,崔述则是用历史的观点,来检验它是否符合史实,朱《传》认为是“淫奔之诗”的个别篇目,崔述给予了否定,如在评《将仲子》时,朱《传》引郑樵的观点云:“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18]《读风偶识》则认为:然以此为淫奔之诗,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果奔女与?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其肯以“父母”“诸兄”“人言”自防闲乎?[19]他既不赞成《诗序》的“刺庄公”,也没赞成朱熹的淫奔说。在治《诗》上,认为朱熹有个别失误的地方,是受了汉儒的影响。尽管在治《诗》上,他和朱熹的着眼点不同,有一些篇目也批驳了朱熹的错误,但从《读风偶识》中还是能够明显看出他还是比较认可朱熹的。《考信录提要・释例》云:“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于汉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20]
综上所述,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崔述在治《诗》的指导思想和许多观点是承袭朱熹的。但可贵的是,他继承了朱熹的许多观点,但又不囿于朱熹的观点,有许多地方能超越朱熹的观点,显示了崔述独立治《诗》的原则。
可见崔述是十分有潜质的,因为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少时曾有志于功名,加上家庭的贫困和几遭水灾,他被逼上了谋官求生的道路,也曾参加科举考试,但崔述的疑古考信治学精神不受儒学传统笼罩下人们的欢迎,以一举人而终,三十岁后决计“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诬”,放弃了科举应仕。虽然科举考试将他排除在了荣耀和富有的士林阶层之外。但后来五十七岁的崔述赴京参加“大挑”,被选中,先后任罗源县令和上杭县令,任职期间,成绩卓越。他如果能够结交权势、投机钻营,凭借自己已有的政绩和学识完全有步步高升的机会。但是崔述一身正气,看透了官场的污浊,毅然辞职归田,潜心治学著书。在追求功名为士人唯一出路的年代,如果没有淡泊名利的思想他又怎能抛弃仕途,进行枯燥繁琐的古书辨伪工作。他也知道“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此外不复寓目”,但崔述能够忍受冷落,不管自己的学术有无承传(当时只有滇南的陈履和拜他为师),仍孜孜以求,正是这种淡泊名利的洒脱,才使他取得了这样突出的成就,在学派林立的《诗经》清学研究史上能独树一帜。
当然清朝浓厚的学术氛围也为崔述《诗》学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人都忙于著书,笔耕不辍,这对崔述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种推动,一种促进。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儒林传》之《列传二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页1327页.
[2]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2页.
[3]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遗书》)第16页.
[4]《孟子・万章》(《孟子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60年1月第一版,第25页.
[5]崔述《读风偶识》卷一之诗柄与诗文《遗书》第524页.
[6]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遗书》)第3页.
[7]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1页.
[8]崔述《考信录自序》(《遗书》)第920页.
[9]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遗书》)第955页.
[10]崔述《先君教述读书法》(《遗书》)第469-470页.
[11]崔述《先君教述读书法》(《遗书》)第470页.
[12]陈澧《东塾集・跋欧阳修文忠公集》(转引自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士》第207页.
[13]崔述《考信附录卷》(《遗书》)第465页.
[14]崔述《考信附录卷》(《遗书》)第465页.
[15]崔述《考信附录卷》(《遗书》)第465页.
[16]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17]崔述《考信附录卷》(《遗书》)第465页.
[18]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