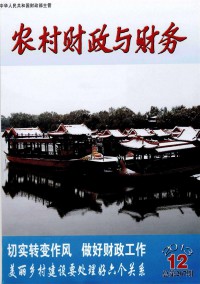三都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三都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三都赋范文第1篇
杜甫的三别指的是《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这三首诗歌。杜甫因为他的诗歌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疾苦而被称作“诗史”,“三吏三别”就是杜甫的代表作,记录了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动荡的历史。
《新婚别》是以新婚妻子的口吻来写的,昨天晚上夫妻新婚燕尔,今天丈夫就要去军中服役,劳燕分飞,妻子万分不舍,恨不得生死相随,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在家等待丈夫,“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塑造了一个极尽哀怨、却又深明大义的女子形象。
《无家别》描写的退伍归家的士兵再次被应征入伍,这首诗是以退伍士兵的口吻来写的,战争过后,家人都没有了消息,“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孑然一身却再次被县吏征召他去操练,他产生了无家可归的凄凉感,发出“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感慨。
《垂老别》讲的是老翁告别老妻,走上战场。老翁家的子孙们都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老翁觉得自己也无所谓了,可以走上战场,可是和妻子分别的时候,却发现,这一别可能就是生死之别,以后很难再相见了,“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来源:文章屋网 )
三都赋范文第2篇
三氟化氮有毒,属于低毒物质。
三氟化氮在常温下是一种无色、无臭、性质稳定的气体,是一种强氧化剂。三氟化氮在微电子工业中作为一种优良的等离子蚀刻气体,在离子蚀刻时裂解为活性氟离子,这些氟离子对硅和钨化合物,高纯三氟化氮具有优异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对氧化硅和硅),它在蚀刻时,在蚀刻物表面不留任何残留物,是非常良好的清洗剂,同时在芯片制造、高能激光器方面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三氟化氮的用途:
三氟化氮主要用途是用作氟化氢-氟化气高能化学激光器的氟源。三氟化氮是微电子工业中一种优良的等离子蚀刻气体,对硅和氮化硅蚀刻,采用三氟化氮比四氟化碳和四氟化碳与氧气的混合气体有更高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而且对表面无污染,尤其是在厚度小于1.5微米的集成电路材料的蚀刻中,三氟化氮具有非常优异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在被蚀刻物表面不留任何残留物,同时也是非常良好的清洗剂。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工业大规模的发展技术,它的需求量将日益增加。
(来源:文章屋网 )
三都赋范文第3篇
互联网的普及和深入使电子商务网站在近几年发展得异常火爆,各种礼品、化妆品、服装、数码产品等购物网站不断涌现,而圣诞、元旦、春节、元宵节、情人节等节日扎堆也让人们更倾向于网上购物来节省时间和精力。因此,我们可以预计的是,当春节假期来临时,各种电子商务网站,如淘宝、卓越、当当、京东商城等将面临巨大的网络系统压力。
想要应对访问量井喷的挑战其实并非难事,随着互联网基础服务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确保在访问高峰期也能让来访者获得良好的在线体验。
为网站全面“体检”
大量访客同时访问网站会对网站产生巨大压力,造成拥堵,导致网页打开速度缓慢,甚至无法打开等现象。大量访客可能因为网站访问速度过慢而终止访问,企业将因此损失销售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网站进行一次“体检”。
网站可以首先借助一些成熟的网站质量监测工具,如WebTrends、CNZZ等,对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载进行分析,查看各服务器负载是否均衡。如果负载差异较大,则可以将负载过高服务器上的流量分流至其他服务器上,这将解决一部分用户打开网页过慢或无法打开的情况。
其次,可以通过工具对宽带传输量提供相应的趋势分析,查看各时间段带宽使用情况。如果发现某一时段流量异常,则重点分析该时段访问网站IP中是否有产生异常流量的IP。例如某一IP请求数过高,通过对异常IP进行屏蔽就可以有效降低带宽占用情况,缓解网页打开速度过慢现象,甚至避免网页无法打开。
另外,对页面打开缓慢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像WebTrends这样的监测工具,用户能够观察网页打开过程中是否由于Flash、流媒体、Gif等文件而造成网页打开速度变慢。通常情况下网页上的Flash等富媒体文件不会对网页打开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访问量上升时,多访客同时打开一个网页,那么富媒体文件则有可能会占用过高网络资源。
最后,网站设计方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春节前夕网站的主色调应该是红色背景还是白色背景的问题。网站管理者需要关注在首页里应该放置哪些内容,哪些内容要重点推介,系统应该放置哪些连接,甚至考虑页面是否要设计成1024×768分辨率,是否要针对Firefox浏览器设计页面等。
做好压力测试
通过有效的访问行为分析,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网站的访问速度,不过对于像WebTrends、CNZZ这样的网站质量检测工具而言,它们主要通过网站日志分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网站的访问量、访问来源以及用户在网站停留的时间及路径,得出各种分析数据,而这只有用户成功访问才能够留下相应数据。反之,如果客户访问不成功,则网站内部根本无法拿到这些相应的数据。对于网站而言,他们可能更加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些用户不能够成功访问?他们不能够成功访问的因素是什么?
对于这种情况,国内类似阿里巴巴、淘宝、当当网这些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通常采用长期的网站性能质量监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应对圣诞、春节这些消费品购物黄金季节引起的大流量访问时,它们通常会提前进行网站的压力测试,选择全国各地庞大的真实用户基数,模拟用户访问时的行为及步骤,针对网站进行点击。在这个量化的过程中,客户可以知道自己网站在哪些方面较为薄弱,甚至是哪些区域的哪些运营商用户访问质量差,找出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提前检验网站自身的服务能力。
基调网络市场总监蒲炜告诉记者:“从互联网角度而言,有很多方面都是未知的,这源于中国互联网的庞大基数、众多的运营商复杂的网络环境。每一次大的流量访问到来时,既是机遇也是“灾难”,提前做出应对的公司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而没有做压力测试的网站往往会因为某些环节的问题,带来商业上的失败。”
这种基于用户真实访问行为的压力测试,与WebTrends等基于日志分析的网站质量监测产品,对于网站用户而言可以形成有效补充。一个是主动访问,一个是被动获得,两方面的数据进行结合,可以得出网站全方面的数据分析。
对于这种压力测试服务,其实还有一种应用方式,就是当电子商务类网站某个新产品上线,或者某个频道改版时,可以通过这种方面去验证产品的性能质量。因为网站内部进行的压力测试,往往并不能真实代表正式上线后的用户体验及产品表现,而这种通过真实客户端访问进行的压力测试,代表了普通用户的真实环境,这样客户可以在产品上线前,得到用户访问时的真实数据。以新浪为例,在近两年新浪博客的迅速发展下,动态Web 2.0的访问压力越来越大,新浪博客为应对各种新的应用,并兼顾客户的真实感受,在新的博客系统上线前,都会采取很多版本的压力测试,最终挑选出真实客户端感受效果最好的一种方案推到用户面前。这是一种值得各个网站借鉴的方法。
优化网络系统
对于网站用户而言,说到底其所有的应用都是靠服务器和网络平台来进行支撑的,因此对于这些网站用户而言,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优化改造,无疑也是应对挑战的一种好方法。就目前的网站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在机房部署负载均衡设备,优化电子商务网站的网络平台。负载均衡设备可以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优化IP应用
通过负载均衡优化器在多个本地和远程服务器间动态分配负载,为每个服务器分配一个可以配置的性能加权,从而提高服务器组的性能。
2.实现系统的冗余
对所有服务器资源的全程健康状况监视保证了关键任务应用和数据库的完全可访问性,并确保了完成交易所需的资源都是可用的。通过提供多级冗余,在不同站点上安装许多负载均衡设备,从而提供完全的站点冗余。如果整个站点发生故障,则备用站点将自动提供服务,确保整个服务可用。这样用户总能获得优质服务,网站也可以高枕无忧。
3.运用智能的服务器服务恢复
将重新启动的服务器应用到服务中时,避免新服务器因突然出现的流量冲击导致系统故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将新服务器引入服务器组时,好的负载均衡设备将逐渐地增加分配到服务器的流量,直至达到其完全的处理能力,从而保证用户不仅在服务器退出服务时,而且在服务器启动期间以及应用程序开始时,均能获得不间断服务。
三都赋范文第4篇
可是,目前复习课存在着许多怪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课堂教学层面。有的教师把复习课上成了新授课的重复课或习题课,每到复习时,常常是教师机械重复所学过的知识点,学生听得索然无味,昏昏欲睡,听课的效率不高,达不到复习的效果,白白地浪费时间。或者是第一课时教师发下试卷,学生做题,第二课时师生对答案,循环往复,大搞题海战术。二是教学研究层面。有的教师要去听某某教师的课,授课教师却以上复习课为由把听课教师“拒之门外”,觉得复习课没什么可听;还有我们许多教师也都不爱听复习课,觉得听复习课没什么收获……种种迹象均已表明,复习课教学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制约语文教学质量提高的瓶颈,改革传统复习课教学模式势在必行。为此,笔者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与同行的一些课堂实例,谈谈我认为的语文复习课的几个维度。
一、温度――优化教学设计,激起情绪波澜
大家知道,人体的正常体温在37℃左右,而人体适宜的温度正好是其中的黄金分割点,大概在22℃左右,就像秋高气爽的天气,22℃的温度对于人体是最为适宜的。课堂也应有它适宜的温度。
新课程倡导建构学习,注重学生的体验与学习兴趣,强调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改变课程实施过程中过分依赖课本、被动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所以在复习课的教学设计上绝不是简单罗列所学的知识点或举几个常见的类型题,同样需要唤醒兴趣,激起学生情绪的波澜。
复习课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知识点的梳理,如若只是要点的简单罗列,学生往往感觉枯燥乏味,味同嚼蜡。因此,复习课也同样要求我们创设丰富的情境,唤醒学生沉睡的记忆。如一教师通过颇具争议的“清明花50元就能为祖先扯一张‘阴间结婚证’”这一话题情境,唤醒了学生的兴趣,引起了学生的注意,使学生处于兴奋状态,与此同时,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复习了议论文现象与论点的区别,清晰地辨别了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的概念。
精心设计好课的开讲,做到一上课就紧紧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很快进入“最佳学习状态”,这是让课堂有温度的起点。
因此,教师在复习课教学中同样要重视实施唤醒教育,激发学生的兴趣,这样往往能使学生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从而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以高昂的情绪融入课堂教学。
二、适度――配置典型例题,作用解题过程
美酒饮至微醺止,好花开在半放时――适度了,人们品出了酒之美,赏出了花之好。复习课也应讲究适度之美,因为生命不是一个容器,它需要适度的“一呼一吸”。复习课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在重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挖掘和拓展,培养学生广泛联想的思维品质,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按照能体现本体裁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的原则,精选题组,进一步巩固复习内容,教给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环节中,教师首要的任务是选好例题,以一当十,力争做到“讲解例题典型化,基本题归类化”,对例题的教学,具体要求如下:
1.题目类型要精选。题目涉及的知识点要尽量覆盖复习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综合性,针对性、典型性、灵活性要强。
2.分析过程要强化。例题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解答结果,而是通过题目的解答过程为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原型和模式,教学中应重视题目分析过程的作用,引导学生思考题目特点,探索解题思路。
3.解题规律要总结。例题解答之后,要引导学生反思思考过程,总结解题的经验教训,对一些常用的阅读思想方法、解题策略要予以归纳概括,提示学生今后注意运用。
精心设计具有一定思维容量的思考题,联系自己的已有经验展开质疑、想象、推理等思维训练,并且保证学生有足够的阅读、思考、交流的时间,让学生能真正沉下心来专注地投入学习。复习教学要有大容量,但这里的大容量并不是指教学内容多多益善,训练内容满满当当,而是指阅读的容量、思维的容量、互动的容量要尽可能大些。
因此,教师在认真钻研教材,管理归类好知识点、能力点、德育点的前提下,准确地、概括地、简洁地对将要复习内容的重难点进行深入浅出的解剖,抓住关键,理出规律,拟成具有启发性的综合思考题,板书给学生,以形成知识的骨架和思维的阶梯,发挥“导”的作用,成就适度之美。
三、广度――综合拓展创新,发散学生思维
复习课的功能要着眼于“提高解决问题能力”之上,包括语文中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等,因而,可根据复习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不同类型的习题,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1.选择阅读理解题,以培养学生筛选信息、合理选择信息、提炼问题实质的能力。
2.选择开放性练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传统复习课提供给学生的大多是一些封闭性题目,思考空间小,思路狭窄,设置开放性练习,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不足。
3.选择探索性练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它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方法,经过不断尝试与探索后,找到问题的答案。
4.选择评价性阅读,以培养学生多元思维,取长补短的能力。要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允许同学之间有争论,创设一个自由、宽松、活泼的气氛,及时发现和克服学生的被动接受习惯、思维定势等思维障碍,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发展思维。逐步使学生实现由知识到技能再到交际能力的转化,从而达到运用的最高技能。
总之,语文复习课要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从传统教学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掌握,转向侧重于促进学生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习惯和态度的形成、学生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态度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它的教学目标更注重认知性和发展性的有机结合,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
1.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都赋范文第5篇
这一天的开始和寻常的日子没什么不同。早上6点过,四川省大竹县月华乡余家村,27岁的母亲唐成芳起身,来不及穿上外裤,便走到两个女儿床头,唤她们起床。
安排女儿吃完早饭,再抱着8个月的小儿子,送大女儿上小学,二女儿上幼儿园;回到家,一边照顾小儿子,一边做农活和家事,等女儿放学,再抱着儿子去接……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唐成芳的人生本应按照这样的顺序继续下去。
那天,两个女孩揉着睡眼来到堂屋桌前,桌上并没有妈妈准备的早饭。取而代之的,是一碗看上去既不像汤也不像饮料的液体。8岁的大女儿李春红已经懂事,她闻了闻碗,皱起了眉头……
大概几小时后,当春红从昏迷中醒来,从福州赶回来的父亲李合元焦急地问:“莽子妹,你晓得是药,为何要喝?”“妈妈把门锁上,使劲灌我们,我跑不了。”那一幕注定将成为这个小女孩一生的梦魇。
最早发现唐成芳家出事的,是和她家一墙之隔的妯娌饶朝琼。早上7点半,看到弟妹家仍家门紧闭,饶朝琼有些狐疑。平常这时,唐成芳已经把女儿送出门,开始照顾小儿子。
和唐成芳一样,饶朝琼也是个留守妇女,丈夫兄弟俩都在福州打工,妯娌俩平日相依生活,照顾两家的五个孩子。
饶朝琼拨打了唐成芳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李春红,“伯娘,妈妈给我们吃了药,她也边吃边吐。”饶朝琼忙让侄女把后门打开。眼前的一切吓得她不知所措:弟妹唐成芳表情痛苦,穿着秋裤、拖鞋,站在水池边剧烈呕吐,吐出来的液体呈蓝绿色。饶朝琼一下认出来,这是除草剂——百草枯,剧毒。二妹李水秀虚弱地倚在楼梯边上,八个月的婴儿李顺仕嘴边已经起了燎泡。“弟弟也吃了药。”李春红哭着说。
为什么为什么
坐在赶回重庆的飞机上,李合元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35岁的木工一下衰老了十年。他很生妻子唐成芳的气,鲜于对妻子说过一句重话的他,甚至想过见面先扇她一巴掌。可随着回忆一点一滴串联成线,李合元的愤怒和仇恨逐渐被沮丧和一种难以名状的悲痛所替代。
两天前,唐成芳就曾打电话向他哭闹:“我不想活了!”“怎么了嘛?没钱花了?我给你寄过去。”李合元好脾气地问。“不缺钱,不用寄。”唐成芳回答。对于像李合元这样模式的农村家庭来说,夫妻两地分居,丈夫在沿海打工,妻子在家照顾农活和老小,不就是为了多攒一点钱?
出事那天,唐成芳身边一共有380元钱,银行卡里还有1800元整。李合元牢牢记得这笔钱的具体数字。可妻子不是为了钱,那又是为什么?
三个重度中毒的子女被送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唐成芳则被警察监管着,住在距离孩子近30分钟车程的重医附一院。李合元除了照顾孩子,还要每天去看妻子。
“为什么干这个傻事?”李合元问唐成芳。“我活着很累。”“你干吗要给几个小孩也灌药?”“我死了,你带几个小孩也很累。”唐成芳轻声叹气,此后再没回答丈夫的任何问题。
4月9日那天,李合元正准备跨出病房门去签字,他下意识地回头,妻子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嘴里已经说不出话。
他冲过去抓住她的手,不断唤她的小名,唐成芳轻轻地捏了两下丈夫的手心,没有留下一句话,便永远阖上了眼睛。她那些不为人知的悔恨,懊恼,自卑,抑郁,悲伤,纠结,牵挂……也随之而去。
一对典型农村夫妻的历程
“已经有儿子了,也不缺钱,我告诉过她只管照顾孩子,我只管赚钱。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李合元像祥林嫂一样重复,亲人和村民也都不明白。
上世纪90年代,和大部分农村青年一样,李合元和哥哥一起外出打工。2003年,26岁的李合元在福州认识了在女衣厂打工的唐成芳。两人谈起恋爱,还办了酒。当年,李合元的父亲得了肺癌,唐成芳答应在家照顾公公,让丈夫出去打工赚医药费。
但李合元刚走两天,唐成芳就大哭大闹,喊头疼。李合元又急忙赶回来。医生说没问题,只开了止痛药。唐成芳背着丈夫把整瓶药吞了下去。李合元吓坏了,问她为什么,唐成芳说村里人骂她懒,李合元觉得她捕风捉影。
如果不是出了后来的这件大事,这段经历,李合元原本没放在心上。在村民印象中,李合元两口子的关系一直不错。有一年,李合元回来养了半年鸭子,唐成芳被玻璃割伤脚,李合元便每天背妻子去医院换药,坚持了半月。在农村,这就是恩爱夫妻最佳的表现。
李合元性子急,易冲动,和妻子却基本没吵过架。父亲去世后,他带着唐成芳继续外出打工,又回到了福州。2004年夏天,大女儿李春红出生。哪里赚钱多,李合元就到哪里去,唐成芳一路跟着,带孩子、洗衣做饭……2006年二女儿出生,李合元交不出罚款,便将孩子送了人。这跟唐成芳的童年经历如出一辙——因为家穷,她一出生便被父母送给了亲戚,直到17岁才认亲。
两口子一直想要个儿子,2007年,第三个孩子出生,还是个女儿。在唐成芳的坚持下,交了18000元罚款,这个被取名李水秀的孩子留了下来。2008年,大女儿被送到了当乡村教师的外公家,没读过书的夫妻俩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后来,小女儿也被送回老家,由嫂子代养。
2011年,第四个孩子出生,终于是梦寐以求的儿子。2012年春节前,唐成芳主动要求回老家,把三个孩子接到一起,自己抚养,“家里宽敞,开支小。”
唐成芳说这话时,距离出事仅两个月。李合元想不通,也是被理解的。
一个非典型农村妇女的生活
余家村距离重庆市区百余公里,李合元和唐成芳的家就在村口。从他们家沿公路左拐几十米,便是月华乡中心。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如果不种田带孩子,饶朝琼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这里,逛街、聊天、打麻将。
而唐成芳很难融入,邻居们拉她打麻将从不参与,买完东西就直接回家。村里面的人觉得她“内向得厉害”:有人请喝喜酒,她也不去,而让8岁的大女儿带着二女儿去。
但唐成芳的勤劳能干和对孩子的好,在村里却很出名。男人能干的农活,她都能干,自家的三层小楼收拾得井井有条。别人偶尔送她块饼,她也总是等到孩子放学后,留给她们吃。
唐成芳每天的作息规律,简单。晚上八点多就回屋休息。李合元购置的电视、音响,她几乎都不用。出事前几天,唐成芳闲下来就给女儿织毛衣。
余家村的留守妇女不算少,农活和家务都压在一个女人身上。像饶朝琼这样的女人懂得排遣,唐成芳却不会,她只会偶尔跟嫂子抱怨腰疼难过。
“我理解唐成芳的感受。”余家村村委会主任梁胜玉,丈夫有几年在外地教书。一次,她一人在田里喷农药,手被芦苇刮伤了,碰上农药钻心地疼。梁胜玉看着就在手边的农药,直想一口喝下去。
余家村村委会书记张真太介绍,余家村70%的青壮年男子都在外务工,三分之一的妻子都留守村中。这个趋势还在蔓延。留守妇女自杀事件,每年乡里都有一两起,但像唐成芳这样拉上孩子的,是头一宗。“我们也想解决留守儿童、留守母亲、空巢老人的问题,
但实际上很难。人力财力上都不可能实现成立‘留守妇女互助’这样的组织。”而在梁胜玉看来,留守妇女的苦闷只可能靠自己,“多跟朋友聊聊天儿”。
难解的后事
4月20日这天,记者在儿童医院肾脏免疫内科见到李合元父女四人,三个孩子那天刚做完复查。
8岁的大女儿李春红面无表情,盯着手里的图画本发呆。她的肝还有些肿,盆腔有积液,这个早熟的孩子怕多花钱,从不喊痛。“妈妈会不会坐牢?”她曾问过外公。“不会,妈妈好了还要照顾你们。”老人哄她。
老二李水秀的肺功能没有变好,也没恶化。她一会四处找寻零食,一会拿气球逗弟弟,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带来病房唯一的笑声。老三李顺仕,每天需要输近20小时的液,嘴边还起着燎泡,浑然不知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老大问妈妈最频繁,这几天却绝口不提。三个孩子都不知道,他们再也见不到那个灌他们喝农药的亲爱的妈妈。李合元蹲在楼梯间一支接一支抽烟,头发凌乱,双眼布满红丝。一些承诺的善款迟迟没有到位,除去他自己的钱和帮帮爱心网、月华乡政府已付的7万善款,他已经欠下15万元的医疗费。这个已经成为鳏夫的男人,现在只一心想着把孩子的命保住。
怎么告诉孩子妈妈的事,孩子将来的安排……李合元没有答案。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件难事,妻子的骨灰仍旧摆放在殡仪馆。娘家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再管。他想把妻子埋在老家屋后,又怕周围人说闲话刺激到三个孩子。他又想,要不等孩子大点懂事了再来处理,又怕他们责怪他没让妈妈入土为安。
链接 留守妇女相关数据
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历时两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她们成为家务、耕种和家庭养殖的主要劳动支柱,延续千年的“男耕女织”的乡村经济模式大多转变为“男工女耕”。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时间辅导子女学习,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使她们更容易患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
接近七成的丈夫每年外出务工达9至12个月,44.3%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而98%的留守妇女只能通过电话与丈夫联系,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的超过五分之一。
留守妇女的“孤独”情绪最为显著,有这种感受的人达63.2%,这种“孤独”的感觉不仅包含留守自身的苦楚,也源于独自承担家庭责任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