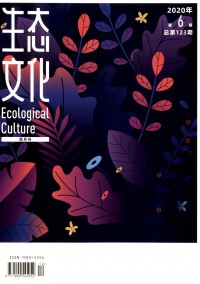以生态心理学为视点的考察探究

摘要:人在追寻自我过程中,一直疏漏了自然之维人,从而撕裂了人与自然间本源性联结,直至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才促逼人们回到原点重新反思自我,构建人与自然合一的生态自我。“生态自我”作为生态心理学的核心观念,在诗人于坚那里实现了对接,唤醒人们要拓展自我边界,建立人与自然间相互交融的生态自我。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于坚的诗;自我救赎;生态自我
一、自我检审:从与自然的隔离到融合
“自我”本是心理学概念,从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始就显示出自我与自然相隔离的特性。冯特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直接经验的科学,而直接经验是指自我主体能直接感受到的感觉、感情、意志等心理过程,对于外部世界的间接认知则排除在外。他既用经验替代心理,又用经验偷换客观事物,从而抹杀了人的心理与外在环境、事物的界限。[2]由此,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阻隔了个体自我与外在环境的联系,只注重被他成为心理元素的感情、感觉、意志等研究与分析。之后华生、斯金纳开创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则致力于心理学的科学化,努力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放弃人的心理和意识的研究,而把观察到的客观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此,华生把行为和引起行为的环境影响分析为两个刺激和反映共同要素,这样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心理活动,都由物理化学引起的变化而已,[3]究其实乃是对自我做科学化的分析,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继续沿着对心理做片面分析的路径,并将作为自我的人的心理分为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心理过程,对自我的复杂心理做简单化处理。心理学中的自我追问,之所以将自我与环境割裂开来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自从赫拉克利特提出“我寻找过我自己”之后,西方哲学便开始关注自我,苏格拉底指出要“认识你自己”,普罗太戈拉则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4]他们对自我的追寻旨在试图建立一种源自人的主体能动精神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的自我。但这种自我主体性的真正确立则是近代,其代表人物就是笛卡尔。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哲学命题,标志着真正确证起自我存在的实在性。在他之后,许多哲学家沿着他的“自我观”对自我进行进一步阐释。如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一切存在都是被自我所感知的存在,在自我感知的存在之外不存在独立的存在。康德说得更加直接,“人是自然的立法者。”[5]另外,费希特、黑格尔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自我的主体性地位。近代以来,自我通过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和哲学的逻辑推演,将人的自我主体实在性突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成为自然主宰,自然只是作为自我的异己而存在,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成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自然也就理所当然成为满足人类欲望和需要的存在场域,展示人类理智力量的载体,最终生态危机的引发也就成为必然。因此我们说生态危机,其根源乃是人的危机、自我危机,是自我意识中缺失自然参与构建引发的危机。而生态心理学的诞生也就成为时代精神的必然召唤,他们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到自我上来,努力建构生态式自我以拯救濒临危机的生态。他们认为“生态自我”就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是一种彼此共存、相互支撑的生命统一体。[6]“生态自我”作为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从认知上来说,生态自我是一种对生命相似性、关联性,以及对其他生命形式认同的认知;从情绪上来说就是一种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情感共鸣,即对其他人、其他物种、生态系统的同情、关怀、共情和归宿的感觉;在行为上就是一种像对待自身的小我一样去关注其他人、其他物种、生态系统健康的自发行为。[7]“生态自我”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崭新的自我面貌,在这样认知和行为规约下,自然不再是作为我们对象性的存在物而存在,而是将自然作为自我边界的延展,并参与作为自我内涵的道德、情感、伦理、价值观等的构建,从而促进自我成为一个回归生命本源的“原生”状态的人。生态心理学的生态自我观,给我们重新认识自身、认识自然、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界,更为我们从事文学的生态批判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界。于坚,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实践正给我们一个观照。
二、自我迷失:现象背后的理性批判
自我,在生态心理学语境下是生态式的自我,是对其他生命形式的认同,揭示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之间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或同一性,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更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然而,一旦在自我中剔除自然维度后,自然万物就成为人的一种对象性存在而走向对立面,此时,自然万物只是作为人的附属物而存在,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体现,是在人的命名状态下存在。就乌鸦而言,在生态自我视域中原本是与人具有相同生命意志的存在物,然而,一旦将乌鸦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乌鸦就不再是原本的乌鸦,而是人的乌鸦,同时人以命名方式将人的意志强加到乌鸦身上,最终剥夺其作为独立生命体的存在。然而,诗人于坚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8]中试图解构乌鸦,让乌鸦回到乌鸦位置。诗人写道:“当一只乌鸦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不是它的象征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只是一只乌鸦”,显然,诗人想给乌鸦去蔽,想把乌鸦从人强加给它的“象征”“隐喻”“神话”等主观意志中解救出来,告诫人们,它只是一只乌鸦,“在它的外面世界只是臆造”,也只有在摆脱人的命名后才能回到自身,让乌鸦回到乌鸦位置(挣脱人的命名),让人回到人的位置(即生态自我),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管它“飞得高些”还是“降得矮些”,始终是只乌鸦,是“一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而已”。然而,正是这只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存在的乌鸦,“可是当那一日我看见一只鸟……被天空灰色的绳子吊着/受难的双腿像木偶那样绷直。”诗人对人类这种漠视生命的行径表达了难以抑制的愤怒,虽试图将人类强加给乌鸦的种种话语隐喻进行解蔽、祛魅,让生命回归本身,然而,在自我中缺失自然参与的时代,乌鸦终归没有逃脱被人类以各种借口猎杀的命运。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诗人鞭策了人类的自私、冷酷与麻木,缺失对作为与人具有同样生命价值的乌鸦的生命认同感,同时也警示人类试图为乌鸦命名的徒劳,表明了人对乌鸦的命名不是对事物本源的切近,而是对生命的一种僭越、一种遮蔽。其实只要我们试图给事物命名并进行言说时,我们就离开了事物所固有的本来属性,而将我们人的意志强加给对象身上,成为人的言说而让对象本身缺席,同时也失去了对对象所本有的生命认同和体验。这种命名方式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自以为是的“闲谈”:“因为这种言说丧失了它和所谈的存在者本源性的在的关系,或者它根本就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它就不会以让这种在者被它享有的方式本源地传达,只能以人云亦云玩弄词藻的方式传达……闲谈即形成于这种人云亦云玩弄词藻的传达之中。……它甚至扩展到我们写的东西,在那时,它的形式是‘陈词滥调’。”这样的“陈词滥调”无疑“破坏了我们和事物本真的关系”。[9]人对乌鸦的命名,就是一种“陈词滥调”,它阻隔了人对乌鸦作为“在者”的本源性传达,阻隔了人与自然间天然的生命联系。即使这样,诗人仍坚守“生态自我”立场,解蔽命名,让物回归物,让物自身在场。海燕在高尔基那里被隐喻为一个冲破暴风雨的革命者形象,然而诗人在《赞美海鸥》中,却呼唤:“高尔基已死他的海燕已死那个二十年代的象征已死/死了旧世纪命名一只海鸥的方式/事实上只要把目光越过海鸥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另一类鸟。”在《鱼》中诗人则对人无情猎杀鱼的残冷行为进行了控诉:“后来它再也不动成为这次晚餐的一员/正像一条死鱼那样它躺在圆桌中间/周围是蓝色瓷器青铜汤勺另一些肉/以及端坐如仪的我们。”诗人从二元论的视角揭示了个体自我与自然万物的分离,也就是在自我建构中缺失自然维度的参与,并将自然万物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否定自然万物的生命意志,最终导致自我迷失。然而,人与自然万物原本具有同等生命意志,二者是在“要求生存”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这就是施韦泽指出的人要“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10]诗人于坚在批判自我与自然分裂的同时,正是在“敬畏生命”这一立场上试图取得自我与自然的和解,重构自我,生成生态式自我即生态自我,从而在自然万物身上剔除人的主观所赋予它们的意旨,进而让它们回到自身。
三、自我救赎:诗意生存的本源召唤
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不得不促逼人们施行拯救,拯救生态,拯救自然,为此就要从拯救自我开始,建立生态自我。生态自我的建立,不仅在认知层面上确立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观念,更要在情感层面上形成人与自然万物的心灵感应、情感体验,即生态体验。在生态心理学家看来,生态体验就是一种情感联结、生命认同,呼唤我们从物所处位置上看世界,体验物的情感,与物同悲同喜。此刻的自我已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而是生态自我。“当我们感觉到自我与他人、其他生命形式、生态系统或是整个地球的联系时,那就是在体验我们的生态自我。当我们感觉到一种与其他物种间深深的共鸣、一种归属性以及与更大的生态整体相联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体验生态自我。”[11]在诗人想象中,正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图景,是自我救赎后听命于人与自然本源召唤的诗意图景。他在《避雨之树》中为我们勾画了这幅生态自我式生存景观。诗中描绘了那棵高大榕树庇护下的一个人与万物友好相处、相亲互敬的世界。在树下,人仅仅是芸芸众生之一员,人与蛇、鼹鼠、蚂蚁、蝴蝶、鹰等都栖身大树之下,心中涌动的“这是来自母亲怀中的经验”,甚至“我们听到它在风中落叶的声音就热泪盈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爱它这感情与生俱来”。这种对大榕树的依恋已经不再是把榕树以及栖居榕树之下避雨的所有生命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将他们作为自我存在的“人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和生命体验从而将自我变成环境的一部分,同时,自然环境也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融合了人与自然万物间的隔离,重构人与自然万物间交融合一的生态自我。《避雨的树》为我们勾画了人类与自然万物诗意栖居的图景,那么在《一只蚂蚁躺在一颗棕榈树下》则将“诗人”与蚂蚁间的情感联结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把人与动物或者动物与人的情感联结展现出来。诗人写到:“一只蚂蚁躺在一颗棕榈树下/三叶草的吊床把它托在阴处”,蚂蚁怡然自得,轻松愉悦,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此刻的诗人不仅在蚂蚁身上看到自己,将自己的情感到蚂蚁身上,蚂蚁也变得像人一样,具有思想、具有情感,从而蚂蚁也“胡思乱想千奇百怪的念头”,而作者自己却“蹲下来看着它像一头巨大的猩猩/在柏林大学的某个座位望着爱因斯坦”,“我的耳朵是那么大它的声音是那么小/即使它解决了相对论这样的问题/我也无法知晓对于这个大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头猩猩”。在这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边界已经消解了,就如庄周梦蝶般,不知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此刻诗人与蚂蚁间已经达到“物我两忘”或“物我合一”的生态体验状态,正是这种体验式的生态自我达到了与其他人、其他物种、生物圈的共情、归属的感觉,在情感上,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溶解了。在《黑马》中诗人更是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诗人叙述了黑马像人一样有其自身生命意志,不仅如此,诗人笔下的大地和草木都具有了生命,同时都与“我”相互交融,我就是黑马,黑马就是我;我就是草,草就是我。诗人写道:“一匹黑马站在蔚蓝的天下”“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啃啮着那片荒原/当我眺望它时似乎我的生命/也成为它嘴下的青草”“只要它一跃而起/大地就会快乐地呻吟”“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啃啮着那片荒原/一动不动悠闲自在/而渴望驰骋的却是我/啊像一匹马那样驰骋/黑马你来看电视我来嚼草/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对我无动于衷”。诗人写得不动声色,浑然天成。我们看到人与马是平等的,都各有其“自在”,又有其在天下地上达成“共在”。这种在人与马之间,通过人与自然的联结,并没有将个体的自我迷失或俺没在自然之中,而是在与自然联结中重新找到自我,形成所有生命形式、生态系统和地球本身紧紧围绕在一起,规避环境伦理、道德律令,形成一种自我与环境、自我与他者的融合、渗透、共情的生命共同体。从生态心理学的“生态自我”核心观念考察于坚诗歌为我们解读文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窗,通过这个视窗,我们洞见人类的生态危机其根源乃是人的自身危机,是自我解构的危机,而于坚的诗正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确立生态自我提供参照,并唤醒我们要真正在心灵深处确立起生态自我的观念,为解除生态危机、开启人类生态文明新时代确立一条路径。
参考文献:
[1]吴建平.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8.
[2]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13-214.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8.
[4]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13.
[5]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93.
[6]朱建军,等.生态环境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33.
[7]吴建平.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47-148.
[8]于坚.于坚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8-92.(本文所选诗歌皆出自该书,以下不再标注)
[9]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62-78.
[10]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
[11]吴建平.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1.
作者:秦春 单位: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