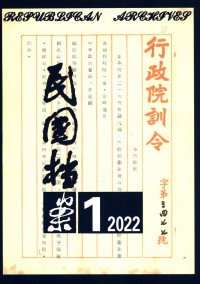民国初大公报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关切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混乱、府库空虚,军政各费仅靠各地解送中央的部分款项难以撑持。于是,举借外债、滥发内券成为政府偷渡难关的灵丹妙药(外债如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等;内债如民元6厘公债,发行定额2亿元,以全国的契约、印花税为担保,发行折扣为九二折[1])。值此财政捉襟见肘之情境,教育经费愈益面临枯竭的边缘,而仅有的教育经费或被他用,或化为军费,能实际用于教育的资金少之又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新闻媒体,《大公报》不可能对当时的教育现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是一秉“开风气,牖民智”[2]之宗旨,对教育经费问题阐发其宏识大义、灼见真知,为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顺畅,提供舆论准备,营造探讨氛围。
一、关注经费,牵系教育
(一)呼吁政府解决教育经费问题1914年,中央与地方互相告穷。皖赣粤军队,兵变猝起,“兵团冲突,交哄互诟”;[3]白朗起义,“横行中原,越郡跨州,如履无人之境”。[4]国家危机四伏,颓败丛生,而袁政府却挥霍甚夥,鲜有顾及教育。“就令教育事业,统通消灭,括其所有,曾不足供政府中人一瞬之挥霍”。同时,政府中某些人附和社会上废教育、复科举的风头,一意以摧残教育为“职志”。该报批评道:“夫天下断无无教育而可以立国之理,裁减教育费,以挪作他用,比之饮鸩,尤为危险”[5]。尽管袁世凯一意孤行,另有他谋,不可能为媒体的一时感慨而放慢其帝制自为的脚步。但《大公报》还是立足国家前途角度,从教育经费这个最现实、最基本的问题出发,阐发其对教育命运的担忧,尽力发挥着新闻媒体督促政府、呼率舆情的责任。1915年元旦,袁总统再出新招,发表新年“第一申令”,声称振兴教育为其施政之大端之一。于是乎,各地上书附和,条陈教育办法者,几乎无日无之,教育之发展似乎呈现兴旺之势。但现实却事与愿违,财政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百分之三,“因减政问题,又将减去其十之四,是综计不足百分之二,亦难乎其为振兴教育”[6]。就此问题,《大公报》及时发文,谴责当权者表面关心教育,实际克扣教育经费的伎俩,并用准确的数据揭穿了大总统“振兴教育”的假相。袁世凯死后,《大公报》继续关注教育发展的进程,提出振兴民国教育之“六端”,其中增加教育经费为其首端。该报认为,国家一年教育经费仅一千二百余万元,较之总支出尚不及百之三,平均每省教育费不及五十万,中等以上学校,几全取给于此。省各有中等学校约二十所,专门学校二三所,“维持现状,岌岌其难”[7]。所以,政府应调整政策,偏向教育。为了解决教育财政之难题,《大公报》力赞政府捐资兴学的主张,连篇报道相关事件或评述。然而,腐败的北洋政府常常使《大公报》的吁请化为乌有。1918年11月,持续三年多的“京钞”问题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币值下跌,投机盛行,交易停顿。尽管美、日两国借款支持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兑现,但由于两行在京、津地区的纸币流通量已达9700万元,京钞跌至六折左右,靠借款已无法弥补。[8]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京津之教育事业,成敷衍之势,“学款概须按成搭付,教员之修脯,因之亦按成折半,甚且有欠奉数月,并钞票亦无从领取者,加以各项公益义捐,官厅按名勒派,学界又无役不从。”教员无法枵腹从公,自然骛心他事,以求赡养身家,授课倍受影响。《大公报》撰文评述道:“减损教育经费,直接受困难者———教员,间接以致荒废者———青年之学业,而国家作养人才之前途,悉归徒劳无功,更不待言矣!”[9]《大公报》担忧学业荒废,人才受损,敦促政府亟谋“维持之方”,莫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否则,不但京师教育停滞,甚至全国的学校会“以款绌几陷于不能维持之境”[10],“国本既失,将焉图存”[11]?但在当时,军阀“政府之言不顾行,已数见不鲜”,面对媒体质问,只能装聋作哑,闭目塞听,听之任之,失信于民。故而,《大公报》只能发出“政府已完全失郤维持教育之能力”[12]的哀叹。
(二)谴责军阀挪用教育经费的行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库款万绌,外债日多,险象日现,几濒于危,而推究支出之巨,实以军费为大端”。[13]这种“大端”正如《大公报》撰文所言:“先战有军备”之费,“将战有军需”之费,“既战有军队善后之款”,“解散也需费,留养也亦需费”,军事费用如此之多,教育经费无从着落也就不足为怪。既然政府如此重视军事费用,国家之重心、国民关注之焦点必定以军事为指针,正所谓“举国注意于战事,即举国无心于教育”,[14]民国教育的发展前途由此而知。然而,好人愿意做,钱却不愿出。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各个军阀都声称教育为立国之重要因素,都口称要振兴教育,但每每涉及教育之具体措施,则一概抱怨“财政支绌,进行为难”[15],其根本原因就是,从中央到各省,凡握有兵权、财权之大僚,都把“撙节学校,以资军饷”作为公同抱定的惟一宗旨。《大公报》分析时事,有感抒怀,认为军饷固属于“弭患求安”之道,关系军队哗变,不得迟缓。“但国家支出项下,掷金虚牝者比比而是,何事不可稍加撙节?而独于至微极薄之教育费,节之又节,以至于无可节之中,亦必强令撙节,窥其意若非消灭教育不止者,果何为也?”显然,《大公报》采取退避三舍的分析方法,明白告诉世人,即使把当时最为头疼的军费割其在外,阻挠教育经费顺利到位的因素也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国家各项经费开支都能顾及,却唯独让经费甚少的教育再作“撙节”。殊不知,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环节,“国家之元气在人才,人才之根基在学校。今乃取学校养命之源,一切剥削之,以供养其所畏之军人,岂以为将才既欲,遂无庸更植人才乎?”[16]。重视教育已徒具虚名,国家未来岌岌可危。《大公报》从教育﹑人才﹑强国三者之间的联系,抨击军费的膨胀,分析教育经费的重要性,感慨教育前途之渺茫,其做法是可取的。袁世凯既死,北洋军阀派系纷争,军务繁兴,各省经济困难,原来之教育也渐趋停办,教育费用越来越多地被挪用于军费。《大公报》希望各省官员,“将各该省之教育事业为根本之培植,勿徒以官样文章塞责了事”[17],呼吁官员们应为教育前途,为国家前途做出实际举动,勿以表面形象敷衍塞责。随着军阀专权的进一步强化,全国各行政部门都惟军阀之马首是瞻。1919年4月,传闻教育总长傅增湘为了维持教育经费,拟向美国借美金50万元,恐怕以唐绍仪为首的南方代表反对,特致电疏通。《大公报》获此消息后异常愤慨,特撰社评批评,认为教育外债应由财政总长出面。即使教育总长出面借债,也只能向国会请求,元首裁断,而如今教育总长却惟南方军阀马首是瞻,“竟乞怜于南方代表,求其赞成。”[18]显然有失教育之社会地位,是中国教育发展之悲哀。事实上,《大公报》无论是对教育经费举借外债的痛心,还是对财政总长失职、教育总长尴尬的无奈,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公报》未能认识到在军阀横行的年月,所谓国会、元首都是空头上司,真正的老板是军阀。没有军阀的恩准,国会、元首也奈教育经费不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经济实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自行其是。《大公报》以教育救国的心态,简单地认为教育可以决定一切。岂知在军阀专横时期,这样的认识也只能是一个“认识”而已,难以成为现实。1921年,当局曾拟裁撤经济调查局,或者举办房捐来解决教育费用的危机,甚至还有人主张移用交通部或财政部之款来筹办教育基金。《大公报》认为,这些措施皆不可靠,因为交通部款项已被叶恭绰严词拒绝,财政部也表示无能为力;而“经济调查局为政府豢养议员之地,岂至今日始知其应裁?兼之为时局关系,利用议员者正多,顾恝然去之乎?举办房捐,虽似可靠,而接济在一时,吾民担负在永久,恐亦非所以维持教育之道。”因此,这些建议或措施仍然如同指雁为羹,充饥画饼。况且今天财政困迫、教育停辍的真实原因是“虚靡国帑者,大有人在。”政府对此类人百般无奈,不能裁撤。《大公报》所说的“虚靡国帑者”,就是军阀和一些当权者,他们花天酒地,奢侈堕落,成为教育经费落实的最大障碍。如果能顺利裁撤,当然利于教育的发展。但当时的中央“威信废堕”,裁减闲散部门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举办教育更是瞻前顾后,尴尬不前,“信用久失,每不能言行相顾”[19]。所以,无论是房捐还是所得税,常常徒托空言,难以付诸行动。正是由于军阀政府对教育经费“口言维持,实则漠视勿问”[20]的消极态度,也源于军费“此索若干万,彼索若干万,无不有求必应”[21]的奇怪现实,20世纪20年的中国教育界学潮不断,纷扰难平。在《大公报》的视野中,中国教育界真是一片荒凉与颓废,“时局纷扰,干戈遍地,天灾流行,荒象纷呈,……财政艰窘,开源乏术,是谓财荒;各校职教员复职无期,任令弦诵久辍,是谓学荒”[22]兵荒、财荒、学荒层层叠叠,中国大地一片荒像。《大公报》的描述不无夸张之辞,但兵荒一项,可谓万恶之源。正是由于兵荒,中央财政才异常拮据,直奉战争爆发时,中央每月收入不足100万元,而预计所需之行政费、军费却高达350万元[23]。因此,像教育这样的政治弱能儿,往往被当政者“视为赘疣之物”[24],“往往经年累月,不得一钱”[25],于是学潮愈演愈烈,无怪乎《大公报》悲叹,“教育之成绩,亦遂一落千丈”,[26]然而,这样的悲叹在“文官武将,各以保守地位”[27]的情势下,显得太弱小。不过,《大公报》对政府敷衍教育﹑唯诺于军阀的态度的指责无疑是值得称颂的。
(三)吁请政府关怀普通教育经费除去京城院校的教育经费,《大公报》也很关心地方学校的经费问题。该报认为,无论是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学风之优劣、办学成效等都与教育经费密切相关。对于前两者,“苟经费短绌,其为增为减”,地方官无能为力;对于后两者,“无经费而办学堂,其结果必至与前清无异”[28]。所以,《大公报》主张既然政府以教育作为考察地方官办学考成之条例,经费问题就必须是考虑的首要问题。教育经费付之阙如,教育将一事无成,则奖惩办法也将徒劳无功。概而言之,《大公报》关于地方教育经费的观点如下:其一,小学经费需求少,应该早日解决。《大公报》在将小学和大学对比后,认为“小学之设备,其需款亦复甚轻,非若大学、高等专门、师范之难于组织”,[29]因此,各地小学经费出不起,而存在“借费”心理,该报认为“令人费解”。《大公报》呼吁当局不要把小学教育“视为可缓之图而专以减少教育经费为得计”。[30]小学教育是人生教育中最基础的教育,轻视小学教育,势必影响学生一生教育前程的发展。《大公报》重视基础教育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其二,重视强迫教育问题,鞭挞政府的挥霍无度。民国初年,强迫教育问题日益被提上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议事日程。1913年,湖北省教育司为普及教育,造就共和人才,实行强迫教育,“以联络警界调查各区域幼年儿童,不论贫富,凡年逾七岁不入学者,一经查出或被人告发,加罪其父母。”[31]就此事件,《大公报》发表文章认为,强迫教育是世界通行之制,有利于中国国力之强盛,“苟不实行强迫教育,则优劣相形,未免见绌,不特不能竞存于彭湃之潮流,抑先无以巩固其富强之基础也。”[32]这就说明,强迫教育对于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意义重大。随后,该报提出强迫教育成败的基础条件———经费问题。因为当时的名流贤士每每谈论教育之重要,经费问题常常使他们束手无策,《大公报》不失时机地发表讽刺性文章,阐发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大公报》批评当局不顾社会现实,盲目惩罚学生父母,必将徒劳无功;第二,讽刺性地建议那些“不学无术尸位素餐”[33]之辈,应该进入某一补习学校,补其作事任事之能力,化废料为有用之人,这其实是一种有意义的强迫教育;第三,没收不学无术者的“分利”,将其捐给各地方办教育,这也是真正“强迫”教育一部分,比强迫无钱的父母更有成效。今天看来,这些建议无异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在军阀横行的年月,此类建议确实难以兑现,但此类文章对当时贫民无钱上学、官僚腐化挥霍的现实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揭露。其三,褒扬议员的政治行为。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众议院中有人提出,在官产收入内,划分五成专备地方教育之用。《大公报》对此消息颇感欣慰,赞叹道,“此后地方教育既有的款,则办理不致为难,学务可日见发达。此非仅惠及青年也,揆诸作养人才之道,新民德强国本,胥于是乎基之。”其实,议员仅仅提及地方教育经费的问题,离具体实施的日子还遥不可待,但毕竟有这种星星之光,总能给人以希望之火。所以,不管这笔经费是否能落到实处,该报都表现出了欣喜和盼望之情。另外,《大公报》对地方官将庙产充捐、山荒充学、绅士解囊等慷慨助学行为也极力予以赞扬,认为其“舍财兴学,与舍生救众同一宗旨”[34],对于借此机会敲剥吸髓,敛财肥己,“朦(蒙)蔽官厅,巧立名目”[35]之官吏,建议地方官,“宜通盘筹算,酌播的款,上以杜不肖官吏之巧立名目,下以免贫苦小民之增重负担”[35]。
二、督率舆情,建言献策
(一)借助舆论力量抑制军费民国初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各种保护教育经费的措施,如1913年11月3日,“教育部通咨各省,教育经费不得挪作别用。”[37]1915年1月22日,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亦称学务纲要),其中第五项规定:“各地方固有学款,宜分别保存,不得移作他用”。[38]1919年,教育部拟定全国教育计划书,对于教育经费之筹措,亦有详尽说明。但由于国家局势动荡,这些措施很难落到实处。甚至因为军阀势力的阻挠,教育经费大多被挪为军费,如1913、1914、1916年,军费预算数分别为16377万余元、13115万余元、14225万余元;[39]而同样是这三年,教育预算费却分别只有690.8850万元、327.6904万元、1283.7307万元。[40]军费与教育费之比相差悬殊。作为媒体,《大公报》试图利用舆论力量,压制学费转为军费的歪风。当时,直隶省因为临近京畿,获得教育经费较他省似乎更为便利,但在1922年直奉战争前夕,该省政府拟将教育费挪作军费。《大公报》撰文认为,“处今时势,如欲制胜他人,首须尊重舆论,绝不能专恃武力取胜也。今因军事,遽将教育停止,必失学生之同情,受舆论之攻击,其不能取胜也必矣。”《大公报》首先说明舆论在社会生活、国家运行中的重要性,然后就此批评该项举动“未为得策”[41]。变相指责军阀政府转化教育费为军费的罪恶行径。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意在以黎为过渡,再拥曹为总统。黎元洪虽然无实权,是直系军阀手中的玩偶,但他仍然顶住压力,宣布暂不支薪俸,以应得之款,尽数拨充京师各校以作学校经费。而曹、吴为了蒙蔽国人视听,也只好宣称教育为兴国之必要事务。虽然军阀的言行只是为敷衍舆论而做的“形象工程”,但《大公报》仍然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对三人之宣言作了耐人寻味的评价:我国自古“尊重教育,轻视武备,以故文学优良,人才称盛。洎乎民国,兵队充斥,军阀专横,教育经费,胥为军阀所劫夺。而教育一端,遂一蹶不复振”。说明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缺少的原因。随后,该报继续评论道:如今各大军阀“亦知仰承黄陂尊重教育之至意,赞成裁兵废督,以撙节之款,教育人才,殆亦为潮流所趋,不得不尔耶!”。很明显,该报既感谢了大总统的一番好意,又说明军阀尊重教育为不得已之举,是潮流之所趋。语气显然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为了督促军阀能言必行、行必果,该报最后说,“彼军阀等,是否真有觉悟,吾不得知。愿全国人士,既已深恶痛恨夫军阀之专横,而视振兴教育,为当今刻不容缓之举。”“各军阀虽仍不觉悟,绝不能与潮流相抗,而与我全国之人为敌也,则是军阀之末日,即我国教育振兴之动机,而谓今日已届军阀之末日,亦无不可也。”[42]《大公报》抛出最后的杀手锏,如果军阀不实践自己的承诺,幡然省悟,与“振兴教育”的潮流相抗,就是与全国人民为敌,就是其末日的到来。《大公报》的评论未必能制止军阀的劣行,但总可以表明自己对教育经费一贯支持的态度。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振兴的重要途径,该报不遗余力地关注教育,说明该报对教育兴国立场的坚持不懈。当然,军阀政府再次食言。1922年9月,各校教职员之欠薪仍无着落。直接导致了各校教职员和学生的直接抗议。1922年9月10日,各校教职员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有40多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声讨当局的欺骗行为,一些著名记者如《京报》记者邵飘萍、《晨报》记者林仲易等都表示支持。邵飘萍表示“决计援助”教职员的要求,点名教育经费短缺,让学生进入“外人经营之教会或学校,伏将来最危险之祸机。”[43]直接点明中国教育受外国教育威胁的险恶情状。这些都说明,当时媒体的态度是倾向教师一边的。与此同时,各校学生团体也组织学生开展读书运动,抗议军阀出尔反尔的行为。该报认为,学生之读书运动,“非运动教员及时上课,乃要求政府速筹学校经费耳。盖学校既有经费,则教员之目的已达,自必照常上课,不然,则虽勉强上课,而枵腹从公,终难持久”。所以,希望政府“不欲维持教育则已,如仍有维持之意,自当赶筹款项,先将教育经费发出,不得再以欺骗教职员术而复施之于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亦当体谅政府之苦衷,稍得经费,即当照常上课,不宜为过甚之举,致贻误青年学子之学业也!”[44]这些评论,虽然对政府和教师都提出了要求,但总的趋向是偏向教师的。因为该报是在提出教师苦衷、批评政府的行为后,才对教师提出“适可而止”的要求,虽然其中带有妥协折中的味道,但毕竟体现了《大公报》从整个教育利益出发而关注教育现状的姿态。在军阀当权、危机重重的民国初年,这也可以说是媒体对于政府的无可奈何之举。1922年11月,政府对8校工资问题仍迟疑不决,只知一味“交欢”各派军阀,而置无数之青年学业于不顾。“似有食言而肥之意”。该报认为,“政府之言不顾行,已数见不鲜”,但教育为国家最要之一端,“京师又为首都之所在,全国有志之青年,莫不归纳于此,其教育宜若何重要”,军阀却漠然视之,熟视无睹,必将影响全国教育。进而该报直接揭露军阀的行径不啻于摧残教育。《大公报》质:“夫中央财政之困难,至于今日,盖已无以复加。今政府对于京师各校之经费,舍关税外,试问尚有他道焉否耶?既不肯拨交关税,又无他道可资接济,则是政府已完全失郤维持教育之能力矣!吾不知国家之有政府,又果何用也!”显然,《大公报》寄望政府拨发教育经费的念头已经丧失,因此发出如此绝望甚至谩骂的论调,反映出媒体对教育现状的忍耐度即将到达极限。从深层次而言,这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状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本身阶级的局限性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关注民生、效力国家的能力大受限制,它对社会的支持力度是很有限的。《大公报》是民族资产阶级办的一张大报,尽管影响很广,但不可能脱离上述局限,因而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枝枝节节的舆论工作。因此,我们看到,该报接着就把视角转到教会学校身上,认为中国政府“既无款项兴学,则莘莘学子,必仍投教会学校而后已。是故教会学校,若雷厉风行,收束学生之身心,眼前虽或不免稍受打击,而终之必获胜利也。”[45]教会学校本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育机构,从本民族角度而言,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我们是不会把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外来机构身上的。该报把中国教育希望转向教会学校这一点也说明当时中国政府对教育之发展黔驴技穷无计可施。而且《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其时也在创办教会学校,该报的这种说法难免有夸奖英氏的嫌疑。但无论为何,该报对政府无视教育经费的谴责还是值得肯定的。总之,《大公报》能从客观的角度批评政府和军阀对教育的忽视和干扰,尤其是把主要责罚对象瞄准了军阀,希望通过各界舆论给当权者造成一种压力,抑或能使军阀恻隐大发。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军阀战争仍在继续,教育仍然身处困境。《大公报》的希望的一次次落空再次证明,在军阀专制的淫威之下,教育要想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是不可能的。
(二)借助庚子退款抒发报业情怀虽然《大公报》的呼吁雷声大雨点小,振兴教育的希望渺而又茫,但该报从来没有放弃呼吁,而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只要有机会,该报就抓住时机,奔走呼喊,制造舆论。1918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身份,与陈独秀、夏元溧、黄炎培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呼吁各界借助欧战之后有利的国际环境,敦促各国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于是,社会上掀起退款兴学运动,但直到华盛顿会议召开,法国国务总理白理安才声明:“至民国十年十二月四日”,法国愿将赔款的“小部分为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46]1920年,北洋政府欲筹建西南大学,计划将来使用国人力争而尚未到位的法国退还赔款。对此,几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曾认为,这些行为是“确立教育独立的基础———教育独立的第一义,使教育经费完全独立,可以按月支用,不受任何方面的牵制”。[47]而当时情况,则正如《大公报》所揭露的:款项未到,军阀已虎视眈眈,“四方罗掘”,“直欲攫取”,所谓振兴教育,“不过如画饼望梅,聊慰饥渴而已”,[48]与其主旨南辕北辙。故而,《大公报》对军阀政府利用庚款办教育的诺言心存芥蒂,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和猜测。1922年7月,英国有归还中国庚子赔款之意,但由于英国国会改选,内阁更迭,使退款进程横生枝节,几经跌宕。敌视中国的新闻记者朴兰德,经常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他致函伦敦《泰晤士报》,说中国政府“对于军备上,较之教育,每岁所挥霍者,实有数倍之多。英国政府近因减政之设施,对于学款,亦极事节缩。是故英国对于庚子赔款,殊无退还中国补助中国教育费之必要也”[49]。诚然,在那样的年代,中国政府预算中军费多于教育费是事实所在,但借此口实而反对退还庚款却是令全体中国人恼恨的行为。《大公报》无论如何都从民族利益出发,发表愤慨的文章,一方面否认中国将庚款用于军费;另一方面也驳斥了朴兰德阻挠退款的无耻谰言。同时声明,朴氏对中国的理解有失偏颇,其结论成见甚深,号召了解中国的英国人一起揭露朴氏的谎言。《大公报》的希望和做法未必切合当时实际,至于通过一家之言影响政府间决策的策略更是如水中月、镜中花。但其极力要求退回庚款的要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态度却在情理之中。之后,在确知英国不退庚款之意后,该报开始责备军阀政府的腐败与妥协行为,并且以美国退款为例,证明军阀的政治内讧是造成英国退款失败的原因。文章说,自从美国把退还庚款改充留学经费后,我国“游学彼邦者,络绎不绝,人才辈出,成绩斐然。”假使我国当局“彼时能援照美国先例,要求各国,一律退还,拨充教育经费”,各国亦必“顾全友谊,慨然应允”,“乃当局诸公,只知争夺个人权利,曾无丝毫振兴教育之心,以至因循贻误,丧失权利不少,直至我国加入战团,各国始允缓付五年,然仍未达到退还之目的也。”当然,《大公报》满怀帝国主义国家会顾全友谊而大发善心的心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它首先站在民族立场,要求英国退还庚款,批评军阀延误时机。这反映了《大公报》既注重媒体督促的策略问题,也注意报纸监督的方向问题。尽管有失当之处,但大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帝国主义拒退庚款的原因很多,如果仅仅把原因归结为争权夺利的缘故,则太简单化了。这也正说明《大公报》在认识上之肤浅和迂陋。
三、结语
民国教育史大家陈青之说:“除了社会达到了真正平等或吾人所理想的大同时代,教育不会有纯洁意义的。”[50]民国初年,政局不稳,军阀擅权,教育官员形同傀儡,中国教育真正意义上之进步是不可能的。然而,《大公报》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办理的一份私人大报,其利用舆论力量,力求促成中国教育发展之观点,则是较为可取的。虽然,由于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问题,使其在认识国情、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上还不成熟,甚至错误诸多;它的幻想诸如期待军阀产生怜悯之心而关注教育前途等也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是,作为新闻媒体,该报不厌其烦地对教育经费问题做追踪报道,提出自己的建议,阐明自己的主张,已经尽到了媒体应有的责任,其期望中国教育发展的殷殷情谊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