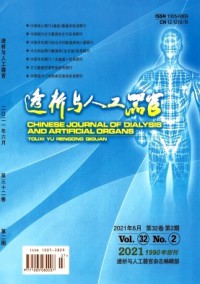透析新时代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对策

【内容提要】以新时期初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传播策略的考察,指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语境下,为达到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与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颉颃互竞,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获取了意识形态与启蒙主义的双重合法性,从而推进了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
关键字:文学、传播、策略
Abstract:intheneweratothebeginningofWesternliteratureexistsforthedisseminationofresearchthroughitsstrategyforthedisseminationofthestudy,pointedoutthatatthetimeofaspecificsocialcontextofthinking,fordisseminationtoachievethepurposeoftheexistenceofliterature,ChineseintellectualsstartedIdeologyanddiscourseoftheEnlightenmentandtheantagonismamongcompetingfortheexistenceofliteratureaccesstothespreadoftheideologyoftheEnlightenment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⑦这番言论发表在萨特逝世后不久,颇有为萨特盖棺定论的意味。不过柳鸣九的分析,使萨特的“倾向性文学”变成了一种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战斗文学,而其真正内涵却被深深遮蔽。事实上,有关外部世界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侧面,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演绎才是萨特等人的创作旨归。在萨特的创作中,作家不仅书写着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还细腻描绘了笔下人物遭受现实异化的生存图景。他对人类恶心式生存体验的叙述,对人类摆脱自在生存方式后向自为境地进发的英勇举动,都倾注了远比政治斗争更大的热情。所谓的“倾向性文学”或“战斗文学”,其实质都与人类脱离存在困境的精神苦斗密切相关。柳鸣九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出于某种传播策略的需要,他不惜以误读存在主义文学为代价,希冀通过对萨特的政治解读来推进存在主义文学的广泛传播。由此引发的一个传播现象,便是语言游戏的大行其道:利用新时期初相对含混和自由的语义空间,中国知识分子凭借有意误读的传播策略,将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并于此过程中逐步完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知识合法化。在新时期初的政治格局中,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去衡量,大部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都不够合格,甚至有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因其阶级属性而被意识形态目为“反动”作家。因此,介绍哪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就不再是一个介绍者的个人兴趣问题,它还关涉到介绍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在经历了“”腥风血雨之后,对于政治运动的恐惧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时,往往侧重于介绍那些在政治立场上与无产阶级作家较为接近的现代主义作家。但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大多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而非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的政治立场。
二、在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利用人道主义思想潮流,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传播策略。而这一传播策略的实质,就是为存在主义文学寻求启蒙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
由于人道主义作为新时期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当时启蒙主义的具体倾向。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具有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层面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启蒙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1979、1980年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为人道主义思想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据,当时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提法充分反映了这场讨论的思想实质。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启蒙合法性之外,使其加入到争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思想潮流中。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业已意识到了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是何等重要,他们通过一系列阐释,最终证明了传播存在主义文学不仅可以迎合思想启蒙的需要,同时还能间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根基。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中,存在主义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人道主义性质?而启蒙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又将如何获得?
1980年,《外国文艺》登载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⑧一文。该文标志着存在主义也加入了当时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在这篇文章中,萨特批判了一切对于人的先验设定,认为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在萨特的解释中,存在主义由于对人类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强调,认为“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而是一种“人道主义”⑨。由于这一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锋芒直指“”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迷信。因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被介绍进来,便成为新时期初启蒙思想者的有力武器。
与此同时,为强化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中国知识分子还以简化存在主义的方式彰显其人道主义品格,如以“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核心命题概括存在主义,认为“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大大优越于那种怠惰寄生的哲学和依靠神仙皇帝的消极处世态度;它把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作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也有助于人为获得优秀的本质而做出主观的努力,为这些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这就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⑩。这段评论中提及的“命定论”和“宿命论”,正是“”阶级决定论和血统论的另一种表达。因此,肯定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论和“自由选择”论,就意味着存在主义文学具有反对“”阶级决定论和血统论的人道主义属性。在这个角度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提法本身就具有启蒙功能。事实证明,惟有
九充分肯定了萨特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尽管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用存在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但“总的说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赞赏和向往的,这就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超脱了狭隘阶级局限性的思想家的风度”②。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为评价其政治立场的思想基础,显然有利于论证萨特的政治正确。而柳鸣九认为萨特“超脱了狭隘阶级局限性”的观点则语带双关:一面固然是以超越阶级分野的标准淡化萨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身份,另一面实则借此暗讽“”阶级决定论的思想流毒。
作为造成中国当代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根源,阶级决定论及其附属的血统论思想无疑是新时期初思想启蒙运动的批判标靶,它不仅阻碍了社会平等和公义的实现,也在客观程度上影响了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按阶级决定论的标准衡量,由于存在主义文学诞生于西方社会,因而也被归入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柳鸣九高度评价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便具有了批判阶级决定论的启蒙意义。因为萨特的例子说明,即使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也有超越狭隘阶级局限性的进步思想家。柳鸣九实际上在肯定萨特政治立场的同时,间接否定了阶级决定论所标榜的普世倾向。这一做法无疑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赋予了一种启蒙色彩。倘若细加追究,又可从柳鸣九的传播策略中一睹新时期初意识形态与启蒙话语的共谋关系。一般说来,作为倡扬理性思想、反对权威的启蒙主义,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但在新时期初的中国大陆,由于意识形态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转向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因而与追求社会平等和公义的启蒙话语不谋而合,由此自然形成了意识形态与启蒙话语的历史共谋。在此思想语境下,柳鸣九解读存在主义作家政治立场的传播策略便具有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关注存在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而柳鸣九对于萨特政治立场的启蒙主义解读,则是思想启蒙运动的自然回应。这一做法尽管看似矛盾,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共谋关系的存在,柳鸣九才会在不触及意识形态权威的前提下,推进了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由此也可看出,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共谋关系,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传播存在主义文学创造了一个相对含混和自由的语义空间,而且也为传播者们的过度阐释创造了便利条件。
实际上,为达到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目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这一文学流派时都有意对其进行了过度阐释。如柳鸣九在论证萨特的政治正确时,就有意回避了影响萨特政治立场取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品性。通过解读萨特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柳鸣九认为萨特“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反动资产阶级的非正义和罪行的抗议者,是被压迫和被迫害者的朋友,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是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抗议者”③。而且萨特的“政治履历表”“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精神和任自己的感情真挚地流露而不加矫饰和伪装的襟怀坦白的政治风格”④。这种政治风格充分说明了萨特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有鉴于此,柳鸣九认为萨特“要求作家用文学来为战斗行动服务”的“倾向性的文学”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即便《肮脏的手》等对无产阶级政党存有“某种偏见”的作品,亦不足以掩盖萨特作为一位进步作家的历史事实。从这一观点出发,柳鸣九认为萨特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进步的政治立场:如“剧本《死无葬身之地》(1946)表现被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的游击队员威武不屈的英雄主义,《毕恭毕敬的妓女》(1947)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涅克拉索夫》(1956)对法国反动势力进行了讽刺,《阿尔托纳的隐藏者》(1960)抨击了法西斯的残余势力”,等等⑤。由柳鸣九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的分析中,不仅可见某种过度阐释的思维逻辑,亦可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引进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的良苦用心。尽管柳鸣九在介绍萨特的政治活动时尚不失客观态度,但在解释其政治表现的历史原因时却有失偏颇。因为在柳鸣九的政治阐释下,萨特所有反抗强暴的政治活动均来自其进步的政治立场,而促成萨特反抗**、不畏强暴的精神动力则付之阙如。萨特曾经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他所具有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感才是引发作家所有抗争行为的精神动力。这份源自公共知识分子品性的反抗冲动,其实远比作家的政治立场更能说明问题。但为论证存在主义作家政治立场的进步性,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采用了“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实用主义策略,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人性良知等个人话语转化为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话语。这种阐释方式在确认存在主义作家政治正确的同时,也为其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获取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柳鸣九据此认为,“我们”应对这些具有进步政治倾向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⑥。他说:“萨特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⑦这番言论发表在萨特逝世后不久,颇有为萨特盖棺定论的意味。不过柳鸣九的分析,使萨特的“倾向性文学”变成了一种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战斗文学,而其真正内涵却被深深遮蔽。事实上,有关外部世界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侧面,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演绎才是萨特等人的创作旨归。在萨特的创作中,作家不仅书写着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还细腻描绘了笔下人物遭受现实异化的生存图景。他对人类恶心式生存体验的叙述,对人类摆脱自在生存方式后向自为境地进发的英勇举动,都倾注了远比政治斗争更大的热情。所谓的“倾向性文学”或“战斗文学”,其实质都与人类脱离存在困境的精神苦斗密切相关。柳鸣九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出于某种传播策略的需要,他不惜以误读存在主义文学为代价,希冀通过对萨特的政治解读来推进存在主义文学的广泛传播。由此引发的一个传播现象,便是语言游戏的大行其道:利用新时期初相对含混和自由的语义空间,中国知识分子凭借有意误读的传播策略,将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并于此过程中逐步完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知识合法化。在新时期初的政治格局中,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去衡量,大部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都不够合格,甚至有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因其阶级属性而被意识形态目为“反动”作家。因此,介绍哪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就不再是一个介绍者的个人兴趣问题,它还关涉到介绍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在经历了“”腥风血雨之后,对于政治运动的恐惧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时,往往侧重于介绍那些在政治立场上与无产阶级作家较为接近的现代主义作家。但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大多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而非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的政治立场。
二、在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利用人道主义思想潮流,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传播策略。而这一传播策略的实质,就是为存在主义文学寻求启蒙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
由于人道主义作为新时期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当时启蒙主义的具体倾向。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具有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层面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启蒙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1979、1980年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为人道主义思想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据,当时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提法充分反映了这场讨论的思想实质。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启蒙合法性之外,使其加入到争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思想潮流中。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业已意识到了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是何等重要,他们通过一系列阐释,最终证明了传播存在主义文学不仅可以迎合思想启蒙的需要,同时还能间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根基。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中,存在主义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人道主义性质?而启蒙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又将如何获得?
1980年,《外国文艺》登载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⑧一文。该文标志着存在主义也加入了当时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在这篇文章中,萨特批判了一切对于人的先验设定,认为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在萨特的解释中,存在主义由于对人类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强调,认为“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而是一种“人道主义”⑨。由于这一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锋芒直指“”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迷信。因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被介绍进来,便成为新时期初启蒙思想者的有力武器。
与此同时,为强化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中国知识分子还以简化存在主义的方式彰显其人道主义品格,如以“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核心命题概括存在主义,认为“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大大优越于那种怠惰寄生的哲学和依靠神仙皇帝的消极处世态度;它把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作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也有助于人为获得优秀的本质而做出主观的努力,为这些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这就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⑩。这段评论中提及的“命定论”和“宿命论”,正是“”阶级决定论和血统论的另一种表达。因此,肯定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论和“自由选择”论,就意味着存在主义文学具有反对“”阶级决定论和血统论的人道主义属性。在这个角度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提法本身就具有启蒙功能。事实证明,惟
推论出存在主义文学所具备的启蒙合法性,才能使其获得广泛而坚实的民间思想支持。在反思“”、呼唤人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存在主义文学最终成为了人们表达“”异化梦魇、批判阶级决定论的思想武器。
不过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若想促进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仅仅具备民间思想的支持还远远不够,除非在意识形态层面证明其合法性,才能真正推进存在主义文学的广泛传播。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时,也充分重视对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证明。
饶有意味的是,尽管对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认识歧义丛生,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在理解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方面殊途同归。以柳鸣九为代表,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延续,即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而刘放桐却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新人道主义”,其实质是对柳鸣九所谓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的反拨。尽管这两种观点南辕北辙,但它们却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阐释中,成为论证存在主义文学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有力论据。
在谈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时,柳鸣九说:“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家不少人都赞颂过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人的开拓精神,人是世界的主人。……我们从萨特对于存在主义的解释中,难道不能听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思想家这类论述的某种余音?”11由此推断,柳鸣九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属于正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就是西欧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它以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绝不能是手段”为其最高成就。尽管在中国当代社会,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传统一度被视为“温情脉脉的资产阶级面纱”而屡遭批判,但它对人类自由精神的弘扬,却暗合了新时期初呼唤人性与正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更为重要的是,柳鸣九将存在主义文学整合到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传统中去的目的,固然是出于论证存在主义文学启蒙合法性的需要,但通过这一方式,柳鸣九同样也能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为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实则是封建主义的天敌,它所具有的反封建功能,恰恰是意识形态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因此,在谈论萨特的政治立场时,柳鸣九极力强调萨特的反封建性,目的就是要论证萨特的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无疑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有力证明。
然而,在刘放桐看来,存在主义文学却是一种反启蒙—理性传统的“新人道主义”。他将20世纪以来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均称为“新人道主义”。这些新人道主义批判和否定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思想,“要求恢复被理性主义所压抑和沉沦(也就是‘异化'''')了的人性”。他认为新人道主义集中反映了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潮流,“要剥去压抑和歪曲人的本质的物质和精神(理性)以及社会等‘虚伪的''''外壳,回复到人的原始的、独特的、内在的本性”12。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剥离了人的社会属性,那么新人道主义就有可能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但在评价新人道主义时,刘放桐却巧妙绕开了“唯心/唯物”的二元对立,转而在新人道主义的批判功能上大做文章。在他看来,新人道主义的颇可观瞻之处,就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亦即启蒙—理性人道主义虚伪性的批判。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古典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人的那种充满信念、乐观的描述是迥然有别的”13,因此,存在主义文学本身就是新人道主义的集大成者,它对于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传统的批判,正暗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维护自身权威、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刘放桐认为存在主义作为新人道主义的重要流派,具有一种间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功能。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也相应地具备了意识形态合法性。
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到,尽管柳鸣九和刘放桐等人在认识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方面存有分歧,但他们通过语言运作,为存在主义文学争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却不言自明:柳鸣九将存在主义文学整合到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传统中去的目的,是想在反封建角度为传播存在主义文学获取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刘放桐对存在主义文学“新人道主义”性质的界定,则是利用新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功能,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维护意识形态权威的话语功能。
三、在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还从存在主义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出发,为其传播行为寻求一种源自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依据,并以此作为
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又一重要策略。在介绍萨特的文学创作时,柳鸣九认为《恶心》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近似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尽管《恶心》没有“表现出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但“其中那种强烈的厌恶的情绪”,却正是“针对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特别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开始猖獗的那样一个时代社会,这正如《狂人日记》一样,……表现了一种激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因此,在法国有人很自然把这种带有某种抽象性质的小说,称为‘左翼小说''''”14。从柳鸣九对于《恶心》的解读方式中,明显可见一种过度阐释的痕迹。为突出《恶心》的反封建性,柳鸣九有意忽略了该作对人类生存体验的揭示,转而从反封建的角度将《恶心》与《狂人日记》相提并论。事实上,《恶心》真正的创作目的仍然是萨特对其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演绎。从洛根丁的生存体验出发,萨特揭示了现实世界的荒诞性,也对人类置身其间的种种精神困境做出了象征性的书写。在此基础上,《恶心》的创作主旨,就是一部象征人类存在困境的荒诞寓言。而柳鸣九彰显《恶心》反封建主题的做法,不过是依据五四新文学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与柳鸣九相对狭小的阐释视野不同,还有学者试图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存在主义解读,全面揭示鲁迅思想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倘若这一推论得以成立,那么鲁迅就会成为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合法性依据。因此,为达到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目的,以误读鲁迅的精神哲学为代价,尝试用存在主义思想改造鲁迅的启蒙文学。
如关于鲁迅与存在主义,尽管是对鲁迅早期思想矛盾的分析,但字里行间,却处处可见对于鲁迅精神哲学的存在主义式改造:无论是以“存在先于本质”说解读“过客”形象的存在意味,还是以“自我意识”说理解鲁迅描绘的精神现象,论者均以先验的存在主义思想为阐释武器。这一阐释方式不仅遮蔽了鲁迅思想及其文学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把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改造成了一位存在主义者。在误读鲁迅的过程中,《阿Q正传》被认为是最能体现鲁迅存在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论者看来,阿Q不光是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他身上还浓缩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变化。而这一自我意识,正蕴涵于精神胜利法之中。也就是说,阿Q在处处受辱的存在窘境下,为维护人性尊严不得不以精神胜利法来保护自己。这种通过歪曲自我意识证明自我存在的精神胜利法,“正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主观唯心主义翻版,也是存在主义‘意识中存在本质''''这一主导思想的真实写照”15。在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本身无可指责:因为一个无论从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人物,如果没有“精神胜利法”的自我保护,势必会失去自我意识,从而沦为“虫豸”一般的动物。“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一种歪曲了的自我意识,它实际上是阿Q在污秽现实中维护自我意识的一种精神武器,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实施自我保护的手段。从这一判断出发,论者认为民族衰落的责任并不应该由阿Q负责,相反,造成阿Q自我意识歪曲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才是小说真正的批判对象。因此,《阿Q正传》仍然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和社会批判意识。
巧妙的地方在于,通过转换论述逻辑,论者尽管指出了《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品格,但最后仍然将鲁迅归结为一个存在主义者。那么,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细究论者的叙述逻辑,隐约可见一种具有诡辩意味的思维方式:首先从存在主义的自我意识出发,认定《阿Q正传》并非一部“批判国民劣根性”作品,而是鲁迅对阿Q歪曲了的自我意识的表达,这一表达方式即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对“精神胜利法”造成阿Q自我意识歪曲现象的分析,论者试图说明鲁迅如何从存在主义的概念出发揭示阿Q。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点,就会忽视鲁迅在《阿Q正传》中鲜明的历史批判和社会批判意识。为弥补因对存在主义的分析而忽略的这一现实因素,论者又将阿Q自我意识歪曲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环境对人的异化,从而使得《阿Q正传》回到了鲁迅对于社会历史的批判当中。通过这一叙述策略,该文作者不仅没有否定鲁迅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反而在存在主义的解读方式中,借助阿Q自我意识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存在主义的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这就意味着在《阿Q正传》中,普世性的存在主义获得了一种与老中国具体时代背景相关的现实意义。因此,鲁迅和存在主义之间的联系,就具有了一种被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所支持的现实基础。这一叙述策略的实质说明,即使是从“唯心主义(存在主义)出发,也能推导出唯物主义(历史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结论。在《鲁迅和存在主义》一文的结尾,论者说:“列宁在1908年给高尔基的信中说:‘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不仅能获得重要的、服务于人类进步的见解,并且最后会导致唯物主义的结论''''。”16论者对于《阿Q正传》的解读方式,仍然是一种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叙述策略。
需要指出一点,这种论点为实现其改造鲁迅精神哲学的目的,有意忽略了鲁迅启蒙文学的精神发生学——须知鲁迅的启蒙文学乃是他对中国大众爱之深、责之切的情绪郁结之产物:从“哀其不幸”出发,在透视国民劣根性的叙述过程中,老中国儿女的愚昧和麻木深深刺痛了鲁迅的灵魂。由此引发的“怒其争”,实实在在表达了鲁迅对于乡土中国的赤子之心。在考察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启蒙文学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带有具体历史背景的精神发生学。相形之下,该文对于鲁迅思想的存在主义解读,显然以先验的理论阐释遮蔽了鲁迅所受的时代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关注人类自我意识的作品都归结为存在主义,就会抹杀文学反映人类自我意识的不同方式,因为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内的文学杰作莫不关注人类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鲁迅启蒙文学的存在主义解读,仍然是一种为传播存在主义文学寻找合法性依据的过度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度阐释尽管在客观效果上扩大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其后果却直接造成了新时期学者对
于五四新文学的深重误读。由于受到新时期初意识形态话语的规约,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时,也不得不戴上镣铐跳舞:他们既要响应思想解放运动的号召,通过传播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履行其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又不能忽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在这种两难抉择中,常见的一个做法似乎就是改造五四新文学。在新时期学者的阐释下,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被无限放大,由此自然割裂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天然脐带。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数不胜数,如:为传播意象派诗歌,刻意夸大五四新诗所受的意象派影响,从鲁迅小说中解读“意识流”因素,等等,均可被视为误读五四新文学、想象现代性的典型个案17。从积极的角度说,这一做法在“体制为游戏规定了一些界线”18的传播背景下,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但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式的阐释学立场,尽管在理论创新方面能以激进的当代姿态介入文学史格局,却无法摆脱进入西学后的理论风险,因为西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似乎一直是现代性的直接阶段,而未经自我理解的现代性想象,显然无法保持民族境遇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话语层面的意识形态之争,抑或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性想象,都不过是新时期初知识分子在现代主义这一“他者”中失掉自我意识的表现。而本文对于80年代新时期文学思潮中误读现象的分析,期待的正是告别文化怀旧、从理解“他者”到自我理解的理论勇气。
注释:
①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③④⑤⑦柳鸣九:《萨特研究?序》,《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2期。
⑧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外国文艺》1980年第5期。
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外国文艺》1980年第5期。
⑩11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2期。
1213刘放桐:《存在主义与文学》,《文艺报》1982年第8期。14柳鸣九:《萨特研究?序》,《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16徐岱、潘一禾:《鲁迅与存在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
17叶立文:《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