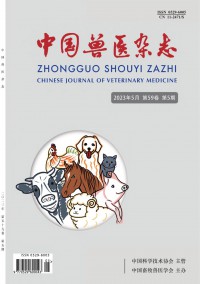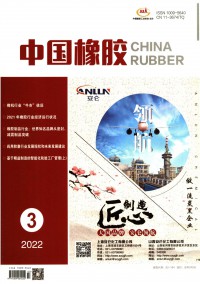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政治化

一视建筑为艺术的观点源起于西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罗马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就提出了建筑的三大原则“坚固、适用、美观”。[1](P16)在建筑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西方比较早地认识到建筑的艺术属性,虽然黑格尔认为建筑艺术包含较多的物质内容,因而处于艺术发展系列的最低层次[2](P8),而罗杰·斯各拉顿也承认,建筑是“政治性最强的艺术形式”[2](P9),但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建筑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雕刻、绘画、诗歌、音乐等经典艺术形式一起被归入艺术的发展系列当中的。许多哲学家、美学家比如谢林、歌德、黑格尔、叔本华等,都有关于建筑美学、建筑艺术的论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名言充分表达了西方学者对建筑艺术属性的肯定。
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从未把建筑作为艺术看待。《易经·系辞下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宫室”是中国古代对房屋的通称,泛指建筑。这段话揭示了建筑产生于人类最初遮风避雨的居住需要,带有明显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特征。而这也是早期人类营造建筑的初衷。
关于建筑,墨子有一段名言:“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墨子·辞过》)这段话同样表达了人类社会早期建筑的物质功能。大概中国古代人对建筑的理解,总是首先从其低层次的物质需要方面切入。对墨子的这段名言,大多数人理解它是讨论“便生则止”的建筑节俭原则,实质上它更重要的内容在“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这一句上。墨子一贯主张节用,认为营造宫室便生即可,反对铺张浪费,而在这里却提出“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作为与“便生”相提并论的建筑原则。在中国古代,“礼”的含义非常广泛,既是礼制、礼法,又是礼节、礼仪,而不管是作何种理解,“礼”所具有的政治意义都是不容否定的。“男女之礼”是礼之大本,是一切社会伦理关系的基础;而“别男女之礼”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伦常道德的基础,而且是制定一切政治制度的伦理原则。墨子把“别男女之礼”与“待雪霜雨露”相提并论,作为建筑最基本的营造原则,可见,古代中国人对建筑的理解,政治功能与经济原则是相伴而生的,建筑被纳入政治领域。
《大戴礼记·朝事》云:“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三公之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在中国传统礼制的规定中,“宫室”(即建筑)与“国家”、“车旗”、“衣服”、“礼仪”,同属国家仪典的范围,其重要性是在宗法礼制的基础上被承认的。
据佛莱彻尔的看法,“艺术是一种诗意的(感情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但建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与其他纯艺术不同,建筑一般都具有物质性的使用功能,受到材料、结构等物质条件的限制,要依靠一定的物质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建筑艺术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而且,根据建筑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结合的紧密程度,建筑艺术的精神属性也可以分成三个层级。最低层级是“坚固、适用”。这是与物质性紧密相关的,建筑首先必须符合其物质功能,带给人安全感与舒适感。中间层级是“美观、悦目”。这就“与物质性因素相距稍远,体现为在达到上一层级的建筑美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所谓多样统一的‘形式美规律’如比例、对称、对比、对位、尺度、虚实、明暗、色彩、质感……等一系列手法,对建筑的一种纯形式的处理,以造成建筑的形式美。”[3](P6)这一层级注重建筑的外在形式,如维特鲁威所说:“当建筑物的外貌优美悦人,细部的比例符合于正确的均衡时,就会保持美观的原则。”[1](P16)最高层级是“赏心”。它“离物质性因素更远,要求创造出某种性质的环境氛围,进而表现出一种情感,一种思想性,富有表情和感染力,以陶冶和震撼人的心灵……以达到渲染某种思想倾向性的效果。”[3](P6-7)进入到精神性的这一层级,建筑艺术才能真正超越工艺美学和技术美学的范畴,成为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成为艺术学和艺术美学的关注对象。这一点非常重要,而恰恰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像维特鲁威所理解的建筑原则,也是至“美观”即止。
从以上对建筑艺术的精神属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建筑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赢得艺术的地位,但它绝不只是如西方人所理解的,只是对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的一种物质上的满足;由于建筑艺术被政治化、伦理化,所以中国古代人更加要把建筑纳入政治生活的领域,通过建筑的特殊语汇和表现手法,来表达其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观念,这不但无损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价值,而且客观上还使它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二维特鲁威对建筑学的分类有明确的说明:“建筑学的内容是三项:建造房屋;制做日晷;制造机械。建造房屋又分为两项:其中之一是筑城和在公用场地上建造公共建筑物;另一则是建造私有建筑物。公共建筑物的分类有三种:第一是防御用的;第二是宗教用的;第三则是实用的。防御用的要预先考虑设计城墙、塔楼、城门,使其经常能够抵御敌人的攻击;宗教用的是建立永生的诸神祇的庙宇和神圣建筑物;实用的是布置供大众使用的公共场地,即港口、广场、浴场、剧场、散步廊以及其他以同样理由而在公共场地规划的建筑物。”[1](P16)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古典建筑体系的公共建筑物,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两大类型的建筑:实用性建筑(防御功能亦属实用功能,因此防御性建筑物亦可看作是实用性建筑物)和宗教性建筑。根据前述建筑艺术精神属性的三个层级,实用性建筑因其与物质性的紧密相关程度而处于精神属性的较低层级,而宗教性建筑则可以看作是处于建筑艺术的最高层级的,因此,宗教建筑是西方古典建筑体系的重心,在西方建筑艺术中占主导地位。
而必须承认,“与西方相比,中国宫殿建筑在艺术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不少艺术史家说,西方建筑是以教堂、寺庙为主体串起来的一部艺术史,而中国建筑则是以宫殿串起来的。的确,在中国古代,宫殿始终是建筑舞台上的主角,从未出现过时间上的断裂……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能存在并发展这么长的历史跨度,实在是很罕见的。在中国古代的任何历史时期中,建造得最宏大、最华丽、级别最高的每每都是宫殿。它代表了中国建筑文化中的精华,在它身上也最能完整地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特殊性格,宫殿不愧为中国古建筑的重心。”[4](P78)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宗教建筑从未取得其独立地位,更毋庸说“主导”了。占据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帝王宫殿。宫殿虽是帝王的居所,但却绝对不是纯粹的私有建筑物,而是具有普遍政治象征意义的纪念物,是国家政权和君主统治权的象征。在中国这个具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度,帝王宫殿在建筑体系中的主导性是无可置疑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其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在汉初国力羸弱、国库空虚之际,萧何大兴土木营建宫室,遭到了汉高祖的斥责,但萧何以“非壮丽无以重威”对应,高祖方转怒为喜。“重威”是壮其宫阙的根本目的,是王权至尊的象征。正是出于强化政治秩序的考虑,汉高祖和萧何才能不计较儒家的“卑宫室”和墨家的“节用”、“便生”思想,堂而皇之地营建富丽堂皇的宫殿。而中国历代关于建筑的记载,以皇宫建筑的资料最为详尽,皇宫的营建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被载入史册,流传后世的。
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萧何一句“非壮丽无以重威”,就足以令汉高祖转怒为喜,庄严雄伟的宫殿虽然未必住得舒服,但却绝对能壮君威。统治者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出则见巨阙巍然,入则见高堂数仞,后车千乘,食前方丈,何等威风的排场!不由得统治者不自信自己确是高人一等,高贵威严的气质油然而生。而群臣百姓在宫阙连绵、鳞次栉比的壮丽景象面前,也很容易被其排山倒海的气势所威慑,敬畏臣服之心顿生。因此,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儒家的“卑宫室”和墨家的“节用”、“便生”等学说,极力倡导经济原则和节约美德,甚至在宫殿建造问题上还有过关于节俭与侈靡的激烈争论,但历朝历代的“高台榭、美宫室”之举只有变本加厉而从无稍息,皆“重威”之政治考虑所致。
诚然,“高台榭、美宫室”并非中国古代宫殿的专利。西方建筑史上比中国皇宫建筑更加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比比皆是,古希腊建筑就以“高贵的庄严,静穆的伟大”著称。比如,中西方建筑史上都有关于营造“通天之台”的传说。《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了人类营造“巴别塔”的故事,说是上古时候,人类对变幻莫测的天空充满好奇心,于是商议着竭尽全人类的力量,协作建造一座能通往上天的“巴别塔”。后来,塔越建越高,连上帝都感到震惊了。为了阻止人类这个计划的实现,上帝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他们语言不通,彼此产生误解,终于使这场人类联合向自然挑战的行动半途而废了。这就是西方关于“通天之塔”的传说。中国也有类似的传说,《新序》曰:“魏王将欲为中天之台,许绾负插而入曰:‘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原(愿)加一力,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九千里,其趾当方一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为台趾。’王默然,罢筑者。”传说魏王想建一座中天之台,大臣许绾对魏王说:“我愿意助大王去建这座中天之台,但听说天地之间相距一万九千里,那么这座台光基址就要方圆一千里,大王您的国土还不够建这个台基呢!”许绾的劝谏终使魏王放弃了荒唐的念头。这是中国古代“中天之台”的传说。由此可见,中西方建筑史上,其实都有过“高台榭”之类的相似的建筑观念,但仔细分析可知,西人营建巴别塔的意图是通过建筑的手段,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这多少有着张扬人类理性和力量的意味;而魏王欲建中天之台,却纯粹是出于帝王的一种奇思狂想,其目的只是想展示帝王的权势和力量,两者的含意还是有区别的。而如我们所见,历代帝王一方面倾其国力“高台榭、美宫室”,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搜罗天下奇花异草,用以营建秀美优雅的皇家园林,而许多帝王更加是不愿意居住在庄严宏大的皇宫中,只要有可能,就到皇家园林中颐养身心。可见,要说“高台榭、美宫室”是为君王居处所需,毋宁说它最主要是服务于“壮君威”的政治目的。
君权至上的政治观念是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点从建筑方面就能充分体现出来。时至今日,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建筑群通常是该地区所有建筑物当中最宏大、最威严、最有气派的,有鹤立鸡群之势,这就是“高台榭、美宫室”的流风遗韵。
三也许皇宫作为建筑体系的主角,还不能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建筑淡于宗教而浓于政治伦理的建筑艺术特色。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集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无不想通过建筑艺术来显示帝国的实力和威严,而在西方古典建筑体系中,宫殿建筑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某些帝王宫殿,其富丽奢华程度,甚至较之中国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法国绝对君权时期的象征物——路易十四的宫殿凡尔赛宫,就是绝佳的例子。
但是,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即使宫殿建筑在西方古典建筑体系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宗教建筑始终是其主导,圣索菲亚大教堂、圣马可教授、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亚眠主教堂、佛罗伦萨主教堂……数不胜数的著名教堂构成了西方古代建筑史的光辉历程,它足以令宫殿建筑相形见绌。而中国历朝历代的佛寺、道观虽然为数众多,但其建筑艺术成就及其对建筑文化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与宫殿建筑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在西方建筑艺术史上,带有政治秩序象征意味的建筑除了帝王宫殿这一条主线之外,还存在着公民大会堂、议会和政府机构这一条副线,尤其在18世纪以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数相当多的元老院、巴西利卡和市政厅,其建筑艺术成就不逊于皇宫。而在中国古代,作为政治权力象征的宫殿建筑,自古辉煌,持久延续。无论是秦朝的阿房宫还是汉朝的未央宫,无论是唐朝的太极宫、大明宫还是明清北京的紫禁城,都是代表当时最高艺术成就的建筑物,作为官方建筑艺术支流的政府部门建筑和各地衙署建筑,则是处于宫殿建筑的绝对从属地位,无论在规模、在艺术水平上都无法与宫殿建筑分庭抗礼。
其三,最重要的是,帝皇宫室虽然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角,但与其说它是独立的艺术作品,不如说它是庞大的都城规划艺术组群中的一个部分。正如汉学专家李约瑟博士的评价:“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正好相反,例如凡尔赛宫,在那里开放的视点是完全集中在中央的一座单独的建筑物上,宫殿作为另外的一种物品与城市分隔开来。而中国的观念是十分深远和极为复杂的,因为在一个构图中有数以百计的建筑物,而宫殿本身只不过是整个城市连同它的城墙街道等更大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而已。”
宫殿是帝皇的地上住宅,皇陵是帝皇地下居所,皇家园林是帝皇的园囿,都城是帝皇的城堡,官衙是帝皇的臣子所居,民宅是帝皇的子民所处……皇宫绝不是一座单独的建筑物,也不是一组孤立的建筑群,皇宫在作为单独的艺术作品被欣赏时,其艺术成就和政治象征意义是远不如它作为都城艺术组群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高远和深邃的。因此,皇宫以及与帝皇有关的一切建筑物,是连同整个都城的规划一起考虑的。都城的每一部分都布置得井井有条、严谨整饧,无处不显露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这种政治性极强的都城规划理念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西方的宫殿建筑和城市规划无法比拟的。
可见,中国古代政治性建筑的辉煌成就,绝不仅仅表现在它的主角——宫殿建筑上,而是表现在它以宫殿建筑为主线而严整规划起来的都城面貌上,都城规划的规范和标准——营国制度,于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式写入政治制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