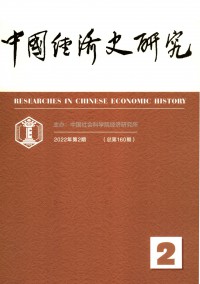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化特征

摘要:基于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运用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点,Prais-WinstenAR(1)和OLS对突变点前后不同增长阶段进行回归,并解析结构变化、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因素是资本、劳动、对外开放和城镇化,阻碍经济增长表现为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不断增多增强;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创新将成为增长新动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化;结构突变点;主动力;负动力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进入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传统增长动力出现衰减迹象,进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期”。那么,究竟是哪些增长动力驱动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又是哪些动力正发生着转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别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资本、劳动、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经济结构(或要素禀赋结构)、政治制度、产权制度等因素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蔡昉等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及能源资源等要素投入[1][2]30-38。赵志耘等分别发现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正向影响[3-4]。林毅夫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6]。同时,Aoki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7][8]40-45。欧阳峣等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不可能跨越“劳动投入驱动”向“资本投入驱动”再向“技术知识驱动”转变中的任何阶段[9]。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一方面来自资本、劳动等要素禀赋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下的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效率的提高,但鲜有学者探究在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结构突变点下的阶段性动力问题,并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综合考虑各增长动力因素特征。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系统,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因素内生化纳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尤其是将基础设施作为要素禀赋因素引入扩展模型;二是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问题,运用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chow突变检验找出13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点,并以此对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划分;三是考虑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驱动作用的异质性,再解析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试图部分解答本文提出的疑问。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基于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模型:Y=AKα(uhL)1-αhγε(γ0)(1)其中:Y是总产出,K是固定资本存量,uhL代表人力资本存量,hγε反映人力资本外部效应,A代表外生技术水平。式(1)取对数形式为: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μ(t)(假设β=1-α)(2)如果lnhε不能解释全部TFP变动,则残差项μ不符合随机分布的特征,表明除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需要引入其他因素来解释生产率变动。因此,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内生化,建立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将式(1)中的A定义为:A=Ae(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3)将式(3)带入式(1),并对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取对数: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4)(二)变量说明考察时间为1952—2014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用名义GDP平减后的实际GDP作为因变量,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系统作为解释变量。要素禀赋动力因子系统。选取4个变量,物质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①固定资本存量(fcs);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pcs)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劳动力:历年就业人数(job);基础设施:平均标准道路里程(inf),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折算成标准道路里程。科技创新动力因子系统。科技资本存量(tcs):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结构变动动力因子系统。选取4个变量,经济外向型结构:外贸依存度(ops),等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外资存量(wcs):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利用外资量;产业结构(ins):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城乡结构(urs):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化率);金融结构(fins):贷款量与工业总产值比值。制度变迁动力因子系统。选取2个变量,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程度(nsta),即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政府主导程度(sta):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演变特征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验证与划分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模型对中国1952—2014年时间序列运用GAUSS软件经5000次迭代,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无法拒绝结构突变点存在假设(在5%显著性水平),且中国经济增长存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3个结构突变点[10],第1个突变点与Aoki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点一致。运用chow突变检验验证3个结构突变点前后变量是否有明显变动,结果表明应该拒绝原假设,即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前后存在突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11]20-28,存在阶段性动力,因此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将经济增长划分为1952—1977年、1978—1994年、1995—2011年和2012—2014年4个阶段。(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追溯及演变特征运用Stata11.2软件,为校正时间序列自相关带来的偏差问题分别采用Prais-WinstenAR(1)或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方法,回归结果详见表1。对比模型(2)与扩展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除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贡献[12],因此选取扩展模型(4)进行为探究经济增长不同阶段动力演化规律与特征,对1952—1977年、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分阶段进行回归,由于2011—2014年时间序列样本较少,回归模型不稳定,故将此阶段并入1995—2011年考虑,结果表明:从要素禀赋动力来看,资本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但驱动作用逐渐下降;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效应;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可见,要素禀赋因素的驱动作用正在逐步衰减,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下降。从科技创新动力来看,科技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溢出效应且逐渐增强,但贡献相对较小。从结构变动动力来看,1952—1977年对外依存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1995—2014年则表现出显著负效应,而外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持续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在1995—2014年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效应,前两个阶段均表现为不显著的正效益;城镇化水平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且不断增强;金融结构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效应。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1952—1977年和1978—1994年非国有化程度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效应,1995—2014年制度变迁因素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制约作用综上可知,要素禀赋因素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资本驱动作用逐步衰减,劳动力驱动作用虽保持增加,但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发展所需不匹配矛盾凸显,“人口规模动力”未有效转化为“人才动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较小,拉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尚未完全释放,是具有潜质动能;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驱动作用越来越显著[13];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度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阻碍经济增长作用日益凸显[14]。
四、结构变化、制度变迁对经济
增长动力演变影响的再解析考虑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不断增多、增强,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对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做进一步再解析。由第一主成分确定1952—2014年结构变化因素(剔除利用外资二级指标)、制度变迁因素各二级指标权数,得出结构指数和制度指数。结构指数数值(相对值)越大,经济结构越合理;制度指数数值(相对值)越大,制度设计与经济发展越匹配。从结构指数与实际GDP动态关系来看(图1),1952—1970年结构指数呈相对下降趋势,实际GDP也处于缓慢增长;1970年以后结构指数稳步上升,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结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实际GDP增长也较快;2008年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放缓,2009年和2011年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而实际GDP增速仍较快,直到2013年这种影响才显现,实际GDP增速开始下降,说明中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未从根本上缓解危机影响,反而可能导致或加剧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总体上看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保持了一致性的变动但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图1结构指数与实际GDP关系图从制度指数与实际GDP动态关系来看(图2),1952—1960年制度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实际GDP也维持一定增长;1960—2000年制度指数在[-0.5,0.5]区间上下波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变化步调基本一致;2000—2011年制度指数不断上升且波动性增大,实际GDP则表现出较快增长,制度体制与经济发展匹配度较好;但2011年以后制度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实际GDP增速也明显下滑,表明制度政策已与经济增长不适应[15]。因此,总体上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变化步调基本一致,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较敏感,即使短期性制度体制改革或政策措施也会引起经济增长不同程度波动,虽也存在传导时滞性,但比结构变化反应快。图2制度指数与实际GDP关系图
五、结论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劳动力、对外开放、城镇化水平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度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负动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效益逐渐减弱,而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牵制作用越来越强。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变表现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不断衰减、衰弱,阻碍经济增长的负动力因素不断增多、增强,尤其是结构性、制度性因素表现出较显著的牵制作用,与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明显下降现状相吻合。第三,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均保持一致性变化及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较敏感、反应要快,影响力更持久,表明中国现阶段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结构性矛盾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之一。第四,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促进要素优化配置来实现[16]。经济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质动能,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主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经历从“要素禀赋”向“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的转换。
作者:钱娟 李金 聂春霞 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