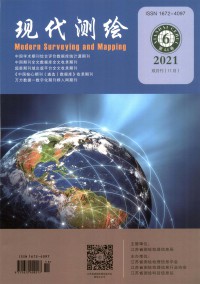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反思

相比于文学语言研究,文学与语言研究则是具有跨学科性的动态研究。其关注核心是文学与语言的互动关系。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是如何建立的?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如何互动的?解答这样的问题,需要结合文学史,从语言史、翻译与传播等方面寻找答案。
现代文学与语言运动对现代文学与语言革命这个问题,我们存在这些疑问:语言是否能被革命?语言中的外来因素是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使然,还是人为变革使然?持有静态观念的学者认为语言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①语法与词汇的稳定性很难被“革命”。②这种看法让文学研究止步于语言学,它固然考虑到语言转变的内在规律,但忽视了语言的自为性变化,即忽视了语言是怎样被人们倡导并发生变革的。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语言运动,以思想启蒙与群众教育为出发点,对现代汉语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涉及教育界,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文学创作。所以若忽视文学与语言运动的关系,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可喜的是,在现代文学与语言革命的问题上,仍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比如把语文教学纳入国语运动来考察,③超出了以往对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的讨论,④也超出了语言变革个案研究的限制。⑤再如结合语言运动、现代文学和语言教学的研究,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细致的材料处理功夫,因而份量十足。⑥其他相关研究,总体方法上仍是走从史料出发的路数,⑦但在研究切入点上各有千秋。有些研究语言与文学的作用关系;⑧有些从文字改革角度考察文学革命;⑨还有从语言变革的角度讨论文学革命的发生和现代文学形成。瑏瑠若把研究对象缩小到新诗语言,现阶段研究显然还不足。只有民间语言资源影响下的歌谣和方言诗歌被关注过。瑏瑡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新学制的实行,使白话教材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以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为例,选文多来自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郭沫若、俞平伯、冰心等人的新诗创作均进入选本。选本的时代性强,文体多样,富有教益性。同时,新诗在中学的推广及引介,也培养了潜在的年轻作者。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和新诗推广同样也促进了新诗发展。学校教育是如何影响新诗发展的,现阶段这类研究较少,瑏瑢因此也可作为对新诗语言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
现代文学与翻译活动近代翻译活动持续时间长,跨度大,译者人数众多,翻译材料充栋,内容驳杂,这些都为翻译研究增加了不少困难。随着近现代翻译史的出现,中国近现代翻译活动的线索得以厘清。尤其是文学翻译史的问世,瑏瑣更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参考。瑏瑤纵观近三十年的文学翻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翻译主体研究点的改变。较于以往的近现代翻译史,现在更侧重研究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瑏瑥作为最早参与中国近现代翻译活动的群体,传教士在华翻译的具体活动、译介策略、引起的反响等问题得到了更充分的研究。瑏瑦诗歌方面,有学者通过发掘基督教诗歌史料,论述了传教士汉译圣诗对新诗形式产生的影响。①这种文本细读与史料发掘相结合的研究,也为现代汉诗语言发生提供了新颖的解释。二是注重翻译与主体的互动关系。翻译活动与翻译主体、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受到了正视。翻译不是简单的符号转换,甚至不是对等的符号转换;在符号的再转换中,翻译主体、社会文化心理共同决定着翻译内容,影响着翻译主题。例如诗歌翻译中出现的“归化”与“异化”现象就体现了诗歌翻译的矛盾心理;而译诗中选取的救亡启蒙、爱国抗争、人道关怀等主题也与社会心理密切相关。②此外,主体的“译”与“作”间的互动也值得关注。③它摆脱了以往翻译研究侧重技术探讨的局限(即剖析文本该怎样翻译),而将翻译活动与翻译主体的关系纳入考察范围。这些新近的研究将翻译活动从静态空间释放到动态领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三是翻译活动中的语言问题逐步得到重视。从最初的翻译技巧研究,到翻译史研究,再到翻译主体的社会文化研究,其研究对象都未切近到翻译活动最本质的载体———语言。若能结合翻译语言谈文学语言变迁,笔者认为也许更能发现改变现代文学语言,甚至现代新诗语言的深层动力。④“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怎样获得合法性,现代性怎样“在翻译中生成”,⑤这类前瞻性论述的提出,开启了我们对翻译活动意义再思考与重估。现代文学语言有多少是在翻译基础上建立的?该怎样看待近现代文学翻译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思考与辨析的问题。此外,比较语言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将翻译现象与语言特性并置而谈,独具特点。⑥翻译活动是语言对语言的渗透式影响,具体到语言结构上,究竟哪些语言结构被汉语言吸收了,哪些语言结构又被淘汰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能落实并细化文学翻译语言研究。总之,翻译活动视野下的新诗语言研究属起步阶段,系统性研究成果稍欠。现有研究虽涉及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变化,但现代汉语怎样生成现代汉诗,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等问题还未解决。较于文学语言,诗的语言特性更难捕捉,所以从语言结构方面研究诗语变化将具有一定难度,也值得我们挑战。
现代文学与传播媒介文学与语言关系之动态研究包含了对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的考察。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⑦媒介性质、出版手段对现代文学性质的影响问题,⑧新传播方式与创作主体的互动问题,是现阶段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在文学语言和诗语言方面,研究成果则稍显稀疏。大部分论著稍稍涉及却未深入展开,仅少数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研究。如从传媒角度重新审视现代文学语言的选择机制。⑨相比古代白话文学作品,近现代文学结合全新传播渠道,以惊人速度迅速发展。媒介作为面对大众的讯息载体,其自身特性决定了白话成为最被接受的表达方式。这种极具推动性的传媒力量,给现代文学语言带来的内容及问题也值得我们思索。运用知识考古法厘清史料,能帮我们找到可供参考的证据。如在研究晚清报刊与诗歌的关系时,考证传教士戒陋俗诗、早期《申报》新题材诗、报刊对诗界革命的促进等内容,瑏瑠丰富了我们对诗歌语言嬗变的认识,使新诗语言的发生呈现出深刻复杂的历史风貌。值得一提的成果还有对“新诗集”的研究。瑏瑡它扩展了诗歌传播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多样,思维方式多元,填补了新诗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空白。纵观近三十年现代文学语言的内外部研究,笔者认为,此话题仍有探讨空间。诗语革新作为文学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其文学史意义已被充分肯定。但现阶段新诗语言的外部研究还相当缺乏,更缺少把语言运动、诗歌翻译与传播等各环节串联起来的研究成果。对文学语言的整体研究虽有参考价值,①但诗作为对语言艺术要求最高的文学形式,具有其自身的语言特性。把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语言研究结论,纳入诗语研究也许并不适合。所以在研究策略上,既要考虑以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要结合新诗自身的特性,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从而对新诗语言的发生和嬗变给予深入描述和阐释。研究方法上,知识考古式的史料清梳是必须工作,同时也应适当结合语言层面的诗歌分析与文本细读。
“诗”与“思”的互动:诗性研究与思想性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语言思潮涌入文学研究界。由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德法语言哲学等流派对文学语言的关注,语言问题也在我国成为热门话题。“文学失语症”②即当时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伴随着对“失语”和“话语重建”的探讨,语言学、③文艺学④和文学界质疑五四语言变革以及新文学创作的声音也不断出现。⑤例如郑敏在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抨击中,⑥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过激地否定了文言传统,造成语言断裂,使现代新诗语言美感匮乏。⑦郑敏等学者对“诗魂何处投胎”的追问,也从诗性和思想性维度,表达了对某些诗语缺乏创造力和深刻性的不满。而诗性和思想性这两个问题,也继而被其后研究者所关注。
(一)对诗性的再寻找什么是诗?诗性是什么?诗性作为诗艺术的本体特征,其内涵经过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追问,成为最具探索价值而又最难被探明的问题。“诗性”(poetic)一词出自意大利美学家维柯,他认为诗性基本特征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就像“原始人类把同类中一切物种或特殊事例都转化成想象的类型,恰恰就像人的时代的一些寓言故事一样”。⑧诗性是涉及人类思维、情感、心理、语言等多方面的术语。如何在对诗性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开拓新的学术空间?探讨中国诗性文化与诗观念就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有学者从文化意义生成和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中国文论史上诗观念进行了梳理,抽绎出中国诗观念的本质意义,分析了中国诗观念构成的模式与元素,认为中国诗性特点是“道性、不可言说性”,而中国诗观念的本质是“不可言说的审美情感”。⑨还有对诗性语言特性的研究,认为“诗性语言”是“利用种种手法,破除规则、逻辑等压制,使具体化倾向得以强化的语言,是使人潜在的具体化倾向得以发掘、解放的语言”,是一种“虚拟意向关系”。瑏瑠在文学研究领域,“诗性主要涉及情感和想象的内容,既可以是词(字),也可以是句子,特别是修辞,最能体现出语言的诗性”。瑏瑡近些年诗性研究不多,尤其是落实到具体文本研究的成果更少。厘清诗性问题能揭示文学语言与语言艺术的关系,也期待这方面早日出现突破性成果。
(二)对语言的再思考旧有研究方式使文学语言让位于主体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其理论基础还建立在语言工具论上。即使涉及语言问题,也多从传统语言学和修辞层面来谈,缺少对文学艺术性、语言思想性维度的辨析。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到来,语言终于摆脱工具论的束缚,成为代表思维活动与衡量思想深度的本体。当语言哲学的智慧之光照亮文学世界时,语言作为文学的存在方式被人接受乃至膜拜。语言学和哲学界对该转向的引介较早,①他们从语言哲学层面讨论语言与存在,将语言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新认识汉语形式对文化、思维、思想等精神维度的影响。这种富含开创精神的研究令人瞩目。理论方法的更新开启了全新的学术视角,提供了多样的文学阐释空间。例如汉语影响下的文学及文类研究,在把握语言特性的同时,充分结合了语言哲学的理论深度,因而对新文学语言特色的思想性阐释极有深度。②再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结合思想变革的语言运动,在阐释语言与文学革命的关联、探讨新文学产生的原因时,适当运用语言哲学理论无疑很有说服力。③这种研究方法也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其后的文学语言研究多少受到过类似思路的影响。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语言研究,不再停留于对语言形式的单纯分析,而是上升到对语言形式与精神维度的探讨,使文学研究的立意更加深远超拔。新颖的理论固然能为文学研究提供再阐释的空间,但这种阐释怎样避免内容空泛,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庞大恢弘,怎么把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研究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去,落实到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品中去,这仍是有待我们去探索的。
“言”与“语”的拓展:言语研究与话语研究
与“语言”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词是“言语”。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比起语言,言语与个体的联系更为紧密:“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了最终的规定性。运用词语时,每个人都跟别人想得不一样,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差异会像一圈波纹那样在整个语言中散播开来。所以,任何理解同时始终又是不理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离异。”在洪堡特看来,尽管语言结构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主体对语言的重新加工,语言也就只是“一大堆散乱的词和规则”,⑤是僵死的材料质素,而不能靠自身产生出意义。只有经过个体的加工,语言材料才能成为活的语言,而言语活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比语言系统更具有灵活性。索绪尔在洪堡特的研究基础上,很有创见地将语言学研究分为“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等方面。对于语言和言语,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由于言语自身的特性,它很难被系统研究;语言则不然,“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①所以当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符号系统进行研究时,言语研究法一开始就有一定障碍。
当然,近年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也存在对文学言语的研究。如强调文学主体性,把文学作为言语现象的研究;②还有对文学言语表达私人性等问题的研究。③这类研究巧妙寻找到言语和文学语言的学术交叉点,从侧面丰富了文学语言学研究,从语言的公共空间转入私人场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语言与主体两者的存在关系,是单线条的先后关系,还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语言与言语是不可分割的,正如言语的主体(说话的人)与语言符号不可分割一样。过分强调主体性会不会令研究结果有所偏颇,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也有从话语角度进行的文学语言研究。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或写出来的语言,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语言形式,还是具有社会性、整体性的语言实践。在巴赫金看来,话语是“说者、听众和被议论者或事件这三者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④话语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运用到诗语研究领域,也为相关研究增添了理论张力。例如以汉语诗歌语境变迁为切入点,在综合开放的研究视野下考察新诗话语的研究,⑤体现了开阔的研究视野。话语研究具有跨界性质,研究包含的内容可能稍显驳杂。但这种开放的内容结构也正体现了当代文学语言研究更尊重事实、尊重文学本身复杂性的特点。当然,就新诗语言研究而言,话语研究还只初见成效,有待深入探索。
作者:夏莹王泽龙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