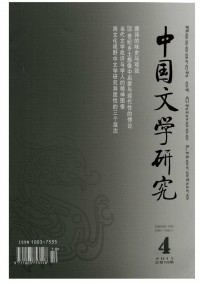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反思

中外文学史叙述的传统,就体现了福柯所谓的以“团体”、“流派”或是“运动”为单位的特点。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就是从这个谱系研究思路出发,对欧洲19世纪的“流亡文学”、法国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文学流派、社团、运动,进行了脉络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同样,这种谱系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运用也是有传统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学案”式书写,可以说是一种侧重文学谱系的研究,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以学派为基础,以人物为个案,将各个学说流派的来龙去脉以及演变情况,分析清楚。文学评论方面,南北朝时期钟嵘的《诗品》对于诗歌题材和作家艺术流派的探讨品评,宋代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及元朝方回对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追认等,也可说是从谱系的角度来进行的文学考察。这些研究反映出文学自身发展的状况与过程,同时其背后也掺杂了谱系研究者自身的文学旨趣和审美标准。因此,除了描绘并确定文学发生、发展的源流和脉络之外,还给文学鉴赏和批评确立一种趣味标准和审美标准,因此,在注重考据的同时,文学谱系本身的得以确立,也带有着很大的主观性,同样反映出其建构过程中各种差异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按照福柯的意思,上述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都存在着过于强调宏大叙事而失真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如福柯所描述那样,单纯强调一个个孤立的文本和作品,完全丢失掉传统谱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难免会陷入“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窘境。尤其就中国文学史的特点来说,思潮、运动、流派社团的作用,往往会影响到单个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产生,这些作家作品一方面有着独特的个性和价值,另一方面又从来不是割裂孤立的。如何在保持对个体现象、文本作品的真实理解、认识的同时,能从具体文本作品出发,还原文学史的历史脉络,这才是文学谱系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文学谱系研究不同于我们通常熟知的文学史建构,文学史主要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历程,而对文学中的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和相互关系,就难以给予多方位的观照,这不免影响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谱系研究则是以文学自身的问题为中心,就好比家谱以姓氏为中心一样,对家族的记录尽可能的详细。文学谱系研究也要尽可能地还原文学自身的细枝末节,以凸显文学的历史感和现实性。文学谱系研究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研究也不相同,它是以一个更宏观、更综合、更深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学,通过文学自身的逻辑关系,打通各个阶段、各种文体、各种现象之间的界限,把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各种研究综合起来,使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既有宏观视野,又不乏微观分析的研究模式。如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谱系的研究,围绕“鸳鸯蝴蝶派”的命名,以新旧文学的冲突为中心,广泛涉及到相关作家作品的评价、思潮论争的辨析、社团流派的定位,以及文学出版的机制和读者群体的划分等等。这就以一个具体的文学问题为展开点,构成了一幅涉及多个层面的相关问题的丰富画卷,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谱系研究还打破了“雅俗二元对立”的研究方式,从而给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互动互补、多元共生的模式。
文学谱系研究能为人们提供更贴近文学自身的线索,在纷繁复杂而又具有演化规律的文学现象中,看到多种文学概念的交融与创新,以及不同文学作家、作品的源流、传承与发展。同时,文学的谱系研究还能为文学鉴赏和批评确立一种趣味标准和审美标准。综上所述,文学谱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代学界学人虽然编撰了许多文学大系,包括文学史的撰写和作品选的选编,但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流变过程,也没有很好地确立文学经典的价值体系,反而显出比较凌乱、繁冗的缺点,文学史越写越长,作品选越编越厚。而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就是立足于追根溯源、去粗取精,寻找文学自身的内在关系,在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的双重视角下,重新构建中国文学经典的图谱。二是促进中国文学整体观的实践。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的整体观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有助于打破各个阶段文学各自为阵尤其是新旧文学二元对立的局面,从整体着眼,加强对中国文学内在渊源的勾连与疏通。中国文学整体观的确立,对具体的研究与教学,乃至对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发行,都会起到崭新的积极的作用。三是推动文学经典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本身就是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提炼,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编选,还有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的人生体验等方面的多重阐释。作为文学谱系最为直观的代表,一部成功的文学大系,应该是厚重且精炼的,能够真正为读者所熟知并接受的。研究文学谱系就是为了凝聚目光,融铸真正的文学经典,扩大文学在当下的影响,促进中国文学经典在中外读者中的接受与传播。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中,或者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由于审美观念的各异,总会有一些文学问题被遮蔽。而文学谱系的研究以特定的文学的具体问题为中心,更关注文学内在的相互关系,因而往往能够挖掘那些被隐藏、被埋葬的“文学遗迹”,使那些趋于碎片化的“文学遗迹”能够重新出土,可以补充文学史书写的缺失,让文学的面貌和特征,变得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更具历史感和真实性。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除了文学史叙述,各种文学作品选本及文学大系的编撰,在建构中国文学谱系的努力中显示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如《昭明文选》对于各种形式文学作品的辨析整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唐宋散文的编选,钟嵘《诗品》对于文人的品评划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对古代散文的编选,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理论、创作的整理编选等。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来看,以作品选本及文学大系为切入点来建构中国文学研究谱系,具有独特的效果及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启示
一些“文学选本”,虽然不是“发展史”,但由于它是按照文学产生的顺序或文学旨趣相近排列的,因之也具有了“潜史”的功能,通过认真考察和辨析,能够隐约捕捉到整个文学发展的沿革和脉络。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除了文学史叙述以外,各种文学作品选本及文学大系的编撰,同样表现出建构中国文学谱系的努力。由赵家璧主编,1935年至1936年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五四新文学产生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文学总集。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朱自清等中国新文学理论、创作的奠基者也参与到这项编纂工作来。它那全面、完整同时又充满个性的编选体例,如同古代一些总集、诗文选一样,对于之后的新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乃至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谱系的形成和架构。
(一)《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谱系意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距离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这期间固然出现了一些对于新文学作品单个的论述和反思,但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出发,对于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源流、脉络的梳理,尚付之阙如,虽然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等这些最早对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叙述,但是从文学谱系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史叙述还很难充分、全面展现出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图景,也不能完全提炼出其区分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本特征。这说明,文学史的书写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在新文学刚刚发生才十多年,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文学史显然不足以承担起新文学谱系建构的任务。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开篇便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个整个的叙述。”①在他看来,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时间太逼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展现的则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谱系意识。在《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当中,对于晚清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一系列的文学观念和思潮都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思考,可以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胡适在自己主编的第一卷《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当中,对于晚清直至五四这一段时期白话文、新文学产生、发展的脉络有清晰的溯源和整理。胡适认为,从晚清姚鼐、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倡应用文,告别骈俪诗赋,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谭嗣同、梁启超的政论文,再到吴汝纶、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等人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新文学文体解放、平易畅达等因子,开始敲响了古文学的丧钟。但是在对晚清以来进步的文学观念以充分肯定和吸纳的同时,他也总结了这些文学观念、实践失败的原因:“他们的失败,总而言之,都在于难懂难学。文字的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人为成功。”②然后才引出王照“官话字母”的主张、劳乃宜“简字全谱”的主张、以及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国语罗马字”主张。从这些思想主张发展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再从白话文运动,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理论包括“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进化的文学观”的提出,这其中的历史发展逻辑脉络一目了然,十分清晰,充分反映了以“启蒙”、“进化”、“现代”等观念为代表的新文学本质品格和特征。这样一种注重新文学自身思想观念、文学旨趣源流、传承的谱系意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其他几卷的导言当中也有充分体现。有学者就认为:这些导言“执笔者不仅亲自参加了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非常熟悉头十年的历史,而且代表了不同的倾向与流派,在导言中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文学观,对其后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他们又是当时之硕儒巨擘,因此所撰各集导言,便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自身的编写体例,决定了它不仅仅是对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简要介绍,还是新文学历史发生、发展脉络的梳理,大量的文献、作品的编选,可以充分展现新文学本身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依然以《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为例,两卷的主编者胡适和郑振铎不仅收入了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阵营的大量文章,同时也收入了林琴南、严复、胡先骕、梅光迪等所谓旧文学阵营的反对文章,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新文学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其间的断裂、分歧、论争恰恰构成新文学自身谱系中重要的环节与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是通过这种‘否定’力量,五四的‘新青年’们力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的主体同一性。这种新的文学主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区别……”①这也是编撰者们谱系眼光和意识的体现。
(二)《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谱系特征文学谱系的描绘与建构,同时强调宏观视野和微观细节的展现,兼顾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新文学发生早期的文学观念固然重要,但是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需要文学作品作为佐证和生动的说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作为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一共十卷,其中理论占两卷,而文学作品卷占七册,史料占一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之所以长期以来得到学界的肯定,有两个基本的、重要的原因:一是每卷前的导言集中体现了新文学的整体追求和价值取向。文学谱系的形成首先注重的是源流、宗谱、相互之间传承影响的关系,虽然十卷本各自导言部分的撰写人不同,且各自有着明显不同的文学风格,但是在某些涉及新文学自身谱系建构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保持了一致。以文学谱系最为重要的源流问题为例,几位编撰者如茅盾、朱自清等人都把新文学的起点指向了《新青年》杂志。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写道:“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②,第二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则被视作新文学的小说创作实绩;朱自清在《诗集•导言》中也认为:“胡适之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可见,无论是文学思想观念还是文学作品创作,《新青年》的作用,都在新文学自身的谱系脉络中凸显出来,这一历史逻辑在之后的大部分文学史叙述中也被采纳和继承。与各卷导言相比,《新文学大系》的作品选择似乎并不那么受到重视,而实质上,作品应该是整个《新文学大系》建构出新文学谱系脉络的主体。用胡适的话便是:“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固然是史料,这七大册的小说、散文、诗、戏剧,也是同样重要的史料。……新文学的创作有了一分的成功,即是文学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一部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与其他文学史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但有理论上的介绍和历史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有大量新文学的作品创作作为支撑,用具体生动的文学作品描述了五四以后十年内中国新文学的创作景象。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体的划分形式,对晚清以来逐渐兴起的小说、戏剧给予了及时的肯定和认同,打破了古代文学传统里偏重诗、文的倾向,使得四种文体趋于平衡。尤其是小说共占三卷,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人编撰,所选篇目基本涵盖了文学研究会、《新青年》、浅草沉钟社、新潮社、“乡土文学”、创造社等创作群体和流派的创作,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的情况和谱系特征。二是作品的选编最能体现新文学运动所坚持的文学理念和主张。例如与新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白话文创作理念相违背的旧体诗词、骈赋,被排除在入选之列,即使是属于白话文创作的通俗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没有出现在大系编选的行列。大系从理论思想的梳理,到历史脉络的叙述,再到四种文体划分和具体作品的编选,都体现了新文学自身谱系的特征,也体现了新文学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他们自己对于新文学的体悟和认知,以及对于新文学自身脉络谱系的梳理和选择,这对之后文学史的叙述和总结,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黄子平指出的:“‘大系’所确立‘文学史’叙事原则,却深刻而久远地延续下来了:文学的进化史观及以‘十年’作为分期单元,文学史内容的‘理论、运动、作品’三大版块,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大文类’,等等。”①中国新文学谱系的基本系统和特征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撰就初具了雏形。
(三)《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独特价值自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谱系有较好的建构以来,之后又有诸多文学大系被编选出版。但是对比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这些后来的文学大系的建构都是不成功的,未能较好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框架,反而显出凌乱、冗杂的缺点,或是材料齐备但是缺乏特点和清晰的脉络梳理,无论在成就还是在影响上都无法与第一个十年的大系相提并论。以周扬、夏衍、巴金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为例,它继承了第一个十年的大系的编写体例,并且在以前的基础上扩展到了文学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电影、史料等九个部分20卷内容,较之第一个十年的编选规模更加宏大,列入的作家作品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如果仅仅是从收录作品、资料的完备情况来说,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要远胜于第一个十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二集》的《导言》中就说:“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②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在导言中也这样说自己的编排:“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③《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选中,更多体现的,是许多编选者个人的个性选择。朱自清主编的诗集当中,郭沫若的诗歌编入了25首,但是《凤凰涅槃》这样一首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里都要充分强调的名篇,却因为不合他对于新诗的审美认知,而没有入选;胡适的《一念》,本来已经删去,朱自清却认为“虽然浅显,但是清新可爱,旧诗里没有这种”④,又选了进来。郁达夫所选编的《散文二集》当中,一共挑选了散文131篇,周氏兄弟的散文就选了81篇,占了全部入选篇目的一半还多,而在所选周氏兄弟的文章中,周作人的散文又占了57篇之多,而这还是郁达夫自己“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的结果⑤。这些充分反映了编选者个人的旨趣和眼光。然而,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影响和效果来看,第一个十年大系的编选并非如鲁迅、周作人自谦的那样是“见闻有限”或“胡抓瞎扯”的,恰恰相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于新文学谱系的建构,特别是对于中国新文学经典作品的形成,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是之后几个十年的大系远远不能比拟的。应该看到的是,文学谱系不等于家谱,虽然要追溯源流、力求全面完整,但是不一定越宏阔就越好。没有选择,就没有所谓谱系建构,很有可能流于资料的整理收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成功在于,从胡适到鲁迅,从郁达夫到周作人,编撰的过程里存在着关于新文学相近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追求,这其中又都有许多自己不同的见解和喜好。这些喜好和个性的背后,渗透着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对于新文学历史价值、地位的理解和看法。这样一种不求全责备,但是去粗取精的方法和态度,与中国古代文学诸多经典选本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所选篇目与其自身的经典意义的形成,也使得中国的新文学在刚刚萌芽的初期,能够在绵延复杂的中国文学史中找准自己的坐标和定位,树立起清晰的脉络和框架。可以说从主编到各卷编选者共有的谱系学意识,是《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价值取向
以往对于文学谱系知识的获取与认知,主要来源于各种文学史的叙述。而当下的文学史建构,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甚至重复的阶段,文学史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和程式化的境况,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从目前的谱系建构来看,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和研究情况来看,文学史所呈现的文学谱系,无论是就西方福柯所强调的复杂性、差异性而论,还是就中国传统谱系观念中秩序性和关联性而言,都是有欠缺和距离的。实质上,如果我们回溯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就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三大板块(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作品)、四大文体(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括许多文学史观念、历史分期问题的处理方法,都来自于这部大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后的文学史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汲取了许多具体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它奠定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构架和组成部分,对文学史写作的宏观影响不容忽视。”①在这之前,也有过诸多的关于新文学的文学史出现,例如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等,然而并未形成真正成熟的文学史范例和体式,更不要说对于新文学谱系整体的概观、研究以及建构。恰恰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出现之后,一套完整的、成熟的谱系展现出来,并且影响了后来文学史的写作。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大系所奠定的体例和观念的基础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不同时代的文学史著作相继产生,新文学史的写作不断走向成熟。
相反,倒是效仿《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编写体例进行编选的几部文学总集和丛书,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接着第一个十年大系陆续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到各种按照地域、流派出版的文学总集、丛书和大系,例如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等等,在资料的收集、汇编,研究的更新和细化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却远远没有超越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系即《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成就,缺少了高屋建瓴、涵括历史的谱系意识,以及独特的个性特征和学术眼光,不仅在文学史建构的谱系方面显出了自身的局限,而且造成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失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它是在现代文学研究起步的时候,真实地表现了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场感,这也体现出“五四”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本身的文学谱系建构形式,在当时文学史研究刚刚起步的阶段就属于一种创见。其次,直接让当时的作家依据自己的个性和认识来描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没有程式化的框架,完全是由文学史的亲历者从自身体验和对文学理解的角度出发,对于新文学的作出估价。尽管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诸如郁达夫这样的编撰者表现出了较强的个人倾向,但是也充分体现了文学和作家本身的个性观点和独立价值,能够真实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文学取向。再次,《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什么叫“大系”,不叫“作品选”?究竟何谓“大系”?所谓“大系”我理解,不在于求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在于从作品编选到导言,从史料、索引到论争,第一个十年大系的编撰者们,拥有一种系统的建构思路、谱系的学术眼光。此后的几次大系编纂,不但在编撰者的选取上不再具备与时代同步的优势,而且编撰者独立真实的个人体验和个性见解也在日益规范化、程式化的架构中逐步丧失,包括王瑶、唐弢等人的文学史在内。设想如果当年赵家璧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限制大系各卷主编的编选,那么即使能够展现各类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鲜活面貌,也难以有清晰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和丰富的史料会被全景式地展现出来,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大系”了。中国新文学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是文学自身从思想到形式不断调整、变化的时期,应该有一个谱系式的描绘,应该有一个类似《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那样对于文学史、文学观念、文学作品的整合和细分。特别是像大系中的几篇导言那样,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进行的高度凝练、提纲挈领同时又海阔天空和充满个性的描述与概括。不是重复性的盘点,而是如数家珍的叙述,是作品论、作家论、资料论与史论等融为一体的谱系性建构。当然,好的作品选,是对于文学史叙述的一种有效补充,大系的成功正在于,它是用作品本身的编选来确立新文学本身的谱系脉络和编写体例。从这之后各种文学大系、作品选的编选情况来看,一部完善、成熟的作品总集和大系编撰,应该具有文学谱系研究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文学谱系研究应该具有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要以文学自身发展为主要脉络,同时确定几个研究的维度:
第一,从作品评价来看,应该从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代表性和个性四个方面出发,来综合确定作品本身的地位。任何一个谱系研究,都是以其构成谱系的本体为研究基础,从中国古代的诗文选到《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它们共同的成功经验来看,都是先从作品自身出发,在重视其艺术个性的前提下,同时注重对其思想性与代表价值的研究。
第二,要兼顾文学发展流变脉络的梳理,这是谱系研究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大系的建构,也要有整体性的概括和轮廓。具体的文学作品不是完全割裂、孤立、无联系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文学作品往往形成一些有传承的社团流派,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京派、海派,作品与作品之间都有着丰富的关联,它们之间构成一个完整、深厚、开阔的脉络联系。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各卷导言为代表的谱系建构,就是要把这些作品在一个发展的脉络中统摄起来,在点面结合中得出史的评价和文学谱系的架构。
第三,应该注重对史料的把握。对于材料的处理要准确和细化。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许多编选者本身都是新文学的直接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一些历史细节的细微感受,能够直接体现在导言和编选当中。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只能靠在材料的处理上多下工夫,如同西方谱系学所强调的那样,注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第四,提炼出来的文学理论、思潮特别是文学作品,虽然应该注重资料的完整和全面,但更应该树立经典意识和眼光,去粗取精,在漫长的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整理出最能代表文学发展历程和成就的经典作品。说到底,文学谱系不是历史谱系,要树立的是一种艺术标准、文学经典的标准。总之,四个价值取向,四个基本维度,共同关注,互动推进,才是文学的谱系学研究。事实上,新时期以来,正是从以上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出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建构才逐步进入正轨和成熟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编选以及文学谱系的研究建构,也亟待贯穿这样的价值取向。在文学史建构进入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在各种文学作品选的编选梳理还稍显滞后的双重背景下,这样做更有助于文学本体和发展脉络的认知与研究。
作者:刘勇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