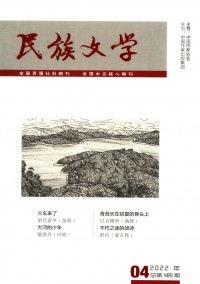文学转向论文:文学的人类学转向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文档上传者
- 文学逻辑布迪厄文学观
- 文学
- 文学哲学
- 文学改良
- 京味文学特征
- 左翼文学唯物
- 文学逻辑观
- 文学形式
- 舞蹈文学
- 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