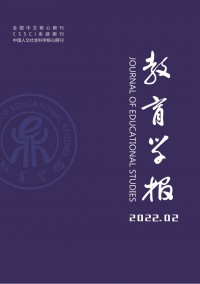教育学发展现状分析

一、构建中国教育学初期时教育知识分子职责的偏离
教育知识分子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号召下,激情澎湃地投入到学习苏联教育学理论的活动中,正是他们的大力配合,使得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变得越发全面和深入,使得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以后要经历诸多的磨难。
(一)知识分子的盲从
经过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目的的一系列批判运动,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性渐渐消减。当时我国提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教育界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并开始学习。尽管在学习之初就强调学习苏联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杜绝教条主义,但事与愿违。当时的教育知识分子把苏联教育理论奉为“圣经”,把中国教育理论自身的建设让位给对现有教育学特别是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换句话说,人们探索的是如何学习凯洛夫《教育学》,而不是对教育理论自身建设的分析和研究。随便翻阅当时任何一本《教育学》,都有凯洛夫《教育学》的痕迹,比较凯洛夫《教育学》与当时中国任何一本自编的《教育学》,几乎都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费孝通回忆当时学习苏联教育时教师的情形,颇具讽刺意味的指出:当时教师上课困难比较少,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对于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并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家驳斥。教育研究者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将它奉为真理,在编写自己的教育学讲义和教材时,也丝毫没有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全面移植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观点,几乎与照搬毫无二致!虽然当时也有学者表示异议,但在学习苏联热潮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反而遭到同仁的批判,因为这种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悖。
(二)知识分子缺乏质疑与批判精神不可否认
“学苏”运动对促进当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苏联的教育学理论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也遭受过批判(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所于1948-1950年曾组织过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因为它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引用,在绝大多数层面上采用了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体现一种过分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凯洛夫《教育学》过分强调统一、强调正规化、强调教师主导作用、课堂教学作用的思想,使培养的人才虽然比较整齐划一,但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中国教育研究者虽然也有人对该书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过异议,但为数甚少,且没有涉及实质性的问题。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徐国棨回忆说,他们当初学习凯洛夫《教育学》时,因为新接触,对它也是有过私下的不公开的评论的。教育工作者这种微弱的不满很快被学习的热情取代,学习苏联由不自觉逐渐变为自觉的行动。对这样一部教育学著作顶礼膜拜,不禁令人反思:知识分子是否已经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是否已完全沦为学院建制中专业化下的应声虫?对权力诉说真理,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和本色,而中国教育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成功改造”,其独立思考意识、批判意识日渐削弱,越来越偏离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职所在。在这种思想状况下,他们不会、不敢也没有能力去发掘凯洛夫《教育学》的缺陷,质疑与批判意识严重缺乏。恐怕凯洛夫教育学的“魅力”,正是不在其深,而在其“浅”,不在其难,而在其易。惟其“浅”、惟其“易”,才便于教育界知识分子如法炮制。教育研究者作为中国教育理论建设的主力,目睹教育理论界这种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理论的现象,却视若无睹,他们的这种漠视已背离了知识分子的职责。知识分子的职责要求知识分子有公共关怀意识,要求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发生在该专业领域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揭示与批判,而当时中国教育知识分子却丧失了公共意识,为教育理论界这种不辨是非、完全否定自己、盲目照搬苏联的现象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使中国教育理论自身的发展在1951-1957年间基本停滞。虽然在1958年“教育大革命”期间,有的教育学著作体系与凯洛夫《教育学》迥然不同如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学》,但到了60年代初又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的基本框架上。
二、中国教育学的曲折发展
学苏运动只是中国教育理论坎坷发展历程的起始,教育工作者在钻研苏联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获得了教育体系、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对充实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如果说此时由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对教育理论的发展危害还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后,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的由人格独立的教育研究者变为权威组织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者与阐释者,把教育理论的研究变为方针政策的汇编或其注解。20世纪60年代,教育学变成了语录的汇编。有的学校甚至不开设教育学课程,而开设“教育思想课”以替代教育学,其教学纲目往往是“教育要革命”“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等。教育变得不成其为教育,而变成了语录的汇编式讲解,完全被“语录化”了。直到1976年,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教育研究者的热情得到调动,关于教育理论的研究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但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泡沫。一些教育学研究者的著作出现一些“败笔”:有为评职称临时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著作;有为盲目追赶时代潮流,用新词汇叙述旧理论的毫无新意的著作;有为以权谋私,利用权势强力发行的著作;有校际或同行合作,自产自销短平快的互惠型著作;有为哗众取宠、以盈利为目的编写的敷衍式著作……难怪陈桂生批评道,如果说以往曾有“教育政策法令汇编”或教育学语录化的教训,那么现在的一些《教育学》著作倒像是“古今中外教育知识的堆积”,而不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学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依附”成为最突出的特征,与其说这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不如说是教育研究者“盲从”的结果。当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我们不应该过分苛求他们,但对此他们仍难辞其咎。陈桂生指出,在中国,由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要想一下子产生优秀的、杰出的教育学家,或在当前的教育理论基础上产生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现在还谈不上。但改善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环境,并非不能做到,外行的非难、无端的干扰是难以避免的,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者要了解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耍手小腕’趋时附势者不能指望在教育基础理论行当中出风头。即使出一阵风头,也不免烟消云散。‘飘风不终期’,其此之谓也。”
三、结束语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但肩负着传承与创造文化的责任,而且肩负着对社会、对人民的的重任。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原因,自1949年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可算多舛,一系列批判运动大多以知识分子为矛头,在批判的浪潮中知识分子逐渐迷失自己并随波逐流,开始偏离知识分子的职责,其知识分子精神走向衰落,由此给学术界、思想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叶澜认为,学科犹如人一样,它的成熟应该以“自我意识”的形成作为标志。如果学科缺乏自我意识,那么它的发展就不可恩能够从“自在”走向“自为”。教育学的发展与完善和教育学自我意识的成熟,需要有人格独立的、有自主创造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教育研究者来建设,教育界知识分子要勇于承担起这个责任。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思想上的独立、自由,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化的教育学。为此,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职责,捍卫其知识分子精神不褪色,呼吁知识分子职责的复归,以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作者:丁慧鸽 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